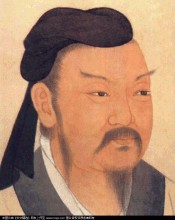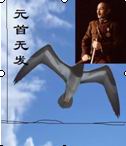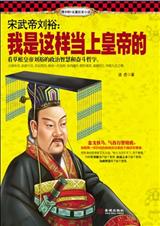刘裕评传-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58人,到崇祯年间已超过20万,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增长为原来的三千四百多倍,可见它比人口平均增长率高出了多少!
从刘邦到刘裕的时间跨度,约是从洪武到崇祯的两倍,虽然不象朱明宗室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刘氏宗族在各地繁衍的数量,必然也已经是非常可观。所以我们在看史书时,见某某是某大人物之后的记载,虽然不排除确有冒认的可能性,但如不经分析,简单地一概认之为非,也是不够客观的。
京口古惑仔
年幼的刘裕在从母家住下之后,他的父亲刘翘又重新娶了妻,新娘是洮阳县令萧卓的女儿萧文寿,很快刘裕就有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道规和刘道怜。几年之后,刘翘去世,继母萧文寿把刘裕接回了家(究竟是刘翘先去世,还是刘裕先回家,在史料中并不明确)。
虽然在文学作品中,继母常常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但刘裕的继母肯定不属于这种类型。因刘翘已死,刘家的经济状况更加窘迫,萧文寿一人拖着三个孩子坚难渡日,刘裕也在这种日子中渐渐长大**,成为一个“身长七尺六寸(约1。86米),风骨奇特”的健壮青年。总的来说,萧文寿待刘裕很好,而刘裕对这位继母也非常孝顺。不知是不是因为名字中带个“寿”字,老太太福寿双全,一直活到八十一岁高龄,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做皇帝时才去世。
不过除了孝顺之外,青少年时代的刘裕身上,基本也就看不出什么优点了。他不好读书,仅粗识文字,整日间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靠卖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似乎还不如他当小吏的父亲。挣不到钱也罢了,他偏偏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赌技又很低微,到处欠帐,很被乡邻们瞧不起。于是,京口世家的家长们在教育下一代时,就不用到远处去找反面典型了:“你要再不努力上进,将来和刘寄奴一起编草鞋去!”
中国历史上的创业之主,其青少年时代的表现常走两个极端。一般说来,其中出身豪门者往往是模范青年,如王莽、司马懿、慕容垂、李世民等;而出身社会下层者常常是问题少年,如刘邦、刘裕、朱温、王建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于出身豪门的人,对他们来说仕途的大门一出生便是敞开的,不用费力去挤,但同时也身处舆论的监督之下,名声良好与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而对下层人来说,在“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是不会有人去关注一个穷孩子是否好学上进,是否德行出众的。出身低微的人中,只有那些蔑视规矩,敢想敢干,带有赌鬼性质的亡命之徒才更有机会抓住命运的赐予,来实现鲤鱼跳龙门。
有一天,刘裕赌博输大发了,欠下了当地大土豪骠骑谘议刁逵三万钱的赌债!这笔钱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位县太爷大半年的工资,对于此时身无长物的刘裕来说,是一笔巨款,当然赔不起。赔不起的结果,是他让刁逵的下人给抓住绑了起来,一顿好打。此时幸亏他有一位阔朋友——骠骑长史王谧帮他代还了赌债,才算勉强过关。后来的历史证明:刘裕有惊人的天赋,奈何术业有专攻,他的才华并不在赌博上,但他的赌徒性格却伴随了他终身。
王谧(mì,读音“密”),字稚远,琅邪临沂人,乃东晋名臣王导的孙子。这个如假包换的高干子弟,大士族出身,如何会与此时的小混混刘裕认识呢?
这就有点说来话长了,据说,刘裕早先有一次去京都建康,回京口时在途中一个小客栈休息。小客栈的老板娘对他说:“里边有酒,要喝自己拿。”刘裕好酒,进去就喝了个醉,倒地便睡。过了一会儿,王谧一个家住京口的门生正好也途经这个小客栈。因为都是熟人,老板娘招呼他:“刘寄奴正在里边,你们一起喝一杯吧。”不料这门生才一进里屋,便吓得跑出来,惊问老板娘:“里边是什么东西?”老板娘进去一瞧,还是刘裕在睡觉,便出来悄悄问这门生:“刚才你看见什么了?”门生答:“刚才看见一怪物,生得五彩斑斓,好象蛟龙,不是刘裕。”后来,门生又把这则奇闻告诉了王谧,王谧忙吩咐他别乱说。但此后,王谧开始结交上这个不起眼的刘寄奴,时时厚礼相待。(见《宋书·符瑞志》)
如果这件事不是虚构的话,很可能这个门生是刘裕的铁哥们,两人合作演一出双簧,来诈王谧的钱财。从后来刘裕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政坛,出老千时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心理素质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王谧与刘裕交上了朋友,并为他还了赌债。多年后王谧将惊喜地发现:这是他一生中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
不过这只潜力股现在还看不出有增值的迹象,不管在制鞋业还是博彩业都不象大有前途的样子,他的机会究竟在哪儿呢?
其实机会已经悄悄降临到他身边。刘裕十四岁那年,一个能干的三十四岁贵公子到与京口仅一江之隔的广陵走马上任,就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开始招兵买马,编练新军,他的名字叫谢玄。两年后,谢玄移镇京口,因当时京口又有“北府”的叫法,这支新建的精锐之师,便有了一个在后来威名远扬的名字:北府军!
京口往事
京口是个好地方!就象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京口能够产生刘寄奴这样军政强人并不是偶然的。
它的位置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地处江南运河北口,江北则正对广陵(今江苏扬州),地扼江淮运河的出口(尽管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才挖掘贯通的,但它其中连接淮河与长江和长江至钱塘江的部份,即邗沟与江南河,早在春秋末期便已由吴国建成),是江南水运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是经济发达的重要贸易中心。而且其地北临大江,南靠峻岭,依山傍水,地势易守难攻。东控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富庶之地(即所谓的“三吴”之地),西距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不过一百余里,朝发而夕可至,实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汉末建安年间,割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就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当称作“京城”,后来孙权迁往建业,“京城”改为“京口”。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北方再没有了安宁,陷入一轮接一轮的征战杀戮之中,短短数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一个个“国家”和势力勃然而兴,又骤然而亡,让人目不瑕接。象查尔斯·达尔文爵士在《物种起源》中总结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此持续不断的外力冲击下,华北原有的城镇乡村的自然结构完全瓦解,能够活下来的百姓要不是集结成一座座坞堡自卫,便是组成一个个武装流民集团,从北方涌入南方,另寻侨居之地。而地处交通咽喉,又富裕的京口自然首当其冲。
大量流民的到来,改变了东晋初年京口、广陵一带的人口结构,北方来的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的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土著。处在北方战乱不休的大背景下(其实南方也没好到哪儿去,也就是逃五十步与逃一百步的区别),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从淮北冲到江南的武装流民们都不简单,早见惯了流血,刀把子握得远比锄头把子熟练,所以千万别把他们想象成是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憨厚朴实的种田老汉。这些武装流民的首领们,即当时所称的流民帅,因手中握有或粗或细的枪杆子,也往往成为当时政坛和军界的风云人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中流击楫”的北伐英雄祖逖,两度勤王的忠臣郗鉴和被逼造反的苏峻等。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京口一带,民风强悍好斗,随便在街头拉个卖烧饼的,军事素质可能都要超过承平年代的正规军,绝不象如今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是吴哝软语的温柔乡。这对于当时控制了京口的实力派人物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价钱便宜量又足的高素质兵源!当初权倾一时的大司马桓温,就因为一度不能把京口控制到自己手中,而醋意绵绵地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落到郗愔手里了?——他想说但没说出来的潜台词)。”
得了,京口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优越条件,如同一个养份丰富的“军阀培养基”,所以它后来成为了与荆州并列的东晋两大地方势力集团中心,也就丝毫不让人奇怪了。下面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谢玄之前京口的历任老大们:
头一个,要算郗鉴,他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据说是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他幼时孤贫,但好学不倦,以儒雅著名。曾作过“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秘书(掾),后来发觉司马伦不自量力地想过皇帝瘾之后,决定不陪着他送死,泡了个长期病假,辞官归家。之后他又拒绝了东海王司马越和征东大将军苟晞的征召。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政治眼光敏锐:这几位大人物后来没一个有好下场的。永嘉五年 (公元311年),刘聪的汉军攻陷洛阳,郗鉴历尽艰辛,辗转逃出,回到家乡高平。当地乡人推他为首,集合一千多户人家组成了一个流民集团,到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逃避战乱,因他统驭有方,部众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七月,郗鉴在石虎所率领的后赵军队压力下,被迫放弃邹山,从山东退到安徽,进驻合肥。该年正逢东晋发生第一次王敦之乱,晋元帝司马睿气病而死,新登基的晋明帝司马绍素闻郗鉴忠义,手中又握有一支不弱的武力,便乘机拉他为外援对抗王敦。在东晋君臣配合之下,最终于太宁二年 (公元324年)平定第二次王敦之乱,郗鉴因功受封为高平侯。咸和二年到咸和三年(公元327…328年),郗鉴又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中立下大功,升任司空,加侍中,封南昌县公,并乘机入据京口这块风水宝地,在东晋王朝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京口集团正式形成。此后郗鉴在京口经营十一年,直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以七十岁高龄去世。郗鉴为人,忠诚正直,顾全大局,对东晋政局的稳定贡献良多;
第二任蔡谟、第三任何充、第四任褚裒,郗鉴死后,京口集团的声势一度转弱,经他推荐,河南兰考人蔡谟接掌京口。蔡谟也是平定苏峻之乱的功臣,执掌京口后成为朝中反大权臣桓温派的领袖,曾阻止桓温迁都回洛阳的动议,后来因为向朝廷拿架子时闪了手,被革去职务。蔡谟之后,何充、褚裒相继坐镇京口,但这两位都属于中央派来的空降部队,在京口当地没有根基,能力又不足,特别是褚裒北伐大败之后,东晋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京口扫地,只得在褚裒之后代之以郗愔;
第五任郗愔,字方回,郗鉴之子,晋成帝时袭父爵为南昌县公。凭借郗鉴在京口的威望,到晋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郗家人再次入主京口。可惜郗愔虽然忠心不亚其父,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号称仅次于他的姐夫王羲之,但若论起军政两方面的才干,比起他那位千锤百炼的父亲,差得就太远了,最终使郗家丧失了对京口的影响力。当时东晋的头号权臣,荆州集团的首领桓温对京口之地垂涎欲滴,费尽心力必欲得之。正巧郗愔又有个极聪明的儿子郗超,是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