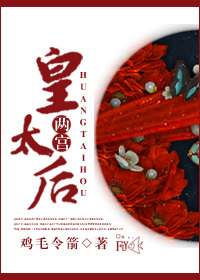̫������-��1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Խ����˵�ָ�������Խ��������з����Ҳ��Dz���ֹ�ġ���ʵ�ϣ��紺��������ž���ǰ�������¾�ԡ�ң������������ϲ衢��̸�����ơ��IJ������̼����Ƶķ����Է�������ȫ��ֹ�ģ���Ϊ���ϡ�
�ŵ���ʱ����ع��С�����ͬ������½��¶�棬���Ҽ������ټ���˼ü�һ�ã���Լ��Ϊ�ٽ���أ����ೡ�������³�һ��ʮ����Ъҵ�����������ⳡ����Ŷ��ꡢ��ׯ���鱦�ꡢ����ԡ�Һ͵���ͨ�������㿪�š�����ʮ��룬��Լ������ʮ�����ˣ�����һЩ����δı�棺������δ�������������������Ķ��ӣ������������˵����ж������ٻ������ձ��˳�����ӵܡ��ѹʴ�ѧʿ����֮�Ӻ�������Ҳ���ˣ����������ң�1901��1�£���ʱ���������Ϸ�ү��������ѹ��������丸��Ϊ��������Դ����������ۿ�������ն�ף����˾������Լල������ʱ�൱Ӳ�ʣ����Ƿ�ȷ���Ϸ�ү֮����������֪ȷʵ��ˣ���̾���������ˣ�̫���������ˣ������������������չ�����ͨ�ڣ�����ͷϣ����ʱ�������ϣ��������ó��ӣ����ᳵ��·�մ����ˡ��������ټ������ˡ��Һ����Һ���ͬԡ��ԡ���Ҷ������˰���һ����ĥ��������г��졣��������������һ�Σ������DZ��������������������Ҳ������š�
��������֮������ȥ�˻���ң��Ҹо���������ȥʮ�ּ��У��ƺ����·��������������Σ��۲��ڼ���Щ���Ե�ͬ�����ߣ������˾ۼ�һ�𣬱�Ȼ��Ѱ�����֡����Ƕ�δ�����£�����������������ġ����빧���������̳�����������������������ǰרΪͬ���߰���һ�վۻᡣ
ͻȻ��̨���´���һ���Ϻȣ������¡����������ϣ����˲��Ҳ��ӣ���������֮���ط����Թ��ˣ��ص����������ƨ����
�ұ�����ʶ������ǰ�������������������������̻�������һ���˵�Ҳ���¡���������˵��һ����������ġ�������������̫���Է�����ͷ�����˼���ɫ�������ʽ����ߵ�Ь������Ӣ�ʹ�¡���������ֻ�������Եģ����������Ƚ������൱��ŭ����˭���ҳ��Բ�ѷ����
�ط��ŵû겻���壬���༸�˴�������������ط����Ϸ�ү���������ɡ���
����ͣ��ͷ���Ϸ�ү�������Ը���Ϊ�����㽾����������Ҳ���ţ������ֳ��뿪�����ͷ�䣬�ȴ����·��ɡ�����������̫�������塣��
������������������������������������ԡ����IJ���֮�ͣ�4��
����֪�Ϸ�үϲŭ�������ó����˿̵�ŭ����һ������������ط���ȷ���Բ�����ð�����ǣ�ʵ������һ���������һ�������øУ��û����ѡ�������Ȼ���ţ�̫�����ڰ����ϣ�������ƽ��������̸�˼��仰������ƫ���мӣ��������ݲ��繧�����ߣ�����ʱ�������������ͺ����������������š�������ôһ���£��Ҳ£����Ƕ��䡢���Ұɡ���
���ǵģ�̫����£�ȷ�������ϣ���ȴ�������С���
�������ҽ�ֹ�����κ������֣�Ҳ�����κ��˺������֣��������ӣ��Ҿ�Ҫ����Ӣ���Һ������˵������㣬���Ӻ��桯������ת�������������������˶���§��һ��������
�������������Ϸ�ү����������ϴԡ֮ʱ�����ź�
������Ȼ֪����������������ζ����������ȡ������ӻ���ν�����
�˿�����Ϊ�Ϸ�ү���ϲ衣�����������¡��ֵ������ҵ�����ɲ���ִ�������������뿪���ۣ�������ͬ�Ե�����������������Ƕ��õ�ȥ���ˣ����߽�ƨ���۶����ˣ�����ӭ��֮·������������ܣ����ǣ��������������м��ˣ���ø��Һú���ʾһ������
���������һ����ò����ԡ�����ټ������Ϸ�ү��������һ�������ӣ�Ҫ������������̫����������ⲻ�ǹ��������֮�ˣ����Һ������֣�����Լ��ʮ�����£���Ϊ�������Ƿ����ѷϴ��߿��ģ�����ȥ��С���������̷��Ϸ�ү�Ѿã���������˴�ǰ�����ı��ӡ���ʮ�����˫���ij��ţ�Ҳ����ο��δ��������֮����ң����������Ҹպͺ�������һ��֮���������Ϸ�ү���͵�������������һЩ�л��ģ���Щ���Ϸ�ү���в��ԣ�����������Ȼ��
���������Ϸ�ү�����������£�����ӢҲƵƵ��ͷ���·����Ǿ��Ե��мһ�����ˣ���������ȫ������������ȷ����ˡ�
�߿���̫��������ϯ����ѡ��������ƨ�ɡ�����������������β��ʸ���ԡС�ˣ�����������������ֹ���ţ�����֮����˿�������з����ڲ���о����Σ��Ϸ�ү̰���ض�������������ζ��Ȼ����֪̫���Ƣ�ԣ������Ժ�����ʵ���ǣ���һ�������������ˮ��ʱ��Ҳ�õ�ǡ���ô�������֮������������̫��ߵͷ��̫����ã�������һ�������Ӹ���ϯ���߿�Ҳ���˷��ͣ���һ��ߵл���м��Ϸ�ү�����ġ�С�ۡ��Ŀ���֮�ͣ���֮������
ͣ��Ƭ�̣��Ϸ�ү�������ϣ�������ʾһ�飻����������ױ��Ӻ�һ�������ү����ع�ֱ��������������ˣ������ǖK�������������Ϳ����������뿴���ַ����������е�������ع��үҲ�Ǿ����¶��ģ�Զ�����֣������������������ţ������������ȣ��ĺ�Ԫ�������ǻ���������Ӳͦ���ʸ��Ϸ�ү�������ߴȰ��ذ���Ƭ�̣���Ȼ����ع��ȥ�����Ƿ����������������ڴﵽĿ�ġ��Ϸ�ү����ʮ�ֻ�ϲ���Ը�һ���ʹӣ����������ֽ��Ѷ�������������ɡ����ױ��Ӻ;�үл��̫������ǰ�ߵ����������������Ժ��ߵ������Ҳ���ûʲô��ͷ�ɣ��������ӿ�Զ�����������
�������ң����Ҳ�������Щ���ӻ���˲��ã����Ҵ�����Ļ��ɣ�������֤��������һ���ǿᰮ�Hƨ�ɵģ��Dz��ǣ���
��̫���Ҳ����ʸ�ش𣬵���˵�ѹʵİ������ӣ�������˹����������1892�꣩���պ���ܳ�Ϊ�����ģ�ȷ�д���ʮ����ǰ�����أ���������Cleveland��St����һ�ڳ��š�������������¼���������һ�������м�Ժ��1889�걻�ؾ����Ѳ飬�����о�˵�����������ء����ϡ�ά�˶����ӣ�Albert��Eddie��Victor�����������������˴��£�δ��ȡʲô�ж���̫������֪����������Ӣ�����ķ���ȼ��鵼�¡�ߪͨ�����̴�������Է��س����𣬽��ᱻ��������ʮ�꣬�������ǰ���ᱻ�д����̡�����֮������潻�ϻ�ؽ���Ҳ��Ҫ�ܷ��ģ�һ��������Ҫ�������ꡣ��
������������������������������������ԡ����IJ���֮�ͣ�5��
���ǿ����ˣ����Ϸ�ү�������˼�ϲ���Hƨ�ɣ���������ȥ���ˡ���֮��㵱��Σ���
���ⲻ�ö�֪�����Ҳ´�����������Ͽ����������ڽ̷����Ե�ɣ������dz������������˵���α����
�ӱ����Ͽ���̫�������һֱû��ƽϢ��Ŀ����һ�������μ�֮����Ѹ��������������ˣ�������Ӣ���ҽ���һ�ԣ����ң����˼�ԼĪ��ʱ���賿1�㣩�������Ϸ�ү���������ٹ�һ������ҹ�����ɡ�����˿���������档
�ҹ���������˼�ⲻ֪�ҵ������ڽ�����Щʱ��Ļ���֮���Ƿ�����Ӧ����Ҫ�ܾ��������Ҳ�����ܣ����������֮ʱ�������˶����ɻ��ˡ��������������ҽ�ڣ����Dz��ܱ����ܵģ��ͷ·����DZ�ª��������˵�������ź��Ҳ��ܲ��ܾ����ĺ��⡱һ�����ܱ��½⡣
�����Ϸ�ү�ֽ����������µľ�ү���Ҳ���֪�����֣�ֻ��������һλ�Ǻ��ֱ���һλ�����ֱ�����Ҫ����¶�����ߣ���״���ˣ���Ϊΰ�������������������Ө���β�������һ�����꣨�Ҳ¶��Ǵ�Լ��ʮ�����ͣ������꣬����ү��������ԥƬ�̣�����������δ���䣬��ϰ�ߴ˵����£�û�Ǹ�����������Ȼ�����Ƕ���ϸ��Ϳ���㣩��������������������ӣ�����ָ��λ��������֭����֮�¡����ɣ�������ɦ����ཫ�������˵��ϣ������ǰ�Ķ���һ�㡣�������͡��У����ϱ��������ɩ�з��������������ÿ�ζ��������ڵ��ϡ��ϵ��ط����������ܿ��������Ϸ�ү�������Ŷ�����˵���������Ĺ������ˡ��������������൱���Ľ�����
���������IJ���֮��Ϸ�ү��Ƣ���ش�����������ѵ����汣���á���
����ү���ǹ����Ϸ�ү�������£��ܷ����������С¿������
��ֻҪ��ͬ���ɣ���Ͱ����ղ��ŵĶ������Ӻ��滹�����ɡ���
����Ӣ�����ӵĻ��ǹ��ƶ��ޣ������������塣���������������Ϻ���̵��β��������������һ����
�����˶����Ǹ�¯�ӡ���̫�����ǰ�����ž��ڵ��ϵľ�ү˵��������İ�¯�ӣ�ͨ���Dz�ΡΡ�ع��ţ�����������������Խ������˿��ѽ���ҹ�����跨�����Ϸ�ү��������Ӣ���ҵ�����ʱ������Ϊ����һ����ҩ���������ǿ϶������õġ�
̫����������ˣ�Ҫ���Ķ����ˣ���������˳���ǵ����£������ɱ��������ǵķ���֮�����ǵ��۶�������ô���Ҳ�ɦŪ����һ���Ѱ����׳���������ֻ��������ͨ�ĺ����಼����������Ҳ�ᵽ��ֻ����һ����������������˭Ҳ���ͣ�ͽȻ����עĿ�������ڹ���Ǿ�ӭ�°ɡ��͵����ˣ��ټ�������������ζ��ص��ͷ�������Ǽ��������ķ��죬����ʱһ��������������뿪������ԡ������100��������ѹ�����������ִ���һ��������������ң��ҹ�Ů���Ƿ�������õ������ĵط����Ҵ��ϰ���죬�����غͰ�����ͬ����������飬����ȻҲ�����Ź��ڵġ��̶����Ǹ��Լ�ȥ����Щ�Թ�δ����ӣ���������Ҳ��ֻ�г�����š��ҴҴһظ���δ���ҵ����ٸ�֪�����˵ȣ���Ҫ������һ��Լ����Ȼ�������ҹȥ���ҵĽ��ӱػ������ɣ��ҽ������������������ͽ���֮�㣬����ֱ������������ᵽ�����ٹ��������賿һʱ������Ӣ������ҩ���ҷ��¡�̫��û����ͣ�����ȵ�Խ�ã��Ҿ�Խ�������ȡ�
������������������������������������ԡ����IJ���֮�ͣ�6��
������1894�꣬�Һ�Ī��˹������˹��Maurice��Barres����һ��������ɫ�軨ʢ���������İ����ʽֵ�����Rue��d��Eperon���ۻᣬ��˵������һ�仰����ÿ���˶��а�����˹�Ľ��࣬ÿ���˶�����Ȥ��ʱ�����ڰ���˹���ԣ�����֮��������ʥ֮������Ϊ��Ҫ�����߹�ִ�����·������棺����������ֻ���ҳ��ѻƬ��������չʾ����IJ����ҵ�������Ϣ������ǿ����û��ʲô���ظ�һ��������¸����ģ������ǹ���ΰ�ˡ�����˹��������Ϥ����֮�ˣ����������������˵Ŀ�ѧ�Ҽ�˹ͨ������ϣ����Gaston��Boissier������������������˹��Tarsus�������ޣ�Saul���ݷ��������н���һ����������Լ��Ը������ͬ�����������������ء����أ�Walter��Pater������ţ���ѧ�ĵ�ʦ��һ��ֿ��ϣ����������������Щ�����ڰ��˼��һ�������������š���Ҳ�����������ð���˹�Ļ�����������һ��������ҶԴ���֮��������ϣ����������ܣ����ҿ�����һ����������ɴ�����������νС�����ν�٣���ǡ�ƶ���֮��ɪ�գ��ι��е���������ƥ����ʷ�Ͽ�����һ������ӻ�Ů�Ӷ�ԶԶ��������������ǰ��������ԡ���У����������������֮�£�����ֱ���š���ʲ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