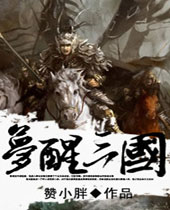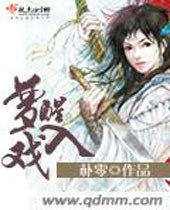�������ӱ䣭����������˼ ����:����-��2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ռŲ˦���������Ŵ��ȿΡ��Ժ��������Ų��ʣ�ȴ��ȫ����˼�������ú��ϣ����±�����ˮʦ��ֻʧ�ޣ���Ω�����Ӹ��£�����������Ҳ�¾ɲ���������̫������ʱ���й���������ƾ����������Ӣ�����˿������ġ�����֮�У��������ۺ��п���ǰ�У�
��һ���棬�������Ե�ȱ��Զ��ʶ����δ�Ӷ�������һ���˵�����������ij�Զ���롣�������������ֱ��������֪����������ǿ��������������Խ������λ��ʮ�����ڼ䣬ȴ��δ�Ӵ������κ�һ����ѧ�������ѧ���鼮��������Ӵ��ⷽ����黹�ǡ��ڼ���֮������������������Ȼ���ظ�����ȴ����û�����ֳ�������κ�һ��������ҵ����Ըվ����������������м䡡��λ�ã��Ա�ʩչ��ƽ����ǣ��֮���ı��졣
�������������ϳ����峯��һ����Ů�ˡ�������Ѻ��˵ġ��������ñȺ��˻�Ҫ���ֵij�͢�����Ψһ��^������վ��ǰ��̨�����˵����緢��ʩ���Ů�ˡ�Ҳ�����˻���˳�ε�ĸ��Тׯ����̫������ТׯҲ�����ݽ����е�һλǿ�ˣ���������ǿ��ʮ�֡����ģ�ǰ�ж����İԵ����������ݵ�רȨ�����־�����ô�ܡ�����������ȣ�����������������������Ȳ��������������ġ�������ֺ��������˳֮�������ϵ���ǰ��Ҳû�г��ֹ�ʲôȨ������
Ҷ����������һ��������ʵ��Ůǿ�ˣ�����ǿ�ˡ����Ӳ��á���Ȩ���䣬ȴ������ȡ������Դ��J�ɣ���ʹ��ʮ�ּ������Ҳ���������˼���ͷ��أ��İ���̫�ల�º���ɽ��Ѳ������ͷ�����������ݡ������ʱ��ʱ�Ŀ���������Ҳ�����á�������ط����������͵������£���������Э��֪��ʲôʱ�����ò���ʲô��146
ʱ��ֻ�����á���������۸��ӵ������У���ʼ���ܰ������ֵġ�ƽ�⣬�ɹ��ؽ����͵ĵط��������������ɷ�Χ֮�ڣ���Ȼû�С��÷�����صĵط���Ա�����Է��Ă�ʲ����Ҳ�ܱ�֤��������Ǩ������֮Ȩ���������
��˵�������������ʵ�����ʦ������˹����˵����ʵ���ϡ�Ů�˵�Ȩ������ת�������Ȩ���������ϻ��Ȩ��������Ϊ���ǡ�Ů�ˣ��������ٵ�Ȩ������Ҳ��Ϊ����Ů�ˡ����������������ϸչ�����ԦȺ���������࣬��Ȩ���ں��ڣ�Ⱥ��Ī�����������ĴݰΡ�������������������۴���ᷨ���ǰ������ƶȣ��������õذѳ�Ȩ�����Dz��Ϸ��ģ����ƶ�����Ψһ��ƾ��������ǡ�ĸ��ĸ���ƶ�Ӧ���˾Ӻ�̨��Զ��Ȩ�����ġ����ƶ�ȴû�С��涨����ĸ���Ҫվ��ǰ̨�����ӽ���ô��������
�Ա�����Ȼ�����Ҷ�������ϣ������Ĺ���������ֻ����һ��������٪��0���Ⱳ���ܵ��ϻʵ۴���żȻ��������������ͬ�Ρ�����������ɥ����ͬ�ε�ƽ���������������Ҳ�Ų��ϵġ����ǡ�������������ɣ�ͬ��ʮ����������Ȫ���������ӣ��������������컨����Ұʷ�����Ļ���������֮����ͻȻ������Ȩ��������������һ����ʽ�ϵĿհף�Ҳ��ʵ�ʰѳֳ�������̫�����һ���ѡ��⣬������һ�����������ҳ����ʵ�����Ҫ��ס�Լ���Ȩ�����á��ʵ۱���߱����¼���������һ�ǻ����֧������˲����Է����ڡ�����ͬ��ƽ��������˾�������ĸ�������ٳ��������䡡Ҫ�㹻��С������˲��ô�������Ҫ��Ҷ����������Ѫ��ϵ����������ȥ���ƴ��������������ֻ������֮������һ�����ѡ��ڡ������������������飬����û���ں���ɥ���ӵı�ʹ����Ѹ�ײ������ڶ�֮�ƽ������С���ٱ����˻ʹ���
�����ϵ�С���������ڵ�ʱ�����Ժ����˿��ú��������������֮�ӣ�������ɣ����ѿ�����ִ��Ȩ���ҵ���ĸΪ��֮�ã���
147
���յ����곤�����ʹ֮��˳�ԴӼ�֮��Ҳ�㡲1����ĩ��ʿ�ސ��^��Ҳ˵�����Ǵ������ո�����Т�պ���Ҳ��Т��������ר������Ϊ�����ڣ�ͬ�Ρ�������Ϊ̫��̫���������裬������������������Ҳ������2����������Ȼ�����ˣ�������һ���Լ������Ӿ����á��ˣ����ڷ��ƶ���������˵Ĵ��ң�һ������������⣬�Ρ���ͬ����Ϊ����֮��Ȼ����ּ������������ĸ�ף�˭�������䡡���أ�
�����С���ٱ�����ͿͿ�ر��������ϣ������������ˣ����������IJ��ҡ����˵��DZ���û�ݵ������˻ʵۣ����ڴ�ͳʱ���ǡ�������������������١���λ��ԡ����ҵ������ĸ��������롡�����������Ӵ˾�������һ��Ůǿ�˵���Ӱ�������ʧȥ�ˡ�ͯ��Ļ��֣�����ʧȥ����һ�������˵�Ȩ�����������������ۡ���������ʹ�Լ���־��Ȩ��Ҳ������ɾ������35���������Ȼ���������ã���������������������ǰͷ������Ĺ�����ȻҲ������̫��һ�������˵�Ĺ�����۰����������⡣
�����������ϵ�ĸ����ʵ�����Ǵ������������������ԡ���̫��Ϊĸ���෴�������Ǹ����Ԑ������ˡ���Ȼ����Ϊ�˺�����Ϊ�ʵۣ���������Ʒ�൱������Ҳ����������Ϊ���н�ǿ�ĵ��¡����θУ�������ȷ�����Ǹ���ǿ�ĺ��ӣ�Ҳ�����Dz��ò����ϵġ���ʵ��
�������������������˾��Ǹ���ʵ��������û��ʲô�����ġ��ˣ���һ�����˲���Ĺ�ҵ���Ǵ���ץ������������˳����λ������ʵ۵ĵ����ӣ��ӽ���ʼ�����ܵ���̫��Ŀ��ƣ�һ������С���J������̫�����i������С���̷��Ȼ�����˱������ٻ�����裬��Ҳսս�̻̣�����Խ�׳ذ벽��������֪�Լ��Ķ��ӱ�
��1������Ӣ������¡��˺�˾����������͡�����85ҳ������2��3����˴���������й�������ʷ���ϡ�����452ҳ��
148
ѡΪ�ûʵ�ʱ����Ȼ������������֪���룬�����ؼ��ڣ���ս����ҡ��������Σ��´������иμ���֢��ʵ��ί�ٳɷϡ�����������Ȼ��������ʱ�뵽������Ϊ�ʵۡ�������������ҫ�����Ǻ��´Ӵ˱������빬͢���������У���Ϊ����֪����λ�����̽㡱�����������֪�ڻ�Ȩ��Χ�������շ����
��������������������һλ���ڽ������ˣ���������ĸ���䡡����̫��������ã�ȴû����̫��İ�ָ�����һ��ֻ��һλ�������ؼ��Ĺ�̫̫��
�����������ļ�ͥ�����ڸռ���ʱ�ͱ�������������ڴȡ������ߣ�ʹ�������������������С���������֮������Ȼ�������ס����õķ��ϣ�Ҳ���������������ӵij��ԣ���̫���С�������ǡ������ģ�������˵�����ʵ۱���mʱ�������꣬���岻��ʵ����䡡����ʪ���ɣ���ÿ3������ã���ҹ����������ϣ�ʱ�亮ů���ӡ������ƣ�������ʳ���ʵ�����ۡʱ��������η����չ���ҽ�������֮���ҿ��鷽ֽ�λʵ�ʶ�֣����ڡ����顷����ʫ�������Ұ���Ω���ֲ������а�����������Щ��Ӧ��˵��Щ����ʵ�ģ�����ҹ�����ԡ������ҿ������棬��������Ϳ�á����¾�δ�أ������鷽ֽ�����̻ʵ�ʶ�ֿ��ܣ������ڡ����顷��حʫ������δ�أ���Ϊ���Լ�����ûѧȫ������̫��Թ�����Ȼ��������Ůǿ�˵İ����е����ˡ��ܲ��ˣ���������ר�ƣ����ðԵ�����������Сʱ���y�������ף�������̫�������ܡ����ԣ����ֳ�Ϧ�ദ�ġ�������������С����������������ӡ���ˡ���ĸ�����Ͽɲ�����ӡ���������꺦�¡�����������ʱ���Ծɾ��´��ף�������������棬����ʦ���̡�ͬ������Ѱ��ӻ���һ���棬��̫����Ϊ�ˣ�����һ�������ܽ��������ˣ������������֮��̬����ϣ�������õĺ��ӱ�Ϊ�Լ�
0�������£�������������¼����һX�ܵ�3ҳ��
��2���B����������ּ���I������䷨�����ġ�����2��ҳ��
149
�ĺ��ӣ���Ϊ�������������������˶�Ȼ��Ϲ�С��������������ĸ����ϵ����ͬ��һ��֮�ڣ����������������һ�����硡���졼���ɣ���Թ��������������������ɲ�����Ӱ�졳����̫����Ҫ���Լ�����־����С�ʵۣ��������Լ�ϣ���ķ���ȥ�ɳ����⡡�����켴ʹ�ԡ���������ʽ���֣�Ҳ�����˸е����ܣ���С������ȴֻ�����������ܵķݡ���С£������������Ϊ��ָ������ֶŮ������һλҶ�������ϵ��ʺ��̱����˼������Ƿ���Ը����һ���棬��������������ֲ�ϣ���⺢�ӱ�������Ļʵۣ���Ը����˶��������Ѿ����˺ܾõ�ӡ���ӡ�����������ì�ܵ���̬����̫�����С�����Ȳ����܃����Լ���˵����һ�ĺǻ��Ĵ�ĸ��Ҳ����������������ʱ��˵�����ױ���Ű�ĺ��������Ȼ�Ӽӣ�����Ҳ�����ᷦ������һ�˹���̫��͡��ص������Ǽ�����ָ���ŷ��̹������Ĵ�̫�࣬Ҫ���DZ��뾡���跨�̵�С���٣�ʹ��֪���Լ������ϡ����������֡�����ү�������������ġ��ʰ��ʡ���ǰȴ����ѩ���������ܵ�צ�۹�ȥ�ˡ����Dz����˼ҽ������ڶ��ĿȾ��С�⡡��Ҳ�ܿ��֪���ˡ����ʰ��֡���ɜy�����ϣ�����ӡ������ġ�Ȼ����֮�������̾��������Ժ��ʹ�������Ͳ�����ȥ�뷴�������ʰ��֡���
�Թ������кøе���Ԫ���ڱ䷨�ڼ���Ӧ��ȥ��������˵�⡡���������ºͣ�����ò����Ƿ�ս�������2����ʵ���������Ը���ǡ�����Ƿ�ս�����Ȼ�ڼ���Ұܣ�����Σ����ǿ�ݼ��µ�һ�Σ�Ҳ�����һ�α��������Լ�����Ը����̫��Ҫ�����ֱ䷨��������ʱ�����Ѿ��������������峯���ƶȺ�أ��Ȿ����ְ��Χ����֮���£�������̫��ʱΪ�Ͼ����������ȣ�Ҳ���Dz�Ը��䷨������Ȼ�䵽���̶ֳ��������ۡ�ֻ�Dz���Ը��Ȩ�����Թ�����������
0�����z���������Ѫ�ǡ���������������磬��53ҳ��
��2����Ԫ�ã�4��������Ļ��䡷��������䷨1�����ġ���325ҳ��
150
��Ҫ���ۿ۵ġ��Ҳ�̫�����ռ��桶��͢����ܐ��ǡ������صġ��ڰ���ά��֮��������ͨ���������Ȅ�����̫��̯�ƣ�̫�����ԡ���������Ȩ����Ը���ô�λ������������֮�������̫���Ȼ�ᡡɱ�����ڵ�˵��������Ը����λ�������Ѳ�Ը����֮����һ���������ϵ�ʱ�����ƣ����������ԶԶδ����ϵ���ѵij̶ȣ�������Ҳ�����Ϲ������Ը�������˸��ԣ�������ʱ�������ľ����һ������̫��ڲ������º�����ѧ��Ʒ������Ը���������ǿ�Ӹ����������䡰�����������ĺ���׳���ʵ����ֻ�����ǵ�һ����Ը��������һ�����һ�γ��ڱ���������������Ķ�����������������̫��ʥ�⣬��Ը�������䣬���������˱�������ӹ֮���������ǡ���Ӣ��ͨ��֮�ˣ�������������Ϊ��ʧ���ġ��侭���Ŵν�ּ������������������ʱ����֮�£���ʥ��ᶨ���տ������¡����硡ʮ����֮���ͣ���̫����Ϊ���أ��ʲ��ò�����֮���˽���ʵ����Ϊ��֮����Ҳ��������֪�й���������������Σ�����ɴ˱�������������һ��ʹ�н�ּ�����ɷ�����������˱���ӹ֮�ˣ�������֮Ȩ����ʵ��δ�㡣��ʹ��ˣ�����λ���ܱ����ο����������������꣬���к����ߣ��¾ɷ����Խ��䣬��������ӹ֮�����а���ح���ǽ�Ӣ��ͨ��֮�ˣ�����������ʹ�й�תΣΪ����������Ϊǿ�����ֲ����з�ʥ�⡣����������̷��ͬ������ڼ��ͬ־�����ٳ��̣����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