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兰亭序》帖又名《兰亭宴集序》帖,是我国古代着名的行书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极为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所写。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对它有这样的介绍:
(《兰亭序》)逸少(按: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按:即羲之,因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蝉聊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暮春3月3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41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所记如亲历者见。不过相传原本被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得,认为堪称王羲之书法之冠,遂令人临摹了许多副本,真迹为其死后陪葬于昭陵。后人见到的《兰亭序》帖,皆为临本摹本。
《兰亭序》贴摹本以冯承素本被公认为最近原作。全篇凡28行324字,写来从容不迫,气韵生动,雄秀兼蓄,文情并茂,真让人感到达到心手合一的高度境界。
除摹本外,唐初的虞(世南)、欧(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书法大家也都有临本传世。但后人评论说:“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去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嗣后,宋代的薛绍彭,元代的赵子昂,也都有临本相传。尽管这些临摹本都各自透露出它们的临摹者自己的个性特色,表现出相当的艺术价值,但均不是右军真迹,不免越发给人临渊羡鱼之情。
《兰亭序》帖不仅因为后人许许多多的临摹本而给人仰不可及爱不可得之感,还因为关于它还有一些传说,更让人觉得它几近神圣的地步。
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位何延之,写了一篇《兰亭记》,文中除了活灵活现地记叙了《兰亭序》的写作情况,还精心地叙说了一段它后来的命运和遭遇。
他是这样讲故事的:“右军(对《兰亭序》帖)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按指王羲之、王献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于是便想尽种种办法诱取《兰亭》,而辩才却始终推说经乱散失,不知所在。后来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骗取,费尽苦心,终于得手。太宗高兴得不得了,钦令对房玄龄、萧翼、辩才都予重赏。并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向高宗耳语:“吾欲将所得《兰亭》去。”于是《兰亭序》的真迹便被作为太宗的陪葬品而埋进了昭陵。
这真是说得有点神乎其神。特别是太宗死时向他的儿子高宗提出要求把《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带进坟墓,且父子二人是用“耳语”,除非是高宗后来传出,当不可能为第三者所听见,太宗的遗愿,《兰亭》的归宿,又究竟会是怎样呢?
还有一位与何延之基本同时代的人刘其所着《隋唐佳话》也有一段传说,全文是: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按即后来的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诸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这段故事,虽有些情节与何延之所说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依然是把《兰亭序》说得十分神乎,读之仍使人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不过,总的说来,历代比较流行的说法乃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诗友饮酒唱和,得诗三十七首,积成一集,王羲之即席挥毫,写下了《兰亭序》。由于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只有王羲之,他尤其喜欢这个字帖,所以断然肯定系王羲之真迹。其后的许多帝王和士大夫也这样宣扬,使《兰亭序》帖一直享有盛誉。这一说法多少年来几乎是书法界和书法史的定论。
说“几乎”是“定论”,是因为对于《兰亭序》帖究竟是否王羲之所作,还是有人不断质疑,尽管质疑的人不是很多,且终未成大气候。
较早的质疑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怀疑为何在唐以前一些史籍丛帖未见入载,只是在唐之后经过唐太宗的特别“青睐”,又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欣赏”及许多封建士大夫的附和迎合,群起“咏赞”,才把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许多人都不否认该帖有其不可低评的艺术价值,但也有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既经钩摹,即难看出真正的王羲之的笔法精神。
应该说,这些质疑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丰年间的赵之谦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对《兰亭序》帖作者的怀疑。他是话中有话,说:
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变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说得曲曲折折,什么“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什么“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什么“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无非是说《兰亭序》的作者问题,实在是值得怀疑和商量的。谓“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是告诉人们从《兰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来面目”的,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兰亭序》帖的作者不会是王羲之吗?
而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顺德出了个李文田,他比赵之谦就更勇敢、更直截了当,根本不顾世俗之见和千年定论,直白地指出《兰亭序》实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为别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写跋文时,发表出自己的这一看法的。他对《兰亭序》帖提出了几点怀疑,最后的结论是连《兰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写的。因此,“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这一问颇为有力,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兰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话不算很长,不妨全文录在下面: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佳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为《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依李文田的看法,《兰亭序》帖,毫无疑问是一篇“佳书”,观之足令人惊心动魄,但不会是王羲之所书。他从“笔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论,最后得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结论。这一下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把过去人们的质疑导向到完全的否定。把过去“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话变而为明明白白的话说出。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大胆的惊人之语。
然而,李文田发表的诚然是大胆高论,但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仍旧习惯遵循长期传下来的看法,还一直照老样尊《兰亭序》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发难,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挑起了新的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挑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是由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
1965年,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地区出土了东晋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等,引起了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的郭沫若的注意。
他立即从墓主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族关系以及碑文书写笔法,联系到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帖,敏锐地发现由出土墓志可以考索《兰亭序》帖的悬案,对于研究《兰亭序》帖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极好的依据。于是,经过认真揣摹研究,他写出了考证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同时发表),得出结论:《兰亭序》帖不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是出于别人的依托。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并未看到李文田的跋文,观点是和李文田不谋而合。他是十分同意李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李的意见,从许多方面加以考据和论证。
《兰亭序》帖既然被目为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郭沫若就首先从书法上来考察它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从出土的墓志看,东晋几十年间,“基本上还是隶书的阶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其笔法却与已见的“北朝碑刻悬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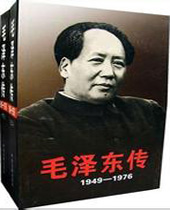

![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8/8401.jpg)
![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9/998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