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岢觥鞍倩ㄆ敕牛偌艺保匾獯掌肓艘话偈仔椿ǖ氖右杂孟笳鳌⒁甑氖址ǎ觥八佟狈秸耄杷躺缁嵘钪小鞍倩ㄆ敕拧钡拇蠛眯问啤K溆行┦缘蒙渤叮帐醮植冢缙渲小都诨ā繁扔髯苈废叩囊蝗涨Ю锏男问疲阂虼耍颐翘乇鸬匕丫毕钌斐ぃ�/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另一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解说“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但这都表明郭沫若是怎样积极主动响应毛泽东,支持毛泽东,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或者是并不想真正将这“双百”方针政策付诸实践。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贯彻这一方针政策时,情况就要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
●四、1957:风云突变,乍暖还寒
“双百”方针给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带来春天的气息,给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吹来的热风,时间却并没有多长。人们似乎还没有怎么回过味来,政治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
从1956年的情况看,国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当宽松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整个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显出了相当的自由气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全国人民,尽可能极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了民主问题。他一再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的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这也有缺点,就是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是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政策方针,但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民主问题本来就不仅仅是文艺,学术民主,也应该包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
正是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是,当民主真正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加大、加强、加浓时,毛泽东又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当时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突破和贡献。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上,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前一类是对抗性质的,后一种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斯大林“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他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方法,解决思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讲话,给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使他们觉得有了保险单,吃了定心丸。人们看到毛泽东反复说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不能用专政手段来对付,而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们开展批评和讨论,容许各种意见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还说闹事出乱子也不要紧,闹事出乱子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处理少数人闹事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对于闹事者则要做好教育工作,即使是对闹事的头子也不要开除,等等,就认为可以无须任何顾虑,完全可以放开胆子说话。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本来就思想敏锐,操心的事情特多,又常犯主观片面的毛病,容易看到缺点和问题,意见也就不少。这样一来,当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当各级党委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一个劲请他们鸣放,劝他们发言,催他们说话时,他们觉得真的是到了“言者无罪”的时候,不免就有点无所顾忌,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起来。
对此情形,毛泽东显得不高兴了。特别是当他听了那些过激言论,一些不很中听的话语,以至具有相当刺激性的意见,他更是非常生气。有人说什么“党天下”,“轮流坐庄”等等,这不明明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夺共产党的权吗?显然,这些言论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更威胁到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历代知识分子都如孔老夫子所言:“近之不逊,远之则怨”,登了鼻子就上脸。他认为到了必须狠狠教训一顿这些人的时候,于是立即提起笔给党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于是,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10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这真是风云突变,原来的好一场热热闹闹,大家竞相提意见,现在便要改为批判修正主义,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社会主义。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立刻变作了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
很有意思的是,还在3月24日,着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中不无激情地说出了他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深刻感受。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文中一方面表现出兴奋不已的心情,又多少流露出一点胆小放不开的味道。即便如此,在整风转为反右之后,《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对这篇代表右派心情的文章进行消毒,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不平常的春天》,针锋相对地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又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如果说是春天,这便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从整风运动发展到反右斗争的过程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思想是有矛盾,是有变化的。
他在着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已经清楚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应该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是要严格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在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许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他又一再号召人们说话,让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然,他在这篇讲话中,也说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讲到阶级斗争,不过它认为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当人们真正畅所欲言,想帮助党整风时,话说得多了些,激烈了些,甚至过火了些(当然不排斥极个别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怀有敌对情绪),他就改变主意,改变做法,变听取意见为反击提意见者了。
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问题产生疑问,发生了动摇,改变了看法,还是他对现实情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远远地把实际情况看得过于严重?
显然,他发出对右派实行反击的命令时,他肯定是认为阶级斗争表现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到了非反击不可的时候了。所以,当人们指责毛泽东是搞“阴谋”(指先让人说话,再把人打成右派),毛泽东还理直气壮说自己搞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引蛇出洞”。这恐怕两方面都没有说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蛇”,并不是存心以“整风”为诱饵,把它们引出洞来,而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有点出乎他的意外,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提意见,而且有些意见提得十分直率,十分尖锐,让他感到情况十分严重,从而决定“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对于由“整风”到“反右”,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始至终还是两个字:
“紧跟”。
他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他一开始就亲耳听了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且多次在最高国务会议小组会这样的高层次会上讨论这一讲话,应该说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知道得比一般人早,了解得比一般人深的。他当时也真是诚心诚意认为党的工作(首先是他自己的工作)确实是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的,说“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他也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人民群众对党整风提出的意见。在5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他不但认真听取了到会的科学家们对科学院领导作风的批评意见,还诚恳表示今后要常下到研究所里和大家谈心,从四面八方来把彼此之间存在的“墙”拆掉。
然而,当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吹响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角,他也就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就在他看到毛泽东写的给党内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后,便在6月27日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现在,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经他这么一说,好像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完全是那些“右派”违反了民意,触怒了人民,是自下而上地要求给予反击。更有意思的是,他以自己的“机智”十分巧妙地回答了记者问到的关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问题。他说: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
郭沫若在这里显然是似是而非的诡辩。究竟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应该有一定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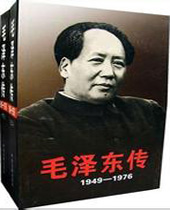

![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8/8401.jpg)
![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9/998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