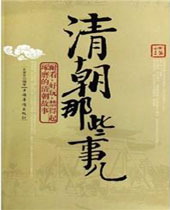这些人,那些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窗外是细雨中的城市,被灰蒙蒙的云层覆盖着。从十五楼的高度可以看到城市边缘墨色的山脉,由浓而淡层层叠叠隐现在云雾之间。
「以前……,我们曾经从那边的山上远远看向这边,你记不记得?」他想起弟弟最后一次来公司的那天,他透过会议室的隔间玻璃远远看到的弟弟就像自己此刻一样,抽着烟,背对其他人安静地看着窗外。当会议结束他走进办公室时,弟弟回过头看他一眼笑笑地说:「没想到现在我们却站在这里看向那里……」
他走向窗边接过弟弟递过来的烟,窗户上反射着兄弟俩淡淡的脸孔。
「哪天——,应该再去那边的山上往这边看……,不过,那条路说不定都不在了。」弟弟说着,他看到弟弟的眼眶有隐约的泪花:「三四十年没有人走,早就被芦苇掩没了吧?」
沉默了好久,最后弟弟说:「而且,我们也背不动那两个小的了。」
「我弟弟过世了。」最后,他终于出声,仿佛告诉自己一般,跟一直站在背后的助理说。
玻璃上浮现着助理有点惊讶的表情,以及或许隐约听到他的声音于是纷纷从位子上站起来看向这边的其他人。
「怎么会?」
他没回答,也没回头。
他忽然想着,那天站在这里等候他开会结束的漫长过程中始终没有转身的弟弟,是不是就如同此刻的自己一般,是因为不想让人家看到自己的眼泪?
整个办公室陷入一阵死寂,所有人似乎都僵立不动,MSN招呼的声音此起彼落,但好像没人回应,没有键盘滴滴答答的声音。
公司的人大多跟弟弟熟,曾经也都喜欢他,因为这一两年来差不多每隔一阵子他都会出现。每次一进公司总习惯带一些点心、小吃过来,然后热切地招呼大家吃喝,把办公室的气氛搞得像夜市一般。尤其是他总有办法把他经历过的人生大小事当成笑话讲,即便是最窝囊不堪的事。
而当所有人都笑成一团的时候,他却又忽然感伤地说:「啊——,总之,都是过去式了!」然后就把这句话当句点,收拾掉所有的笑声,一转身以另一个表情走进他的办公室,关起门跟他谈正事。
后来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Tora 桑」。那是日本有名的系列电影《男人真命苦》里的男主角名字。他们说弟弟不仅个性像,甚至连长相也都有点像。
但是,慢慢地他们也跟他一样,很怕弟弟出现。他一出现,即使是招呼或者笑声都可以听得出勉强和尴尬。
因为后来他们都知道弟弟是来跟他调钱或者找理由借钱的,数目愈来愈大,理由愈来愈牵强,而且被拆穿的次数愈来愈多。比较起弟弟,老实说,在人生的路上他是走得比较平顺一点。
虽然同样是初中毕业就离家到城市工作,每一步都走得辛苦,但如果用一种俗滥的比喻说人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至少他都摸得到下一颗石头而且也都可以踩稳。而弟弟的每一步好像都会落水一次、挣扎一番才勉强摸到另一颗,而且摸到的可不一定比先前的宽阔、稳定。
比如同样是当学徒的阶段,他换过几个行业之后就找到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而弟弟却始终四处流荡,不是碰到苛刻的老板就是凶狠的师傅。
退伍之后他很快找到工作,并且顺利考上夜间部大学,甚至还因为发表了几篇文章而多了一个兼职的收入,但晚他两年退伍的弟弟却偏偏遇到石油危机的普遍不景气,半年多之后才勉强找到工作。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弟弟至少还是明朗、积极而且健康的。
那一阵子晚上下课回到住处,只要看到楼下停着弟弟的摩托车,他心里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地方让疲惫的弟弟安心地休息真好。
觉得可以当一个被信任被倚靠的哥哥真好。
记得有天晚上他开门进宿舍的时候,弟弟已经睡了。书桌上放了几袋他带回来的夜点,臭豆腐、蚵仔面线、当归鸭之类的,而且分量总是多到夸张。
洗完澡之后,他一边吃着那些已经凉掉的东西,一边看着弟弟沉睡着的脸,看着看着他忽然想起几年前还是学徒时候的一段往事。
记得是冬天,过年前不久的半夜,弟弟忽然从工作的基隆跑来台北找他。
也许怕吵醒老板一家吧,他不敢按电铃,捡了一根树枝敲他房间外的气窗,不知道敲了多久他才从梦中惊醒。当他开门看到弟弟的第一眼时,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弟弟好像是工作到一半仓皇离开,所以连衣服也没换。那年代的工作服无非就是已经不合身的学生制服,袖子、裤管都短了几号,而且全身上下沾满了乌黑黏腻的机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在外流浪多年的游民。
那时候弟弟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常写信跟他抱怨师傅动不动就打人,但结尾总是像安慰他也安慰自己一般说:「为了学人家的功夫,我一定会忍耐……」弟弟说那天因为动作慢,师傅忽然就一个耳光过来,他本能地想闪,没想到反而被直接打在耳朵上,之后他就完全听不见声音。
「我怕聋掉——,想去看医生,但是我没有钱……」弟弟说,「所以只好来找你。」
也许听觉还没恢复,所以整个过程弟弟几乎都是用很大的音量说着,但是他没有阻止。
后来他烧了热水带弟弟去洗澡。脱掉衣服的时候,他看到弟弟瘦骨嶙峋的背上竟然有好几道长长的伤痕,有黑有红纵横交错。
「引擎的皮带打的……」弟弟说,「刚打到的时候不会痛,打完才会痛很久。」
洗完澡后,他叫弟弟趴在床上,他去找碘酒帮他上药。也许太累了,当他找到碘酒进来的时候弟弟已经睡着了,他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帮他上药,因为他怕碘酒的刺痛会惊醒他。
然后他看见弟弟稍微移动了一下姿势,一如梦呓一般说:「不要跟爸爸妈妈说……,不要说哦……」
虽然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看着此刻同样沉沉睡着的弟弟,记忆里那些依然清晰的画面和声音还是让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那天夜里忽然醒来的弟弟看着他,却以为哥哥是为他的现况担忧,竟然反过来安慰他说:「不要烦恼啦,我会找到工作啦!」
然后要哥哥帮他重新写一份自传。
「不要写得太文学,写完我来抄。」
后来弟弟说,那天去面试的时候,管人事的女人看完那篇自传,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他,然后要他写下联络地址电话。弟弟说他才写几个字,那女人就发飙开骂,说她就知道那篇自传绝对不是他自己写的,嫌他字丑,还说他不诚实,说她们公司不要不诚实的人。
「干!」他记得弟弟一边点烟一边说,「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诚实哦?挑屎不会偷吃啦,诚实?〃
人生很多滋味都要到一个年纪才懂得去细细品味,比如类似这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幸福。
然而当你一旦懂了,一切却都已经远了。
远了——,到底是年纪?是有了自己的家庭,因此有了另一种责任和更亲近的关系?还是工作、生活以及彼此人际关系上的落差,所以把原先那么紧密的关系给稀释或拉远了?
即便到现在他依然不解。
退伍之后的弟弟做过很多工作,后来开了一间小型的工厂做代工。然后结婚生小孩。不久工厂倒闭,还因为票据法短暂入狱。
他则是进了传播界,在压力极大的环境下平顺地工作着。
第一次他觉得彼此之间那种紧密的联系似乎即将慢慢消失的起始点,就在弟弟坐牢期间他去探监的那一刻。
隔着玻璃他都还没有开口,弟弟竟然透过话筒说:「你是名人,不要到这里来!」然后就在所有人诧异的注视下转身离去。
他从没有问过弟弟当时那种诡异的反应的理由,即便是弟弟出狱不久有一天忽然出现在他家里,跟他借钱说想买车当计程车司机,在开车去银行领钱的路程中他宁愿忍受彼此之间那种尴尬而痛苦的沉默,也不敢开口问弟弟为什么。
「长大以后,这个弟弟是要替哥哥提皮包的。」他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在屋外的榕树下,那个瞎眼的相命师曾经这么说过。
他不确定那是几岁的事,但他记得那时自己跟祖父坐在树下的竹椅上,甚至清楚记得祖父抽烟的样子和烟斗的颜色。记得坐在地上的弟弟短裤滑到肚脐下,汗水和泥尘在他额头和腿上纵横的痕迹,记得他不停地把快流到嘴巴的鼻涕给吸回去的样子。
后来他才知道,弟弟竟然也记得那句话。
有一段时间弟弟曾经在他公司上班,过年回老家,邻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听见弟弟用有点自暴自弃的语气说:「在替我哥哥提皮包!小时候相命的就说过了,那个瞎眼的还真准!」
那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原先的传播公司,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影像工作室,而弟弟当了几年的计程车司机之后,由于台北捷运施工天天交通阻塞,加上私家车愈来愈多,收入很不稳定。换新车的钱一样找他借,却也从来没还。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找理由几千几千地拿。有一天一个亲戚来找他,说弟弟跟他借用了一大笔他预备买房子的钱,弟弟还不了,问他可不可以先替弟弟还钱……,他终于约弟弟见面。
弟弟承认他赌博。
「除了这条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地让自己的生活像样一点。」弟弟开车载着他,好像没有目的地地绕,一路绕一路说,「我不像你,笔随便写一写,话随便讲一讲就有钱进来。」
他没有回话,任弟弟有一句没一句地讲。时而自嘲、时而抱怨,偶尔还插入对外头的车子或路人的怒骂:「你以为马路是你家的啊?你不想长大结婚生小孩啊?……」
弟弟说,虽然天天在这个城市里奔波,每天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但终日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的自己其实像一个孤魂野鬼,不认识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认识。到处都去,但前途茫茫、毫无方向:「一天十几个小时跑下来,算算口袋里的收入,可能还不够别人在餐厅里叫一道菜。」
「现在你是名人——」最后他说,「有时候我跟乘客说我是你弟弟,有的说,是哦,啊你怎么在开计程车?有的说,你臭盖!」
一路听着的他忽然觉得苍凉,觉得这个就坐在他身旁的弟弟似乎离他很远很远了。
不过,说不定弟弟也这样觉得吧?他想。
后来车子穿越城市停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山路上。雾很浓,外头白茫茫一片。
那是矿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俯瞰如今已经成为废墟的他们的故乡,但那天什么都看不见。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自己一个人开车到这里……,想一想,想到有些事就会哭……」
「比如呢——?」
「都是一些无聊的事……,你不会记得的,」他说,「像有一次,爸爸受伤在罗东住院,妈妈在那里照顾他,有一天那两个小的因为桌上没有菜不吃饭,一直哭,你忽然说,那我们去远足!还做了一大堆饭团给我们吃。」
他当然记得。
记得他背二弟,弟弟背小妹,带着只是白饭拌酱油的饭团走上山,然后沿着山上的小路,穿过阴暗的相思树林一直走到尽头明亮的山崖。
那天午后天气清朗,从那里可以看得见山下的火车站,看得见无声移动着的火车,以及它即将奔赴的在叠叠山脉远处的城市。
他记得他跟弟妹们说:「那里——,有大烟囱的那里是基隆——,还有更远更远的地方就是台北——,以后,长大以后,我们要到那里赚钱——,然后拿钱回来给爸爸妈妈,这样我们就不会没钱买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