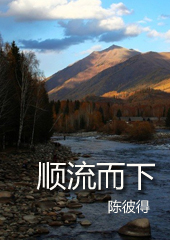顺流而下-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正在目不转睛地偷窥,辅导员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前年从本系毕业留校,一边担任我们班的辅导员,一边考研,一头长发垂到腰间,脸上虽然总是挂着雀斑,但是非常温柔,很容易就让人爱上她。
“Hi。”她碰了碰我的胳脯。
“Hello。”我说。
“Where are your friends?”她问我。
“I haven’t friends。”我说。
“I don’t believe。”她说,“oh,I want ask you when will you pay the tuition?”
“学费?”我说。我最担心辅导员或者班主任问我学费的事,这个学年还需要三千多元的学费,我一直在抵抗,我告诉她们家里还没有寄来。我知道一定是妈妈无处去借了,为了我上这个大学,家里已经借得千疮百孔。“再等等,行吗?”我不想告诉辅导员真正的原因,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你说了汉语了,你得表演个节目。”逮住有人说汉语让他表演节目时大家都可以说汉语,这是英语角的一个规则,辅导员就像一个少女一样笑得合不拢嘴。
“求求你,不要让我表演节目。”
“别怕,表演一个,让大家知道你。说不定你就成了校园名人了。”
我才不想成为校园名人呢。我不能表演节目,我不能让我的丑态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何况台下还有我心仪的女孩瞅着呢。我想抓紧在这个地方消失,可是辅导员拉着我不让我走,一会就过来很多人看,丁丁在走廊下面也往这里看了几眼。在辅导员的推搡下,我被推到了园林中间的圆台上,这是专供表演用的平台。很快园林里的学生都围过来看,在刺目的灯光下我垂着头,我再也不敢去看丁丁,我知道她就在台下。“快点,表演个你们的地方戏?”辅导员在台下鼓励我,可我一直在看我的鞋,一双扁扁的黑色布鞋,自从考上大学我就一直穿着,脚尖处被趾甲顶破了,鞋面也被我刷得泛白。太丢人了,我感觉每个人都是用侮辱的眼光看我,我真想就在这个台上蒸发,再也不出现在人间。台下有个男生起哄喊我“笨蛋”,如果我跑下台逃窜的话,更没法活了。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抚平巨烈跳动的心脏,抬头看着挂在飞檐上的弯月,心中感叹命运的捉弄。“我就给大伙整一段二人转吧。”我说。我唱了一曲《猪八戒拱地》,还弯腰模仿猪八戒的样子,大家笑得哈哈得,我不知道是赞赏我还是辱没我,唱完了我赶紧跳下来,整好落在丁丁面前。
“You look very lovely,you don’t like Monk Pig,but like Monkey King,because you are vey thin。”她笑着对我说。
“Really?”我说。
我很想和她说话,可是我的英语水平很差,我怕我再次说出汉语。不过说英语倒是让我减少了面对她的紧张。
“Would you like eat ice…cream ?”我生硬地说。
“Yes,I like。”
幸福快车突然驶到我面前,让我一时找不到车门。我带着她走出英语角,可以说汉话了,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现在是八点多钟,离就寝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如果这两个小时能够让我和她一起分享,算是不枉此生了。我必须表现得灵巧,不能让一切阻碍我的心理的问题干扰我追求她。
“你很像一个人。”我没话找话说。
“像谁?”她跟在我身后,我不知道她什么表情,于是和她并肩走在一起,离着一米的距离。她走路轻盈,表情轻松,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阻碍她的力量。她又穿着那件丝麻衬衣和牛仔裤,脚上挂着一双高跟的桔黄色凉鞋,她的个头似乎和我一样高,让我感觉压力很大。
“全智贤,就是我的野蛮……。”
“噢她呀,还有人说我像张娜拉呢。”
“张娜拉?”我想在音像店门口看到过一张张娜拉的海报,但是她的样子记不清了。
“你是哪个班的?”
“中文零二的。”
“你的文笔一定挺好?”
“没有,一般。”我说,我不喜欢自夸。
“你喜欢虚构形象吗?”她问我。
“写小说啊,我没写过。”我说。
在校门口的商店里买了两只和路雪冰激凌,花了我十元钱。然后我带她走到不远处的拱桥旁,那里有好几对情侣正拥抱着亲吻,让我非常尴尬。我又带着她走回来,站在校门口的路灯下。她休闲的样子和我格格不入,我就像一个乞丐在向一位白雪公主索钱,可是我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我又不能带她到太黑的地方,免得她讨厌我。站在校门口路灯下,被那么多人视察,也让我无地自容。我拿出下生二十一年来积蓄的所有勇气和力量与她聊天,说出一切我所知道的笑话,让她开心。很多时候,我总是忐忑不安地低着头,不敢直视她的脸庞,更不敢让目光与她的眼睛相撞,我的眼睛只会偶而扫过她的眉宇时,就像探照灯一样。冰激凌奶油沾在她的嘴唇上,她的嘴唇小巧而又丰满,还故意翘起上嘴唇把奶油顶到鼻尖上,可爱的样子无法用语言形容,只有我冲动的身体可以描摹这一景象。
“第一次看到你时,让我就想到很多成语。”我说。
“说来听听。”
“花,月,鱼,雁,羞,闭,沉,落,国,城,天,色,倾,香……”我紧张地语不成句。
“这是成语吗?中文系的喜欢故弄玄虚。”
这夜我知道她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是南京军区的一位少将。而我六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我的父亲现在也许是奈河桥的保洁员吧。我知道这些时,我突然感觉我被推向了远方,我们中间就像隔着一座大山,原本是不可能谋面的,只不过我有一股愚公移山的劲头吧。她的专业是音乐教育,现在正在选学古筝,她答应我星期天到她们音乐楼上听她弹奏。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她就像我梦中移来移去的虚幻影子,在诱引我走向美丽的深渊。
“下次我再请你吃冰激凌好吗?”送她到楼下时我问道。
“OK。”她说。
回到宿舍里,中间的桌子上正在展开牌局赌博。我坐到床沿上,准备找本书看。隔壁的一位同学因肚子疼走了,于是胖子拉我入伙,可能因为我被突如其来的恋爱感觉轰得我晕头转向,没加思索就同意了。很快熄灯了,李思齐把窗帘拉死,由于他们经常点烛打牌,怕被老师抓住,特意加了两层厚厚的黑绒布窗帘。在烛光下,他们三个人就像恶鬼一样想把我吃掉。玩拖拉机,我玩得特别小心,如果牌不好,我就不上,最多输一块底钱,如果牌好,我也不使劲往上押注,很快就开牌,对方也开心没有输更多的钱。有时侯赢了一点点钱,我还兴奋地哈哈大笑。整个晚上我的牌运还不错,没有输钱,倒是赢了十块钱,把晚上请丁丁吃冰激凌的钱又找了回来。他们觉得和我这样保守的人玩一点意思没有,不到十二点就散了。我倒喜欢躺到床上想我的丁丁,任凭意识天马行空。
我把晚上丁丁说的每句话都数了一遍,害怕自己当时没有了解她的意思。最后我的意识全都集中到她说的“你喜欢虚构形象吗”这句话,她也许已经猜测到是我给她写的那些怪怪的情书,所以才这样问我,一想到这,裹在被单里里我好像从头红到了脚腕。夜晚是那样美好,我无心睡去,只想认真地体会生命的每一分钟,体会丁丁的开朗与温存。
第二天,我又向音乐系的邮箱里塞进去一封在山上写好的信。“我只是一介保安,这不能阻碍我有爱的权利,这项权利却深深地折磨着我,我知道我爱的是梦幻,是我不能触摸的美丽,最不能令我容忍的是我的梦经常从我身边擦过,我只能看着那个美丽的背影,黯自神伤。我的工作是多么枯燥乏味,像一个稻草人一样站在那里,挥舞着木偶一样的手臂,敬礼,敬礼,再敬礼,只有在你出现时,我才感到我的工作还是有一点幸运的,幸运的是我能够看到你,那一眼足够让我一天充满力量。我鼓足勇气写出了这封信,请你收到后不要从我面前走,我怕我会站在岗哨上像石膏像一样粉碎……”
在收发室门口我碰到韩雪,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浑身的肥肉如江水在咆哮,我感觉收发室的门是那样狭窄。
“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你那寒酸样。”她冲我吼叫。
“我怎么了?”我说。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和丁铃在一起了?”
“谁是丁玲,那个作家?”
“丁丁啊,咱们的校花,苏州大学生服装模特比赛的冠军。”
“那怎么了?”
“呆瓜,你不知道吗?很豪门子弟都追不上她,你还凑什么热闹!”
“我没有追她。”我说。
“放屁,刚才我还看见你给她寄信。”
“你管我那么多事干什么?”
“我才懒得管你,要不是因为可怜你。”她语气弱下来,“你得小心着点,小心晚上挨了闷棍。跟她在一起,只会让你倒霉。”
第十章
胡子和头发越来越长,身体和自然越来越近,再也没有什么恐惧和羞耻之心。我裸体奔走于沙滩,海鸥也不再当我是异物,有时我还收集很多蛤蜊肉喂它们。
十
我只知道杭州,从来不知道杭州湾。近海的水淡黄如宣纸,迎面的风如飘动的红旗打在脸上。我逼着渔民一直把船开到蔚蓝的海面,途中我看到一处大桥跨进海湾,桥面上布满了钻机,轰隆声几乎掩盖了渔船的马达声。海水越来越蓝,海浪也越来越大,直至四周布满岛屿,我不知道在何处停船好,就继续让渔民往海的深处开,看见军舰的时候我就让他绕行。
我不知道何处可以躲身,渔民娴熟地驾驶他心爱的渔船,不抵抗,也不说话,任凭我的指挥。我们沿着一座座岛屿的外围游转,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成群的戏水者分布于沙滩,还看见奔波忙碌于岛与岛之间的游船。我不愿看到人类生活的景象,直到发现一座离开群岛的孤山,山脚的沙滩较短,只见成群的海欧在礁山上歇脚,还有一种腿儿细长的如天鹅般的鸟,大概是一种鹭,傻傻地立在鸥群中,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里。我让船停在两块大礁石之间,说了声“我不想这样……”,渔民回转头,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弯刀就切入他的喉咙,他的头僵硬地仰在我的肩膀上,急冲过来的海浪吞没了他喷出的血,但舢板上依然血迹斑斑。我把他放平,将锚抛向岸边的石尖。我蹦到岸上后,拉绳把船固定在岸边,把尸体拖到岸上。
桅杆的高度超过了礁石,特别刺眼,我又上船把桅杆放倒。坐在渔民大叔身旁,在海边纯净的阳光下,我的心如一颗朝向风口的巨大海螺,发出愧疚和羞耻的回声。这具坚实的尸体,横躺在我面前,让我想到父亲这个词。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父亲在我六岁时自杀的,他躺在玉米地里,脖子上挂着一把镰刀,而当时的我正和一帮小孩在玉米地里穿棱,任凭玉米叶子刮在弱小的身体上。我不知道这位渔民有几个孩子,这位渔民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也不知道这位渔民在我的弯刀下是否想到了必死,我只知道我必须活着。
我长久地伏在渔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