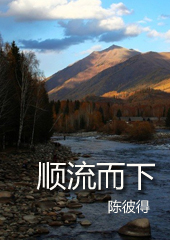顺流而下-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慢慢荡着,船夫哼着歌曲,我知道那是有家的感觉,在家乡的河流中荡着一条心爱的船,生命多么悠闲自得,如果我可以化身,我宁愿做一条船,永远承载着心爱的船夫,将灵魂藏在船底。我又开始有饥饿的感觉,饥饿灼烧着我,浑身如着火了一般。可是每家外卖都有人守得死死的,而饭店的厨房又藏在深处,最后我在河边抢了一个孩子的面包。
在乌镇牌楼一侧,我看见很多人挤在一块看墙上的一张告示,人们异常兴奋,脸皮发紫,眼球暴突,就像看到皇帝在招驸马,每一个男人都对性感、美丽的公主充满向往,希望一亲香泽。我把脸缩进口腔里,挤进去瞧了瞧,我看见我的头像被印刷在一张纸上,下面描述着我的身体特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偏瘦,方脸,双眼皮,高鼻梁,尖下巴,表情忧郁,操东北口音。上面还印着我的身份证号和张野、李思齐、曹路的身份证号,还诱惑地说,对提供准确线索的公民给予二十万元的奖励。我的心狂躁地撞击着胸腔,站在人群中我宁愿变成一只蚂蚁,悄悄地从疯狂的人群脚下爬出去,可是我还是我,陈正强,出生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个雪天的陈正强,最后我感觉我的脸徐徐膨胀,为了不显得忧郁,一种千年不见的笑容挂在脸上,我倒退几步,转身向着没人的地方走去。口袋里空空如也却身价二十万的我足以让一个穷光蛋疯狂,我知道从这天起,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比警察多出百万倍的盲流、乞丐、流浪汉、无家可归者会来追击我,就像追截狼狗一样。幸好工地上的灰垢包裹着我的脸、我的衣服,没有人认出我。我像一阵风一样,跑啊,跑啊,跑出乌镇的入口,跑过一条条小河,最后跑到一座小山上,躲到一个山洞里。
山洞里阴暗、潮湿,我躲在深处,像一具僵尸紧紧贴着岩壁。我看见一架架飞机驶过,空中飘满了通辑令;我看见成千上万的疯子手里挥舞着通辑令,涌上山来;我看见我心爱的女孩站在山顶,警察用枪指着她美丽的头。山洞里弥漫着腥潮味,我害怕里面有蝙蝠,有蛇,有蜈蚣,我总感觉有某种黑暗的生物爬到我的裤裆里。我躲在里边直到洞口的微光消失了,才爬出来,山风激得我起了一身疙瘩,我突然有种发烧的感觉,摸了摸额头,果然很烫。弯月挂在半空,如一只咬掉一口的烧饼。山上没有一个人影,我四处找吃的,幸好找到一种低矮的野枣树,我坐在野枣树旁边,被荆棘扎破了屁股。身边每当有动静,我就得站起来打量一翻,我恨我脑后没有两只眼睛,因为我害怕突然有人从身后把我提起来,把我挂在树梢上。看不见月亮的时候,山上漆黑一片,松涛阵阵如狼嚎一般。我把藏刀攥在手中,我告诫自己,如有生物靠近我身边,就捅上一刀。快到天亮的时候,我在山后看到一条河,但是没有看到船。等了许久,直到太阳在天上划了四分之一个圆,才看到一个人划着一条船过来,我藏在灌木丛中,期待着他能离开那条船。果然,他把船挂在岸边,背着一只篓子向山上走去。等到树木挡住他的身影,我就顺着山坡滚下去,滚到他的船上。我不知道这条河通向哪里,但是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知道凡是接触我的人,工头,马乐,偷我的钱的人,都会知道我就是被通辑的人,都会想法找到我。我必须离开。
我尽量避免与其它的船擦肩而过,坐在舢板上,拼命地划,我希望划出人类的世界,划出警戒的世界。急剧增长的疲惫和身体持续发出的高烧使我难受的要命,实在受不了时候,我就跳进河里,让河水浇灭我身上的火焰。夜晚来临,星星洒满河面,我就躺在船上想我的女孩,她是否正躺在床上想我呢?在那抽屉一样的宿舍楼里,她躺在雪白的蚊帐里面,起伏的胸部是否还能感觉到我的心跳?我许下的诺言是否还回荡她的脑海里?我的梦想是否还在蛊惑着她的心?
我就像孤魂野鬼停留在未知的河流,假如我是一股烟,我一定附着在水面上,让渔夫看到晨起的氤氲,让洗衣妇看到远处和树林连成一片的雾气。可是我还是我,一个吃、喝、有着性欲和恋爱的男孩,一个害怕权贵和警察的男孩,我希望在拮据和困窘中维持高烧的生命,我希望在生命的仅存时刻做一些有为的事。
船已经失控,因为高烧捆绑了我,使我躺在舢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在寂静的夜里,没有愿意陪我的事物,星星退了,月亮消失在云后,曾经觊觎我的蚊子也不知何处去了,没有光,没有声音,只有我残存的喘息。我希望这是一个宗教的世界,让我的灵魂追随着光芒而去,我希望这是一个造反的世界,无数的兄弟在岸边迎接我,我希望这是一个空虚的时代,所有人都会跳河自杀,我希望这是一个远古的时代,没有人类,只有植物在呼吸。
第五章
身上的米粒还没等我去拍它,就兴奋地弹跳起来,飞舞起来,在天空中形成流星雨的形状,形成白玉兰花的形状,形成五线谱乐符的形状,就像Widows media player中的音乐可视化效果一样千变万化。
五
那夜看到我朝思暮想的女孩以后,我早早地摆脱了韩雪,让这块一百五十斤重的肥肉回到宿舍唏嘘感叹。我一直在小饭店门口逡巡,透过玻璃窗偷看她,她的头发遮着半边脸,隐约露出鼻子的轮廓,也许因为夜晚的缘故,他脸部的皮肤映现出一层光芒,她多像全智贤啊,那个生长在韩国的淘气包,一直是我梦遗的缘由。她说话的时候小手在空中飞舞,让人想到蝴蝶、蜻蜓什么的,她的小手将长发从额角捋向脑后的时候,让人想到瀑布、夜空什么的,我多么想变成一颗星星,飘落在她光洁的额头做她的装饰品,我多么想变成她胸前的贴身物件,永远跟随着她亲吻芳泽。最让我讨厌的是坐在她旁边的男生,擅长打篮球的,擅长唱歌的,擅长溜冰的,擅长跳舞的,擅长吹牛的,擅长写作的,都是一些自大狂,用古语形容就是狂蜂浪蝶。他们围着她,每个人都想说出一些俏皮话,逗她发笑,或者讲一些低三下四的笑话,引发性的联想,试图从她的眼角看到一些羞涩的表情,这些人便感觉极大的满足。我真不明白像她那样的女孩为什么喜欢和这些人在一起,难道只为了多长些虚荣的面子,如同韩雪渴望全球的帅哥都跟在她屁股后面一样。
马上要十一点了,学校快要关大门了。他们终于扔下酒杯出来,还没出门口,其中两个男生就大打出手,撞碎了小饭店的门玻璃。店老板冲出来,接着挨了一拳,倒在后面的桌子上,饭汤沾了一身。我听到我的女孩叫起来,混在里面阻止更多的拳头和伤害,换来的却是恶意的拥抱和触摸。起初她还没在意,很快她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恶作剧,但是在这个场面中酒精占了上风,酒精控制了那几个男生的意识和手脚,我的女孩被一个男生拦腰抱着,舌头滑过她的脖子伸进衣领。这时的我被愤怒扯着从路边捡起一根木棍,上去一顿狠抽,不知道打折了几条腿,打断了几只手,打花了几张脸,我的女孩在一旁看着,我,一只怪兽,如同《美女与野兽》中的狮子,全身散发的怒气都可以把人烧死,待到那几个男生全都躺下,头顶的鲜血蒙住他们的眼睛,我弓下腰,用尾巴卷起我的女孩,送到我的背上,扬长而去,背后是衬托我的英雄气概的一路烟尘。
可是我不是狮子,我只能呆在路边远远地欣赏我的女孩,我只是一个穷苦的学生,脑袋里装满臆想,眼前也没有出现打架的场面,因此我也没有出头的理由。我只能跟着他们,看着他们走进校门,接着我进去,接着保安将大门关死。男生把她送到宿舍门前,便分散而去。剩下我无处可去,望着女生宿舍一格一格地灭了灯。
这一夜,我相信,我追寻的不是子虚乌有,而是一个确凿的女孩;她不是我饥饿时的幻想,而是住在大学宿舍里的真实女生,她是我有生以来最渴望拥有的事物,她的存在可以抚慰我冰冷的心灵。
第二天中午,在大学食堂二楼的走廊上,我再次看到了她。她穿着一件粉色的长裙,站在走廊的尽头,手中端着一只白色的塑料快餐盒,阵阵微风,吹动她的裙摆,形成漂亮的弧线。她看着远处的操场,眼神纯洁无瑕,她那精致的下颌,她那光洁的额头,处处都可以把我的灵魂击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试图走到她身边,问她是否记得我,是否记得超市里的追逐,可是我已不能自拔,我的双脚粘在水泥地板上不听使唤,另一股力量控制着我的头,向她倾斜,导致我的上身倒下去,饭盒中的米饭撒了一地,勺子滑到了她的双脚之间。我相信这是世间最滑稽的一幕,我想从地上爬起来,试图赶紧撤离现场,又恐在她心中留下永远的笑柄。
她捡起我的勺子递给我。我知道,一个男人对自己心爱的陌生女人说第一句话是最难的,他想让这句话成为一辈子的经典,可是事到临头却不会说了。
“哦,我的勺子,谢谢你。”我说。
“这么平的地也会摔跤啊。”她说,声音如绸缎滑过云彩。
“美……美女恐惧症。”我说出这句话时脸顿时变得紫红,因为我是不适合说这样的话的,像我这样穿着破衣烂衫过着糟糠生活的人,从来不会说“漂亮、哇塞、昂贵、酷毙了”之类的话,如果说了,我会一天都感觉嘴里含着沙子,而此时此刻我竟说了这样一个词。
“见了美女就朝拜啊。”她说。
“只有见了你才会这样。”我说。
“啊,你是……”她终于认出我来了,我没有白活在这个世上,至少我曾飘浮在她的大脑皮层没有被她彻底地赶走。
“是,我是。”我多想告诉她我一直在找她,我一直想跟她说话,我一直想进入她的生活,我一直把我的全部出卖给她。
“起来吧。”原来我一直还趴在地上呢。
和她一起走下楼梯,和她一起走过一排白玉兰树,世界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一切变得那么自然,仿佛我也走进有钱长得帅的男生的行列,可以从容地和她做朋友。可是当她和我说“拜拜”之后,我立即进入自惭形秽的行列,我的十五元一条的牛仔裤上还沾着一些米粒,我立即想到我还没有吃饭,可是我一点不饿,我相信爱情可以战胜饥饿。身上的米粒还没等我去拍它,就兴奋地弹跳起来,飞舞起来,在天空中形成流星雨的形状,形成白玉兰花的形状,形成五线谱乐符的形状,就像Widows media player中的音乐可视化效果一样千变万化。
和她一起过的那段路,我永远记得,我感觉就像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远处有美丽的极光在欢迎我。在路上,我的勺子在饭盒里不停地跳动,叮叮当当,因为我的手在发抖。
“你不要告诉我你姓什么,我猜猜你的姓好吗?”我说。
“猜吧。”
“姓丁。”
“不对。”
“姓于”
“错了。”
“姓宁。”
“对了。”
“你真的姓宁啊?”我说。
“我姓丁,一开始你就猜对了。你是不是知道我的名字?”她说。
“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