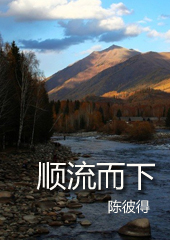顺流而下-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暴躁的重低音都让我能感觉到地板的颤动,拥挤的舞场,快速明灭的灯光,时出时没的变色面孔,让我极不适应。我诧异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角落,人们沉醉于震耳欲聋的音乐中,手脚晃来晃去,就像在从身上撕肉,然后再把成片的肉抛给别人。不知道谁把我拉了一把,我就进入了人肉森林,盘根错节的胳膊和腿阻挠着我,我只能捂着胸口蹭来蹭去。我笨拙的样子很快引起注意,直到我被挤到了胖子面前,胖子朝我挤眉弄眼,指了指丁丁所在的位置,还故意用大屁股顶我一下,我碰到了一位金黄色头发的女生,女生随着节奏猛一回头,你有病啊,接着把我推了一把,场子顿时乱了,浸淫在狂躁节奏里人把我当成水球抛来抛去,最后把我抛给了丁丁。
我无法接受这种局面,面前随着强光闪现的丁丁不是我往常眼中的样子,她穿着一件银白色的七分裤,一件印着甜美花朵的苏绣衬衫在腰口打着结,双手在身体两侧梦幻般地摇摆,微闭着眼睛完全沉浸于热舞之中。她对面,一位穿着黑色紧身裤子和T恤的貌似马龙&;#8226;白兰度的男生,以同样的姿势迎合着她,他大睁着眼睛盯着丁丁时而露出的肚脐。如同我是一根碍事的木桩,他照例用摇动的身体把我撞开,差点倒了。丁丁伸手把我拉住,我几乎贴着脸和她站到一起,立即闻到一股隐秘的香味,接着音乐停了,换成一种缓慢的节奏,就像缓坡上的溪水。
我意想不到的是,这首音乐就像专门献给丁丁的,人群散到四周,露出舞厅中央的平地,中央站着丁丁、我、我身后那个貌似马龙&;#8226;白兰度的男生。丁丁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腰上,把双手放在我的右肩和左手,随着音乐的节奏推动我。我不知道该怎样走,急促地挪动着脚步。
“是我为你点的这首曲子,是我要求老板通知他们散开的,你应该跟我跳的!”背后那个男生叫道。
丁丁仿佛没有听到,她浅笑微微地看着我,周围是吃吃的笑声,伴随着尖叫声和千夫所指的姿势。我脑中一团乱麻,应对环境、担虑背后的马龙&;#8226;白兰度、感恩、激动、指挥舞步、体味丁丁柔软的身体,我觉得我是不适合公众生活的,我的茧会被公众狠心地撕下来,露出白白的蚕一样的皮肤,让我对自己产生恐惧。我心中狂喊不能丢脸,学会适应丁丁的舞步,慢慢地身体变得平衡、轻盈,托着丁丁的腰肢,就像云中漫步。
第十四章
我真希望我是太平洋中的一条小鱼,无头无脑地游来游去,不需要任何期冀。可是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被称作做“鱼”的人,我希望尽早游到彼岸。
岛上的生活如梦似幻,那个姑娘和我相依为命,共同捉鱼,烤鱼,共同到溶洞打水,当我在海水中锻炼肢体的时候,她就坐在岩石上等我。我感觉她就像丁丁投射的影子,如果生活可以继续的话,也许我也可以和真实的丁丁一起享受这种生活方式。
我始终不能决定脱去她的衣服,我倒不是怕她冷,我怕我看到她毛衣下的形状,会让我的裸体不能适应自然。由于爱着丁丁,纵使让这个姑娘观察我的裸体,我也不会轻易崛起。后来,她愤怒了,就像她不情愿我无形的手护着她的钮扣一样,她把外套脱了,扔到一边。
“我要你帮助我,”她说,“我本来不想自己脱的。”
我不言语。她又脱掉羊毛衫,当羊毛衫的下围移到下巴时,她胸前的两个小山丘在米黄的棉内衣上勾勒出半圆形的轮廓,我感觉一股热气向我龚来。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脱了。
“我们是在梦里,我们是已经死过的人,我们不再有活人的忌讳。”她说。
如果我想说话的话,我一定会和她争论这不是梦,是现实,是我的逃亡路上的一段休憩,我不想让我逃亡的意义丧失在她的石榴裙下。我过去抓住她的手,不让她再脱了,我已经看到的她的颈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抚摸着她的脖子,让那层鸡皮疙瘩消下去。她迷惘地看着我,眼中噙着泪水。
“你只是一条鱼啊,为什么这样恐慌?”她扑到我身上,试图把头埋进我的胸大肌里。我挪挪了位置,不让身体中间的杵物压到她的腿上。我盯着远处的海面,心里想,不能冲动,不能转移精神上对丁丁的关注,这就是岛上的规则。
她的泪水浸湿了我胸前的肌肉,似乎想把前世残留的泪水全部喷出来,只留下一个纯净的梦。她抬起头来,开心地笑着,仿佛只要哭过一场,一切都会好起来。她在岛上弹腿跳着,大概是一种健美操,我真想呼唤海鸥全都飞到她身边为她伴舞,那一定是梦中才有的美景。
“我也会变得像你一样的,和自然融为一体!”她边运动边喊。
我希望我一眨眼的工夫她就会消失。我将专门锻炼水性,尽早回到那块广袤的土地,开始我新的旅程。我再次扎入水中,潜到百米外的地方,然后仰身随波逐流。面朝深蓝色的天空,我感觉不到时光的存在,我想时光大约是存在于人群之中,如果你不在意时光的存在,总有另外一个人会提醒你。
我再次回到岸上,那个姑娘已经把上衣也脱掉了,她蹲在地上哭泣,胳膊环抱着胸部,海风阵阵,她薄薄的皮肤渗透出血液的颜色,她一定很冷。看到我,她抬起头说,“去了那么久,我以为你再不也回来了呢。”
我最担心她站起来扑向我,我将难以决定是否闪开。“一个人做梦真没意思啊,你游了那么远,都看不见你了。”她说。她果真站起来,细高挑的身体上两个圆圆的肉球特别醒目,在岛上我培养的自由、淡定的性格差点毁在了这一刻。
“抱着我,抱着我。”她说。我记得劳伦斯死前曾这样说过。她的乳房压在我的胸脯,我仍坚持心中无物。“你为什么总是躲我,在梦中还要保持生前的样子,真是太傻了。”她躺在我怀里开始教训我,“把一切教条都抛掉吧,把一切理论都扔了吧,让你自己成为你自己,你是一条有欲望的鱼啊,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让我感到我还悲惨地活在世上。你看周围的云彩,天空,海鸟,都不像真的,这是幻境,让我们一起纵情欢乐吧。”
我何尝不想纵情欢乐,我曾经以为这个想法是人生的奢侈,被贫穷、懦弱、道德、思想所困,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找一点精神的愉悦,在世界划给我的一小圈土地上创造些奇迹。其实人生并没有奇迹。奇迹只是扭曲性格的想法,是城市的语言,在简单的生活中是不需要的。可是我的头脑已打上了爱丁丁的烙印,如果我有背叛的意识,那个圆圆的黑色的烙印就会跳出火光,烧得通红,整个头脑就会灼痛不已。丁丁是我生存的意义,我一直这样认为。面前的女孩是什么,只是来破坏我的意义的罗刹女罢了。我的思想急速地混乱地思考着这一切,而忘记了身体的存在,当我去看她淘气的面孔时,发现身体还是放松的,而没有硬挺着,便放下心来。
我开始教她适应自然,让她做各种运动。动是让身体祛除不适的惟一办法,动是削弱恐惧意识的最好办法。如果我必须去死的话,我一定在一个动作的未完成式中实现这个结果,而不会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搀扶;如果我必须被枪毙的话,我一定要跳起来迎接枪子儿,而不是在跪在地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我拉着她的手环绕着岛屿奔跑,惊起鸥鹭无数。飞舞的头发,光亮的裸体,开放的心灵,终究没有陷于欲念之中。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一株粗大的榕树上搭了一间屋子,让她睡在上面,我在树下睡。我想我的爱情从来没有经受考验,也许她就是丁丁指派来考验我的。我必须经受住这个考验。世界在我闭上眼皮的时刻化了,四处都是流淌的熔岩,只剩下冥空中一个判断说,空无。
第二天她从树上爬下来的时候,抛掉了所有的衣服。从她腰间的细处来看,上下截然不同,上边一半被昨天的日光晒成青铜色,下边一半是如海上明月般洁白。
“鱼,”她叫在一边练功的我,“我已经明白了,冷只是我心中的一个想法,现在我不觉得冷了。”
动物欲望也只是我心中一个想法罢了,我没有那个想法,当两个裸体相处时便不会有羞耻了。我想世界上应该有那么一座大学,如某处的裸体海滩一样,教授裸体授书,学生裸体上课,礼堂里裸体的观众欣赏裸体的舞蹈,我在那里读书就不会有差异感了。也许不呢,皮肤白的会笑话皮肤黑的,乳房饱满的会笑话平胸的,老二大的会笑话老二小的,总之只要是人类群居之处,就会有耻笑,就会有骄横,就会有耻辱,就会有自卑,我只是一个曾经在大学里穿着衣服依然自卑的可怜人罢了。
如果不是曾经拥有一份纯真的爱情,我真把这里当成创世纪了。一对裸体的男女,穿棱于山林和鸥群之间,采摘干果,捡海螺,捉鱼,烧火,然后孕育子女,子女结合,然后再孕育子女,子女多了有人开始制订规则,树立道德,有人要出海,有人要做岛主,出海的和岛上的反目为仇,便暴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战争,后来世界被分成一个个国家,每个国家制订自己的规则,建立自己的防备,时而为敌,时而为友,用军备和经济相互制衡,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观念,永无休止的私欲,永远不能统一为一个世界。
我决不能沉迷于她的诱惑之中,她只是一个节奏缓慢的脱衣女郎,想把我拉进万劫不复的欲坑。我也不能重蹈创世纪的覆辙,和她结合,滋生一个不平等的世界。
“鱼,我漂亮吗?”她问我,我停下手中的动作,看着她,她真的很漂亮,腿儿细长,皮肤圆润,乳房弯挺,香甜瓜果般的脸,明亮的眸子。我翘起大拇指。
随着日常的锻炼,我逐渐可以紧贴她的身体而不会欲望膨胀,我们就像兄弟一样生活在这座仙岛上,她也不再设法诱我关注她的身体。后来,她也不再说话,逐渐变得和我一样,我有时觉得她就是我,如同我的肋骨和肉组成的幻像,是出来方便我观察我自己的。她和我形影不离,逐渐也学会潜入水中,和我并肩游。
有一天,我非常兴奋,我决定游回彼岸。她也非常兴奋,我看见我的笑容出现她的脸上,她的脸很快长出胡子,我就拉着她的胡子和我的胡子系在一起,跳入水中。我们拼命游,向着那个有灯塔的岛。身后的岛越来越远,灯塔越来越近,我的胳膊越来越酸痛,希望越来越大,就像前面的岛。最后我们借助一股海浪的冲劲,奋力游到岸上。我们躺在沙滩上看着互相看着,大喘着气,我感觉我是那么的爱她,就像爱丁丁一样地爱她。她陪着我度过了岛上的日日夜夜,她从不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只是把我当做鱼。我笑起来,她也笑起来,我郑重其事地吻了她。我们拥有海豹一样的身体,在沙滩上滚来滚去,来庆祝这场伟大的游泳。我真想我们都变成海豹,双双再次潜入大海。
也许冬天已经来了,海边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挽着手在岛上走来走去,最后登上山岗的顶部,我们看到更多的相近的岛屿,层层铺开,仿佛一群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