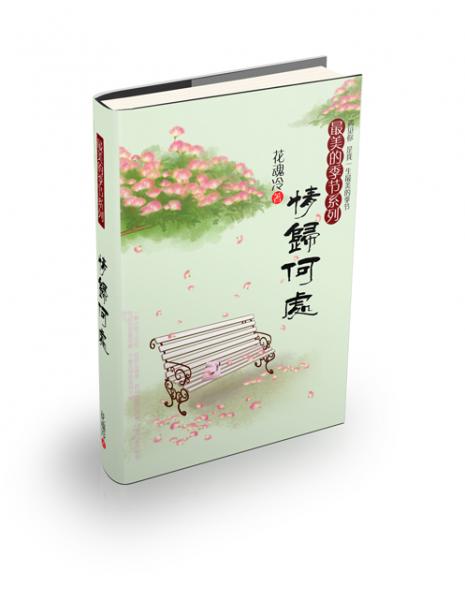堕落的季节--80后阿飞的那些往事-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一夜一直没有看见阿婵的身影,我一直留意,一直等待着她熟悉的身影的到来,最后依然只是等得一丝丝心酸。
回家已经是在学校度过两个日夜的时候。母亲很是担心,父亲却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父亲一向如此,对于我们的事,仿佛他都不会太多的留心和在意。但是,如果要开家长会之类的,父亲决计不会错过,即使稻苗都弄到田里了,他也会放弃干活,准时到学校开家长会的。如若得知是好表现,回来就一声不吭地乐呵呵地扛了农具干活去了;若或得知是坏表现,回家先是抽一阵烟,而后沏杯茶,把你叫到身边,也不骂,也不打,只是问问最近的心情和想法,末了语重心长地讲些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而后告诫到:“一切要靠自己,知道吗?父母亲不可能一辈子把你绑在裤带上。”,一边喝茶。
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身边:“你叔父来信了,看看吧!”
心里一喜,叔父到南方某报社任职后,很少给家里写信了,我忙接过信,信的大意是对我的中考成绩表示祝贺,还有就是带了点钱回来。
吃过晚饭,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徐志摩诗选》,忽然想起了叔父的那封信,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仿佛千言万语堵塞着,不吐不快。于是,取来笔和纸,仿照叔父的语调,写了封回信。信里只字片言而已:
叔父:
近念,问安!
来信及款俱收,先谢!本想此次你会躬亲莅临,甚是失望。窃以为少了点钱之外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又说不上来。
后祝
工作身体俱进
侄儿:阿飞
年月日
父亲东挪西凑,凡是能榨出油水的东西,哪怕是跳蚤身上抽筋,终于勉强凑足了上学需要的对我们来说简直天文数字般的学费。
临行前一晚,母亲特意从鸡窝里取了最后的几个作为母蛋的鸡蛋。
“这几个鸡蛋特意留给你在路上吃的,你爸爸准备弄去卖呢,我执意给你留的。”
母亲笑着,慈祥地看着我。
“哎,妈没有能力,没文化,总让你们兄弟吃苦。”母亲一边把蛋放进锅里煮,一边摇着头缓缓地说到。
我心里一紧,想想要离开父母亲,自己照顾自己了,想想自己以前的不孝与作为,越想心里就越见疼了。见母亲要扭头了,忙擦了擦眼泪。
“谢谢你,妈。”
“到学校以后要与同学们好好相处,都是有缘嘛,才走到一块儿。不要老任着性子,动不动看不惯人,爱理不理人家。还有,要经常洗脚,就那懒劲儿,脚都不爱洗。”母亲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说。
该死的泪水,又跳出了眼眶。
“爸呢?”我勉强着不让泪水流下来。
母亲正替我收拾衣物和行李,顺便也把那几个鸡蛋放进了包里。
“谁知道。或许,搞工作去了吧。”
“村干部的事很多吗?重要得很吗?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爸就这性子,甭管他,也别恨他。你越恨他,他越得意呢。早点儿睡吧,明早我煮熟了饭叫你。”
“嗯。”
我第一次这么听话地上楼去睡觉了。总睡不着,莫名其妙地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弟弟买的明星像贴在对面墙上,看了却让人有些烦。还有阿婵,毕业晚会她怎么没有参加呢,有什么事呢?……
“小飞,小飞……”睡梦中,模模糊糊地听见有人低缓地叫我。我一骨碌爬起来,以为是班主任来“叫”我上课呢。睁开眼,是母亲,她正看着我,一脸慈祥地站在床前。
“昨晚睡得不好吗?”母亲问。
“叫爸跟我一起到学校报名吧。”我说。
“你爸一早就出门了,说村里有急事要处理,叫你到学校以后好好学习,好好表现。”母亲坐到床沿上,抚摸着我的头说:“早饭已经熟了,起床吧,进刚在等你一起去学校呢。”
走了,坐在车里向送别的母亲挥了挥手就走了,带着村人的祝福与希冀,揣着父母的沉甸甸的爱,到S师范学校去实现自己的教师梦了。父亲终究没有来,母亲仿佛站了很久很久,即使车子拐了七八个弯,我依然能感觉母亲的身影在身后站着,望着车,一脸祈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思想
失去目标的人生,是一片浸透着悲哀与痛苦的浮云。初中时的我至少还有阿婵,但是阿婵离开了。我在S师范学校的日子,不知道算不算还活着,总之,每一天都是混混沌沌地过着,机械地麻木地重复着相同的单调的生活。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却连钟都没有撞好,算不得一个和尚了。在我心里,村人的祝福与希冀,父母亲沉甸甸的爱,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化成了惰逸的另一种理由,变了质,成了抹灭的粉笔字。
“喂,阿飞,又梦游黄山去了,还是到杭州看美女去了?”同桌流年轻轻地推了推我,在我耳边轻声喊道:“班主任正看着你呢!”
惊魂过来,望望四周,同学们都专心致志地,有的托腮聆听,有的奋笔疾书,甚是安静,班主任在讲台上“哇啦啦”讲着《师德常识》,偶尔用极为难看的粉笔字板书着什么,偶尔又用极为无奈的眼光看着我。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按按太阳穴,摇摇沉重的脑袋:“几点了,要下课了吧?”问流年。
“还有两分钟。”流年看了看挂在胸前的心形表:“昨天你写的诗我看过了,超级棒!不过,我是看不懂了。”
流年是我在S师范的至交,拜过天地的那种。经济上的窘迫常常都是他帮我度过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小的人情。
流年是外县人,父亲是某地的父母官,家里很有钱。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百来块,他却又六七百块,于是我的吃喝玩乐都得靠他。
流年是自费生,于学校开设的课程来说,除了语文还知道点皮毛外,就只晓得一加一之类的问题了,每学期都要准备至少五六科补考的费用。于是在学习上我都是极力地帮助他。他唯一的嗜好是打麻将或者玩扑克,而我则喜欢文学,偶尔学鸦几句诗歌。
但是,我们确实算得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铁哥们,好兄弟,感情笃厚。
我每次写的东西,都要让流年先睹为快,即使他狗屁不懂。
昨天我写的诗叫《飘絮》:
抚慰过折翅的蜻蜓
拖着长长的秀发
深情的秀发
微风毕剥着柳枝的纯寂
心如止水的柳枝呵
被煦阳吻红了脸般
飘絮如舞
拂过心湖
溅起涟漪
微风
柳枝
柳枝
微风
不知是风在舞
还是柳在飞
我不知道这是我在S师范里写的第几首诗了。对于在S师范学校里的生活我曾经这样描述自己:
这里是个鸟笼,我以为。只有军训的半月生活还过得充实而愉快,苦中有乐。我第一次领教了封闭式军事化管理的妙处:被禁锢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书香圣地,少了外面的污浊空气。严厉的老师,严格的纪律,稍有不留神就会有被通报、罚款等之类的厄运降临。学校谓之为:处处无小事。长此以往,一个人难免就会植物人似的照章行事,万事求个条条框框了,如此的结果当然就是造就“听话”的公民。
这里每天都是玩。上课玩,下课也玩,却又毫无自由,不能痛快地玩,我不知道怎样描述这种感觉,总之无聊得紧。
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的东西:怎样穿得体面,怎样去玩,怎样才是“懒”,怎样打扫卫生,怎样应付查夜;除了军训里学到的走正步、叠被子、衣物放整齐之类的外。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点不算什么的东西。我常常想,幸好上天给了我这一点点天赋,可以让我玩玩文字游戏,打发打发时间,倾述倾述心绪。
在S师范里,我只是一纸飘摇在半空的废纸,漫无目的地生活着,极其无聊地学习着,空虚混沌地思想着。又是那么的脆弱,稍有不小心就会从半空中跌入垃圾堆里,身心被撕得粉碎。
于是,我飘忽无聊地做着自己以前从不敢做的傻事,堕落犹如一张魔网,又如一张天网,注定会姗姗而降,扼紧我的身心,让我无力挣扎,任其放肆。
夜晚,有月,是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学生会巡夜的恐怕也早与庄公一样做着似蝶似己的梦了。
我和流年猫着身子,轻车熟路地越过栏杆,爬上围墙,然后,大侠般从十几米高的围墙上一跃而下,回过头朝围墙里已经亲密接触了一年多的校园来个飞吻,就兴冲冲地融入这城市里黑暗的夜色了。
“去哪里玩呢?”问流年。
“跟我走吧!”
“搞什么啊,还跟我玩神秘?”
“逛窑子,去过吗?”流年突然拉着我的衣领,看着我的眼睛说。
妈的,混蛋。望着流年那矮胖如冬瓜的身影,啐一口,心里骂道:这么污秽的事,岂不坏了我这童男贞操。
“说啊,玩过没有?”流年那长有还算端正的五官的憨厚而可爱的脸庞突然靠近我的脸。
“随便,听你的。”我耸耸肩,凝视着他那双还算清澈的眼。
说真的,我看过不少的所谓A片,但那是雾里看花,画饼充饥,其实心里早就有点迫不及待了。
我们漫无目的地踱着懒步。这城市的夜景或许很美,但可惜的是,我们都庸俗得不去欣赏,不懂得欣赏。我们一步步地丈量着每一条街,一口口地吮吸着污浊的有些臭味的空气。
流年一直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着。着城市真的在此刻显得那么的熟悉而陌生,熟悉的是有几条街,有几个巷道;陌生的是到底哪里才有“窑子”。流年就是恼怒这种陌生,他在极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熟悉这座城市。
我仿佛是一只哈巴狗,一步不离地跟着流年茫然地移动着双脚。此时的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当时有月无星的天空,高高远远的空凉得让人有些害怕,月光却甚是皎洁,照得能看见流年的每一根头发丝。
走到一处,流年突然停住了脚步。是*,一块硕大的霓虹招牌用颇有些创意的美术字写着“×××*”五个大字,竖立在门面的左上方。门面周围布置着许多彩灯,直挂到第二层楼,五颜六色,忽亮忽熄。门关着,里面亮着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偶尔听见门里传来一阵女子的嬉笑声。
“你进去看看。”流年说,对着我。
“我口笨,还是你去。”
“还是你去。”
“……”
其实,我想去,只是没有勇气走进那道门,我不知道该怎样打交道,我说不出口。我是第一次在这种地方徘徊,心里像抽成了真空,被某种东西压缩得拉紧了每一个细胞,好生害怕和紧张。
后来,我们谁也没有勇气走进那道门,只是一步三回头地有些留恋有些遗憾有些不甘心地又继续闲逛了。
告别童男
流年在一家旅社前停住了脚步,那旅社的霓虹招牌齐楼高,招牌上写着“××旅社”几个硕大的字,我们在踌躇半天后,终于作了重大决定,鼓足勇气走进了旅社大门。
“老板,开间房,双人间,标间。”流年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