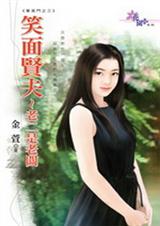�������ϱ���-��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ڡ�ˮ䰴���ʽ��һ���������ް�Ҳ��ҡҡ�ģ�������ô������ν֮������������������Ի�ܲ��ˣ����ְ��ý���֮�£�Ѱ���գ�Ū��һ����Ϳ�ա�
��������ģ����Ӳ��߱ʼǡ���������÷��б��61����1922������ij�������ʱ��ס��������һ������������˳�������լԺ����ʱ�С�����������ݡ���λ�ھ���ǰ���⡣��ʱ�����Ļ�վ����ǰ�Ÿ��������ԣ��������һ���ܹ����������������ѵij������������������С�����������ΰ�ġ�
������������ʱ���Ұ��������ѵij����������������ҷ���������ΰ���Ҳ�ѱ��Ұ�ģ�������Щ�����������IJ���֪����Զ��ã�г�ȥ�����ⲻ���ǿ����į�Ŀ�Ԣ��һ�ּ��а��ˣ�������ͬ������缦�����Ľ�����ȣ����˵�Ȥζ��������ȫ��ͬ�ˡ�
�������ڿ�Ԣ�д��������й�һ�ذ�ҹ�ﱻ�������ѵ����顣���ڰ�������˵糵��¡¡�����⣬���ǰ������������������ĸ���µ�ʱ����������Ҳû�������������������ı�������ס���˼��Dz������ġ�Ȼ��������֪������²��Dz��Եġ�ÿ�α���ʶ���������������������Ӽ�������Ѭ����һ������ơ��ҵ����г�ȥ��ʱ�����ܿ���С̯���±��������ȷҲ�ֻ���һЩ�����ʡ�ë���ļ���������ͬ���ӣ���������վ��ȴû������������֮���Բ��ܽУ����߲����Dz���У�ֻ��ʱʱ�������£������Ƿ����ĵ����й���ˮ���dz�����ѽе����鶼�����˰ɣ�
����Ȼ���һ��в����ߣ������ļ�����Ȼ�����������Ǿ��У��ѵ���ط��ļ����Ͳ���������ģ�Ϊʲô��ĵط��ļ��������������Ը߸����أ�
�������������ɽ�������������ҡ���ν���������ҡ���������һ��˵��������������������೮���ɹ������֮�����������ǣ�������ɹ��������뾩��ֵ����ʳ���Я֮ȥ��Ի�������ҡ���������������Ӷ�֮��ƽ������������Ϊ��֭��մ妣����쾡�£�����ϧҲ����
�����������ߣ�������Ҳ���������ģ�ֽ���ģ����ֶ��С�һ�����ţ����Ǿͻ���������������������������������ʹ���ǽ��������ε�˿���ġ������֣���Щ�ط�ӲҪ�ѡ���������������Ҳ�������п����еġ�����һ�������DZ������������̵Ļ���ȡ�������ɽ����Ȼ��ʹ������͡��������ҡ��ġ�������ˣ����ǻ��ǰ�����ֽ���������εĻ����ϻ��εĻ�������ͷ����ǰ���������������һ���Ļ��£���һ��컨���±�һ����緣����顰��ɽ����������ҡ����֡�
�������������ҡ�Ҳ��һ�ֿںţ�������ɽʱ���á��ϡ�һ������ɽʱ��ͬ·�߾ͻ��á��������ҡ�����ʹ��ɽ·�����ŵ���ؤ�ǣ���ɽʱ���㡰�ϵ���ү̫̫������ɽʱ�ͽ��㡰�������ҵ���ү̫̫���ˡ�
�����︣��������������
���������������������ˡ�
����������̨�Ժ��Żţ����������ߵļ���*����ͣ�˺��������������ı��ⱱ�������ε�������������������վ������վ��ʼ�����������ʮ���꣨1901����ԭַλ���������ͳǶ��ࣨ���ϳ�վ�̳��������Ļ������ڵأ����ɳơ�������·�����Ŷ���վ����������ʷ�ظ������ǰ��վ������վ����ƽվ����ƽ��վ��վ�����������ᵽ�ġ�һƬ��ɫ��Զ��ש���ij�¥���֣������ߺ�ǽ�ij�¥��������ɫ�IJ����У����ܱ�����������ţ������Ͻ�������һ�С�������1925��ʱ������·��������վ�����ķ羰���顡��������txtС˵�ϴ�����
����������5��
һƬ��ɫ��Զ��ש���ij�¥���֣������ߺ�ǽ�ij�¥��������ɫ�IJ����У����ܱ�����������ţ������Ͻ�������һ�С�
���������뾩ʱ�����������űߣ��������˵������ñ�����ΰ���Һܲ������Ƶ����������꣬���ڣ����ҵ��ֵ�հ�������Ⱦ�����ˡ�
���������˻���У����������������ĺ����У�������ϸ��Ʈ��ѩ����������ڸ�ȫԺ��������չ��ï�ܵ�֦Ҷȱ��©����������������ɫ��б�ߣ�����ʪ�����̻����ĵ��ϣ����µ���������״�İ��ơ��������ˬ����������չ���ӳ�ճ�������Ͷ�����������ı�����
��������Ժ������ŵǰ�����˹��ɽ�����������ں�嫵�ӡ����Ȼ���Ҳ��ܶ������ǵĺô�����������˹ɽ�ij����ӡ����֮Զ��Զ���ڱ����ǡ�����������ġ�Ȼ���Ҳ������Ǽ����˶Ա����ǵij���������Ľ����Ŭ����Ѱ�����ϵ���Щ���ģ��������ң����Ƕ��ģ��������������ϱ���ij�������������Ҳ���������������Ǹ����Ը���ɫ�����֡������ȫ���ǻ�����̫��̫�࣬������Ҳ�ͱ�ɱ��߶��������ˡ���ʵ�ϣ������ҽӴ������������ֺܶ࣬��������Ҳ���Ҹ�ĸ�����¡���ʱ���Ƕ��ǡ�������ƽ���´��ļ��ߣ������ڹ���������Ҫ��֮�䣬��д���ϱ������ײ��ɫ���о�����������ǵ�ʱ��ͳ��һ�ź���Ӱ��ı�ֽ������1947�ꡢ1948������Χ��ʱ�ڣ�����������Ҫ�ľ��¡�������Ϣ����Ҫ���Ҹ���������ԯ�μ���ͻᣬȻ���ɡ�����������ȥ����Ϊ��������ҵ�Ѳ��������Լ��ġ������ձ����ˡ������Ҹ���д�������о���̬��Ҳ�ͱ��������е�һЩ������
������ӯ���������ǡ������ǡ�
������ƽ��һ������֪������ʷ���ǣ����֡��ܽ������ˣ�����������ʱ�������Dz���˵�����ܽ����Ƿ��䡱��Ҫͳһ��Ҫ��ɢ�����������������ö��ˣ��ܽ�����û������������ijЩ���������Լ����սʤ������Ϊ�ܽ�����Ҫ���䣬��Ҷ�����������������Ǹ��Ե��ң�ǣ�ƶִ࣬�е��٣�����࣬�������١��ֱ��ɾֲ����������������ף����˹���������Ħ�����ҳ���һ�š�����������£����²��ܽ��������˵Ļ�����վ���ص���ˮ�࣬����㱻���а˿飬��Ҳƴ�ղ���������ƽ�ܽ���Ļ��ң�������ȫ��������е������
������ƽ����һ������¯���˿��̳�������ʹ�˸е�Ŀ���ĺ�������Χ�ų��У���������������ʮԪһ�������ߴ�������ʮԪ����������ʳ����Ա�ϵ�ʱ���˵����ġ�����ƽ��ֿ⡱���������������Э�ᡱ����������ͨ��ʳ����������������������ϡ������ѱ��˽���һ�ա����貿����Աȴ���վ��ò�Ӧ�����յ��Ĺ�ҵ�Թ����裬��������ȴ������ũ�ֲ�����ҵ�Ľ��ᣬ��Ϊ���������Щ�������ϣ������ϵ����Ļ������������������ֽ�⡢��ī���Ͳ��ϲֿ⡣�ر�����Щ��ǹ���ˣ��ò������ĵİ��´����壬�������ӣ����Ӹ��˲Ƹ���ʹ���ٲֿ��ÿտ���Ҳ�����ǽ�����Ա֮�乷ҧ����Ц�������ض�����ʹ�ǡ������롢�����룬�������˸����ꡱ�ı�ƽ�����Ц���ú����ġ�����������һƪ��ĸ�����£���Ҳ�ǡ������ļ��ߣ����ıʸ�����ѧɫ�ʡ���д�����������������߲�*��ʿ����д�����졢��ƽ����ɫɫ���ϰ��ա������������ֽ���ʼ�ú��磬����������ȴ��ʮ��֮���1946�ꡣ��������ʱһ����ƽ�������Ҹ���ȥ������˿ա����ڶ�����ȥ�������ڼ�����
����������6��
���Ӹԣ���������ڱ�ƽ��1946���ģ�����Ĵ���������ص���ƽ�������ڱ����ν̣���ס�ھ���У����Զ��ɳ̲���Ϻ�ͬ�Ľ������������ס������Ļ������DZ���ܱ��ա����õȽ��ڡ����DZ��Ů�������ͯ���Ӽǣ���¼����ζ��ݵĿ���ʱ�⣺����������п������Ǹ���������ͬԺ������ġ����롢��������ռԪ��ס��ի�ij�����dz��͡�����̸��ѧ��ʫ�裬�����֡���
��������8��29�գ���ƽ����Ļƻ裬���Ϲ���̯�ϸ���ɫ���������˻��һ��壬���ƺ��Ѿ��ŵ����������ӵ���ζ�ˡ���ƽ����ѧ�ĸ�ԭ�����˸�ɫ������ѧ�߽������ˣ��Լ���Ծ��֪ʶ���ꡣ��ƽ���Ļ���Ϣ��ȻŨ��ɫ��Ҳ��Ȼ�����ḻ��������Ļ����´�����һɫ��������Ϣ������
���������������ڷ����������ɸ壬����������ӯ����˵���������ǡ�����
�����������֣��������ʦ�������ִ��������
����������д�˷���Ҫ�ĸ��㣡�������˷��Ÿ���˵����ʮ�겻���绰����֪����ô������ͬʱҲ����ʮ������͵��ˡ���
��������ռ���������е��������ӣ����˱�ֻ�����ڸ��˰ױ�������һ����ë̺�Ĵ��ϡ��е����⣬��ô������С��һ���ˣ�д��80�����顣�������⣬�ĸ����˸����������������ͳһ�ģ���ȫ�ް������˵ĺ�����ȴ�е����һ��ɡ��������ǡ��е������̾�Ӧ�����⸱���ӡ��±�ɾ����ʮһ����Ȼ�Σ�������С�����£��ɡ��䱱ƽ��Ҳ���Կ�������ʱ�ֵ����ǣ���������ʱ�ֵ�֢������Ǹ����ң������ң�����ҷ���ɵ��˵�˺�Ϳ�������������ᵽ����С�����ǣ���Щ���������������ˣ������Ƴ�������������������ڱ��������ա����Ϻ����Ϳ�����ո��ˡ���������Ʒ��
����������ڱ�ƽ�������С��ͬ����һλ�������ߴ�������һ����ɫ��dz��ɫ��ë�ʳ��������İ�С������һ��������������۾�����̯��Ѱ�Ҿ�������������ƺ��룬˵һ�ں��ϡ���ƽ���������۵���ͨ�����DZ�������ġ�����Ը�����������ȥ���������������ҷdz�����������һ�Σ�����Ȧ������ʲô�˿����˶�Ҫ�İ��о������������в�������¶���������Ⱦ���ƺ��˵ġ���ĸ����ƪ����û��ֱ��д����������д��һ��������������˱�������������ҵ��ˡ���ĸ������������̳������λ����ʦ����һλ��Ҷʥ�գ�������λ�dz����Ƶ��Ϻ��ˣ���������أ���ץ�������������ص㡣�������Լ������āD��������д��һ�������������С���ӡ����ġ���Ҳ���߰����֣������Ҷ�Ͼ�������һ��ĸ���ڹ�����������һ��С�ĺ�Ժ����ȥ���ģ��䲻�DZ����ĺ�Ժ��ô�Ͻ�����Ժ�л�ľ���裬�������ġ�Ժ�ӳ���û��ס����*������������½�ķ�ȥ���������������ѷ�������������Э�����ˡ�½�ķ����ﵱȻ��л����������һ�䣬ƽʱҲע���ɨ��רΪҶ�ϵ���Ů����ʱ��ס��½����Ҳ�Ǻܺõģ�������˵�����������ݣ������Ҫ��ס���������Ҳ�ǿ��ŵġ���Ҷ�ϴ�����ʱ�ͺܹ��ĺ�������ҡ���ĸ��Ҳ�������ˣ�ͬʱ����������������ġ���ѧ������־�Ļ������ߡ��Ҹ���Ҳͬʱ�����ߣ�˫���������ʶ�ˣ�����ߵ���һ�����룬����������У�Ҷ�����ٶ���ĸ�����С���磬�Dz�ȡ�˹������ƶ������õġ������ĸ����һλ��ʦ��������ģ�����ʱ������һ�ݸ�ҵ�������桶�����ั����������ĸ��ʱ���и���Ͷ�ĸ������������ĺ�Ѹ�ٿ��ǡ���ĸ���ּ������ϣ�ÿ���ʵ�����Բ�ġ�Ȼ����������ë���ַdz���ء���Сʱ�ڼ��ﻹ����ĸ��ʱͶ���ԭ�壬���ֱʼ���������ţ�ĸ����ؾɸ��Ѿ����ꡣȻ��������������ĸ�ļ��棬ȴ��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