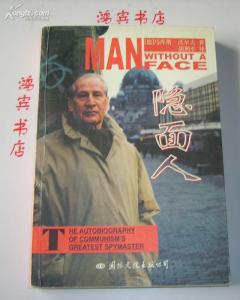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他这么矮胖,秃顶闪闪发光,同电影和画像中的伟大领袖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我先是感到失望,随后又有一种骄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个正常人。所有关于他个人崇拜的传说一定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他本人并不知道,”我想。
我作为临时代办代表大使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坐在前排。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互相祝酒。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讲话时,斯大林一根接一根地抽劲儿很大的弗洛尔牌香烟(一种斯大林喜爱的用俄国烟纸卷成的加长纸烟)。后来,他也亲自祝了几次酒。在一次祝酒时,他赞扬了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团结。然后又举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天重返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在两年前,南斯拉夫极富魅力的领导人铁托拒绝接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求在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巴尔干国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权,南斯拉夫因此被斯大林打入冷宫。我们这些来自对苏联忠贞不渝的国家的人,对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铁托居然敢违抗斯大林的意志!
这位苏联领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圣旨一般令我们诚惶诚恐。在我和大部分来宾的眼里,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中苏分裂毫无察觉。但我还记得,当时心里也曾纳闷:整个晚会,毛泽东一言未发,颇不寻常。我思忖着,这大概就是传说的中国人深不可测的性格吧?
两年的外交生涯中,像这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并不多。一次,使馆内部为庆祝东德成立两周年筹备招待会时起了争执。争执的焦点不是中苏同盟的破裂或是一个叛逆的共产党国家,而是穿什么的问题。大使说该穿燕尾服,以示庄重。而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没有燕尾服,要求允许穿西装。最后达成妥协,穿正式西装,系黑领结。当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把黑领结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拒绝佩戴。虽然我们日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国,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明显地带有其前身普鲁士一丝不苟的遗风。结果那天晚上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这样正式。我们简直狼狈极了。当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克鲁季茨基起身告辞时,我彬彬有礼地陪他走到衣帽间。他的手在宽大的披风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掏出三个卢布,很严肃地交到我手里,算是小费。
1951年8月,我接到紧急指示,要我返回东柏林向阿克曼述职。阿克曼的真名叫哈尼施,是东德的外交部长,也是政治局里屈指可数的战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见了我。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让我在当天午饭后再去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某个房间报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午到了那儿,看到还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我。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安排是因为阿克曼一向强调保密,并主张党政机关分开。其实党政机关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组建一个政治情报机构。上面已确定调我到这个机构工作,担负起使“年轻的祖国耳聪目明”的重任。说得更露骨点,我将成为一个间谍。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没想过这次调动对我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当年党送我上共产国际学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广播电台工作。还是党,派我去莫斯科干外交。如果党认为我适于做情报工作,我绝无二话。党的领导人信任我才派我参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种不讲价钱的纪律性。然而,不理解党对我们的绝对支配权力,不理解党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就根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评价我们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办公大楼外面挂上这块牌子是为了掩护里面的东德刚刚诞生的情报机构。上班伊始,施塔尔曼就带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轿车转了一圈儿。这种型号的轿车在当时十分扎眼。负责创建东德情报组织的施塔尔曼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长者。他的真名叫伊尔纳。由于长期在共产党内从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称呼他,结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国共产党内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1923年当选为德共“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绝少谈及过去。不过,他倒是跟我聊起过他在苏联、英国、中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美国执行任务时的佚闻趣事。西班牙内战时,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称“游击队员理查德”。他还是被纳粹指控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盖世太保前来逮捕季米特洛夫时,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对粗暴的逮捕和审问,他俩始终沉着应对,毫不畏惧。季米特洛夫以后称施塔尔曼是“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由于他的这种老资历,新的东德领导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见。他同他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当组建工作遇到障碍时,他就直接去奥托·格罗提提总理家找他面谈,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问题不外乎是钱和经费的来源。早期我们现金奇缺,捉襟见肘。通过官方渠道申请外汇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偶尔施塔尔曼登门找到财政部长,回来时他那破旧不堪的公文箱里塞满了崭新的钞票。捷克斯洛伐克体谅我们的困难,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送了24辆塔特拉牌小汽车后,施塔尔曼不知用什么法子为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部门搞到了其中的12辆。别看我们办公条件寒酸,出门坐的车却很气派。施塔尔曼懂得,这玩意儿有助于提高我们情报机构在政府中的地位。处处省钱反倒会引起消减预算的人的注意。我们的首次会议是在柏林东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开的。谁也记不得这次开会的日期,也没有保留会议记录。以后我们把1951年9月1日定为东德情报部门的诞生日。此后不久,我们搬到了东柏林潘科夫区从前的一所学校里,距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很近。这一迹象表明,我们已变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们只有八个人,外加四名苏联顾问,包括一名人民内务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叫“格劳尔同志”。格劳尔曾作为一名情报军官在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常围着他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过去的经历:如何挖出鼹鼠,如何打入敌人内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员的英勇事迹。从他那儿,我们学会了如何搭起一个情报机构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等。没想到他以后的结局很惨。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这恐怕是特工这行的职业病,同时也与当时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他和东德情报局的局长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劳尔怀疑阿克曼是间谍。后来,苏联不得不把他调回莫斯科。苏联情报机构的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格劳尔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当年,凭着高度的警惕性,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军官。今天,他却沦为这种警惕性的牺牲品。
我们情报局对内称为经济及科学研究总局。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隐讳,任何知情人一看到“总局”这个字眼立即会联想到克格勃内负责间谍活动的“第一情报总局”。1956年,外国情报局改名为“情报总局”。
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握有决定权。起初,各科科长起草所有工作计划都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而这些顾问依据的是苏联政府部门内的繁文礼节。这些章程之繁琐刻板简直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抄写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外,还要花大量时间把它们装订成活页本。这种办法还是革命前沙皇的秘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没人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也没人对此提出疑问。
我们情报局的结构完全是抄袭苏联模式。工作方针的用语一看便知是从俄语翻过来的。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原子能、化学、电力工程和电子、航空及常规武器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情报,以及有关西方国家的情报,并摸清它们对德国和柏林打的是什么算盘。
情报总局下面有一个人员精干、相对独立的反谍报处,专门对付西方的秘密情报机构并设法打入其中。可它马上与国家安全部发生了冲突,因为安全部下面也有一个负责侦听的司。1953年我们并入安全部后,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谍报部门一直直属安全部。由于各部门之间的倾轧,我们往往对自己部内的情况茫然无知。特别是以后反间谍部门的成员开始跟外国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是被蒙在鼓里。
人们常常不解,为什么莫斯科要组建一个德国情报机构,与苏联自己的情报机构竞争。斯大林正确地估计到,苏联的情报人员很难渗透到战后时期的德国。在当初的德国苏占区内建立一支德国人自己的情报队伍会使我们这些人产生一种荣誉感,从而更符合苏联的利益。一开始,我们把得到的所有情报都转给苏联顾问,甚至包括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个间谍的情况。以后我们逐渐开始保护自己的情报来源,只是有选择地向苏联联络员提供情报。
起先,我在罗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政治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知识,如伊斯兰教,以色列建国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度次大陆上的宗教冲突等。他是一个优秀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不要轻信下面情报人员报上来的材料。没多久,我俩就得出一致结论,仔细阅读报刊杂志往往比看间谍提供的秘密情报更有收获。我们自己的分析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报来源得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才能对搜集到的原始情报的真伪优劣作出判断。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始终受益于这一见解。
科布不仅思想大胆,为人处世也十分洒脱。他谈吐幽默风趣,对在座的听取情况介绍的要人们颇有不敬,而听众却感到津津有味。由于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气扬的达官贵人,我俩于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对。尽管我们也是国家的忠实仆人,却没有像某些政治领导人那样染上传教士般的狂热。
随着人员的急剧膨胀,我们不得不再次搬家,从原地点搬到东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更大的楼里。我很快被提升为新成立的外国情报局副局长。局长古斯塔夫·辛德有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
面对纳粹德国覆灭后几乎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西德情报组织,辛德和我都不知从何人手。当年效命于希特勒的高级情报官员现在又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叫普拉赫的神秘的小村子里为新主子服务。普拉赫这个名字刚开始在报上露面时,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好一会儿。对于敌手,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后来对敌手的情况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