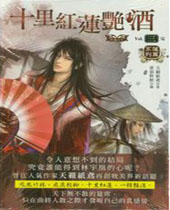十里荒凉 胭脂泪-第7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维晚听了,却是娇面一红,勾下头去:“左护法怎么知得奴家的称号……”
若即也不急,缓缓道:“静女踟蹰,江湖上不知这名号的,怕也是少。只是每每都让冷冷淡淡的另一个给骗去了。”
维晚双颊绯红,含羞带怯说道:“奴家也早便听说了左护法的名声,今日有幸见得真颜,竟是这般少年风流,奴家心下好生欢喜。”
那个欢喜还没有说完,她手上红绡一抖,好似春风拂面,循循而来。
若即抽剑一挡,两相交接,竟是如兵器相碰一般,好大一声响。那红绡毫不示弱,轻柔一摆,尾梢复又席卷过来。
若即将我一抱,纵身跃向林中,只听得身后一声大响,我从他肩膀上望过去,方才我们还站着的那根树枝,被那柔弱无骨的红绡一拍,顿时断散成一堆木屑,从夜空里洋洋洒洒落了下去。
顿时浑身一阵冷,再看若即,双眉依旧平淡地舒着,眼里却神色深深。我闭嘴不言,暗自在心里盘算。
维晚果真起身追来,三丈红绡缠在身上,又向后面夜里飘去,若隐若现,在树林中穿梭翻飞而来,一边娇笑道:“左护法作何走得这般急,千辛万苦来这么一趟,也要让奴家尽尽这地主之谊,否则往后与姐妹说起来,可不要给他们笑话了去。”
若即也笑道:“静女这情谊,若非金刚不坏之身,怕是消受不起。”
他这么一说,我便想起辛垣来,两人倒是相生相克,想起他那张有苦不敢言的脸,忍不住一声笑了出来。
维晚却瞬间变了颜色,眼里精光一闪,面上突然就是无尽的委屈,一双眸子也腾起水雾来:“公子不待见奴家便也罢了,又何必带这么个女子来耻笑与我。”说罢咬唇而立,泫然欲泣,眼中苦楚翻腾,“人人皆道左护法无情,再怎么相亲相好的女子,宫主一令下,也能决绝而去。可人人又道,左护法风流卓绝,极恋胭脂香。本是无情,作何要生这一副多情相貌?”
若即清秀的眉毛压了下来,我知道他是被戳了痛处,抵在他胸前,才要说什么,他却一吻压在我额前,一瞬间将千言万语都泯了去。
突然身后疾风大盛,一抬头,红光几要逼入眼里。若即反袖一卷将我留在树上,纵身跃进去,手上一抖,剑鞘退开去,那剑身印着月,亮得骇人,好似握着一手寒泉。
若即在那妖娆红绡里来去自如,身姿卓绝,翩若惊鸿,矫若游龙,一头青丝未束紧,在夜里扬起,印着星光,一丝一缕的风流动人。
正看得入迷,不觉一道寒光向我而来,若即身影一动,铿然一声大响,我还未反应过来,他便跃身到我面前,挽了一个剑花,就听得乒乒乒几声响,一些闪亮的东西向下坠入夜里。
一切皆是转眼的事情,我才回过神来,见那漫天的红绡散成几段,自半空缓缓飘下,安宁淡远。
维晚捂着胸吐出一口血来,若即冷眼看她道:“我念你一路待小若如礼,又是身世凄苦,才招招留情不下杀手。你若敢再动她一分心思,无情有情不用问也晓得了。”
维晚却不再言笑,只捂着胸口,冷冷看我。
我知她已不是方才那个人,也不知道说什么。
她却一声笑出来,凄烈苍凉,完全不是方才风情:“无似有,有时不知是有,反反复复,终不可求,不可求!”言罢哈哈大笑,笑得吐血不止。
我不解,若即却是面色惨白,只顾将我一手护在身后。
余光见着另有些人往林中来,为首的百里,身后随着辛垣一干人。
维晚止了笑,冷冷看着百里,将手中半截残绡扔在百里面前:“这个人情,我可还尽了?”
辛垣面色惨白,方要说什么,却给百里拦住,面上无情道了一句:“尽了。”
维晚一声冷笑:“那是最好。”说罢却是一眼也不看旁人,竟是向若即投来一瞥,眼中嘲弄讥讽,怜悯更甚。
见她这么一眼,我心下火起,若即却好似吃人一剑,身形都微微一晃,那维晚才出声问道:“那把剑,是你家宫主的罢?”
他这么一说,百里人等中好几个竟倒抽冷气:“灵珏剑?”
维晚冷笑:“上官弱冠夺魁,便是凭的这把剑。”她顿了半晌,淡淡补上一句,“无情人,多情剑,倒是般配得很。”
话音还未落,就见她纵身往那夜里去,身姿在林间闪烁几下,便完全不见了踪影。
不知是她那一眼,还是那些话语,一口气哽在我胸口,徘徊不去。
若即冷冷问百里要做什么,百里先是一愣,又对他循循善诱,说话无非便是宫主待他如何不好,何苦如此明珠暗投,不妨入他麾下,将来这大好江河如何如何。
今日夜里过惊过劳,我自觉不对,赶紧转过头去,果然浊气上涌,我忍不住呕出一大口血来。
我自己是见惯了的,却将若即惊着,心中愧意,刚要对他好言相慰,腹中却又是一阵翻腾,只能强忍下来,却是再无心其它了。
若即吓得用力抱住我:“小若,怎么了?”
百里低低地笑:“若小姐无甚大碍,怕只是我用的那克制她病情的药性上来了。”
我见他下套,就扯着若即的衣裳,无力说道:“带我回去……见晋子安……”
百里武功不行,耳力却是极佳,听我这般说,便笑道:“晋子安若是有法子救,早就给你解了,怎么还会轮到今日。”
若即抱着我,只片刻踟蹰,便纵身往树林深处去。我强压着胸口气血翻滚,心中却是平静欣喜,终于能回去了。
百里并不死心,话语从背后悠悠传来,竟是十拿九稳的腔调:“若无药物,她撑不出这片林子。”
若即明显一迟疑,我摇头,揪着他的衣衫:“带我回去。莫再生什么事端,就带我回临阳,会清风楼,可好?”
他看我,神色挣扎,却说不出一个好字。我再也强压不住,又吐出一口血来,神志昏沉,连他在耳边的声音都听不清,只依稀记得还在说道:“带我回去……”
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
我醒来的时刻,只见得了月凉如水,凄凄淡淡洒了满地,零碎不堪收拾。
浑身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只勉强微微睁着眼,瞬时又是萎靡困顿。
身后靠着的人却是一动,急急起身来问道:“醒了?”
我听着若即的声音,才强打着精神睁开眼来,立时就见了他从后面探出身子来,不知过了几个日夜,面容上竟是有憔悴之色了。
他见我睁了眼,却是大喜,一派眉飞色舞的样子:“可是醒了!”
说罢连忙起身来,端过一边的温茶,小心地扶着我喝下去。
一杯茶才喝了一半,我便觉着腹中鼓鼓,竟是喝不下去了,便摇摇头,将那茶杯推了开去。
若即接过去,也不以为意,只往边上一放:“你方才醒,也不好吃那么许多的,先歇息一会。”
我嗯了一声,复又靠在他身子上,脑中混混,只觉得他轻轻地抚我,唇一下一下轻轻地印在额头上,另一手环在我腰上,不敢用力,却也丝毫不放松了去。
我只是疲乏,却不困顿了,依在他身上,握着他的手,细细微微地蹭。
若在平日,他肯定要笑嘻嘻凑到我耳边来说些话的,今日里却是反常,他只将我往怀里搂得更紧,低低唤了一声小若,便没有话语了。
我垂下眸子,看到身下再眼熟不过的床榻被褥,心中便清楚了,我们却还是在百里的山头上。
若即肯定不是自愿留下的,渐渐回想起那日百里的话,便也不再问了。
他肯来寻我,已是冒着不小的风险,如何还能让他这么两相难为。
我便轻轻说道:“带我回去罢。”
他环在我腰身上的手一紧,却未说话。
我再开口:“若知从那年与你一道逃出来,要见这么多的事端,我倒宁愿……”
宁愿……
话到这里,却是说不下去了。
若即将头埋在我脖颈处,贴着我耳朵轻轻问:“宁愿什么?”
我叹一口气:“这么多的变迁,这么多的事故,我竟是甘愿的。也从来不曾想过,当初若变动一步,会变成什么不同光景。”
若即又不说话,只将我牢牢圈在怀里。
我挣扎着转过身去,轻轻吻他有些干燥的唇,低低说:“若即,我是甘愿的,知道么,只因有你,这一切,都甘愿了。”
他将我死死压在胸口,压得他呼吸都有些变了,却是什么也未说,印上我的唇,舌尖一点一点描摹着。
我知他在犹豫什么。
百里不过是拿我的命逼他,逼他要背叛皇上。
我是不信若即会背叛皇上的。即便只听那只言片语的,也知道皇上于他,不仅仅是宫主。
从小便是那人教他武功,教他行为道义,教他立身处世。
他那样的身份,皇上与他,更是如兄如父。
若即说过,他这条命是皇上的。
我不争。
那日里,我已说了,他给不了我的,无事,我来给他。
红尘相伴,山高水远。
知足,所以不争。
若即,我于你情深如此。
轻轻拉开他,我道:“若即,带我回去罢。”
话才说完,便听得几声指节扣在门上,只是礼节性的几声,也不等门内人的回音,径直推开门走了进来。
先入眼的是一只捧着药碗的手,我心中一个咯噔,不经然想起晋子安那厮,待那人跨入门来,才见得竟然是百里。
我在这里三年,都未曾见过百里十指沾上那么一点点阳春水,今个儿倒是怎么了。
百里见我们如此躺在榻上,眼中一暗,却在面上堆起笑来:“如何,我便说的,那付药一下去,今日定能醒来。”
若即坐起身来接过药,并不言语。
百里也不复多言,只是噙着笑看他扶我喝下药去。
我有些反胃,若即轻轻抚着我的背,待我平稳下来,才复又将我放回榻上,又将那床幔放下,隔去百里的目光。
我静静面向里面卧着,听着若即不冷不淡道:“阁下又来巡视么?”
百里竟吃吃笑道:“百里这三尺土墙,怎么可能拦得住左护法来去。只是见左护法似无去意,区区便尽些地主情谊罢了。”
言罢是茶水入盅的声音,似有人将圆凳拖开,两人在桌边坐下。
若即似是缓过心境来,话语微微轻扬,带了丝丝笑意:“阁下倒是好客之主,只是也要看那入幕之宾为何人了。”顿了晌,复又接上,“阁下便忘了白少情白宫主了么?”
我心中又是一个咯噔,若不提起倒真要忘了去,那人也算是最早识得我的人之一了。
百里也是一顿,却立时缓了过来,也接着笑道:“白宫主便是念着血缘之亲,太过轻视与你,不曾邀一质子,方才落得这般下场
若即似不以为意:“如今倒有何不同的?”
百里笑:“这便是造化弄人了。若姑娘身上的病,偏只有在下能治,左护法看这可也是种缘份。”
若即却是一声冷笑:“可不是,当初也是你种下这祸根。”
百里道:“此言差矣。若姑娘不曾习武,体格娇翼,当日从那崖上坠下已是魂断魄碎,如若不是这一剂汤药,起那无量回魂之术,怕已香消玉殒,左护法可往哪里去成这么一段再续前缘的佳话。”
若即仍旧是一声笑,似是自嘲道:“我曾叛她一次,你便不怕我故技重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