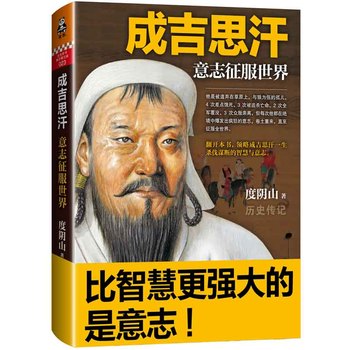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7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尽管写得那么坏,甚至是混杂着迷信和荒唐而写出的,但因为题材的意义重大,故仍然要比普禄达尔克和利维乌斯重要得多,教育意义丰富得多。
此外,为了更详细和更充份地认识到在我们这论述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中叫作生命意志之否定的是什么,再考察一下那些充满这种精神的人们在这种意义上所定出来的伦理训诫'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训诫同时也会指出我们的'这一'见解,尽管在纯哲学上的表出是这么新颖,'实际上'是如何的古老。同我们最接近的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伦理就完全在上述精神的范围之内,并且不仅是导向最高度的博爱,而且也导向克制欲求。最后,'否定意志'这个方面在那稣门徒的著作中显然地已有了萌芽,不过直到后来才有充分的发展,才明显的说了出来。我们看到使徒门'已有这样'的训诫:爱你邻近的人要和爱自己一样;要行善,要以德报怨,以爱报怨;要忍耐,要柔顺,要忍受各种可能的侮辱而不反抗,饮食要菲薄以抑制佚荡,要抗拒性冲动,如果可能的话就完全戒色'等等'。这里我们已看到禁欲或真正否定意志的初阶。否定意志这一词所说的正就是福音书里所讲的否认自己,掮起十字架。(《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两段;《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三十五两段;《路加福音》第九章二三、二四两段。第十四章二六、二七、三三、三段。)这一倾向不久就愈益发展而成为忏悔者、隐士和僧侣的缘起了。这本来是纯洁而神圣的,然而也正是因此所以完全不能适合于大多数人,'所以,这种倾向既在许多人中间流行起来,'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就只能是伪装的虔诚和可怕的丑行了。这是因为“滥用最好的即是最坏的”。在后来建成了的基督教里,我们才在基督教圣者和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到那种禁欲的萌芽发展成为茂盛的花朵。这些人的布道除了讲求纯洁的仁爱而外,还讲求彻底的清心寡欲,自愿的彻底贫困,真正的宁静无争,彻底漠然于人世的一切;讲求本人意志的逐渐寂灭和在上帝中再生,完全忘记本人而浸沉于对上帝的直观中'等等'。关于这一切,人们可在费涅隆著的《圣者们所沦内在生活规范解说》中找到完整的记述。但是基督教精神在它这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哪里比在德国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就是在迈斯特尔·埃克哈特理当有名的《德国的神学》一书中,还有更完善,更有力的说明了。路德在他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除了《圣经》和奥古斯丁外,他从任何一本书也不能象从这本书一样更懂得什么是上帝,什么是基督,什么是人。——我们一直到1851年才从普菲费尔校订的斯督特迎特版本得到了这本未经改篡的原文。这本书里所记载的规范和训诫对于我所论述过的生命意志之否定是一种最完备的,从内心深处的信心中产生的分析。所以人们在以犹太教加新教的自信而对此作出否定的武断之前,应该好好的拿这本书学习一下。在同一卓越的精神中写下来而不能和这本书完全同样评价的是陶勒的《基督贫困生活在后世的摹仿》和《生命的神髓》。我认为这些真诚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说教比之于《新约全书》,就好比是酒精对酒的关系一样。或者这样说:凡是我们在《新约全书》中象是透过一层轻纱或薄雾看到的东西,在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却是毫无遮拦地,充分清晰明确地摆在我们眼前的,最后人们还可把《新约全书》看作第一次的超凡人圣,把神秘主义看作第二次的超凡入圣——“小神秘和大神秘”。
可是我们在上古的梵文著述里就看到我们所谓生命意志之否定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有更多方面的说法和更生动的描写,'这些'都是基督教和西方世界所不能及的。至于人生的这一重要伦理观点所以能在印度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更坚定的表现,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这儿完全没有外来因素的局限,不象犹太教之于基督教。基督教崇高的创始人,或意识地或不意识地不得不迁就犹太教以使新的教义与旧的犹太教相衔接;于是基督教便有了两种性质大不相同的组成部分,我想其中纯伦理的部分首先应该是基督教的因素,而且是基督教专有的因素,并想以此区别基督教和原有的犹太教教义。如果人们在已往就曾多次担心过这一卓越的,造福人类的宗教有一天会要完全濒于崩溃,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更要担心,那么,我认为可以为这种担心找得到的理由,只是这个宗教不是由一个单一的因素所组成的,而是由来源不同,卑凭世事变迁牵合到一起去的两种因素组成的。由于这两种组成部分对于逼到头上来的时代精神关系不同,反应不同而产生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解体可能是势所必然的。不过在解体之后,基督教的纯伦理部分仍可永保不受损害,因为这是不可能毁灭的部分。——尽管我们所知道的文献还很不充分,我们现在就已看到在《吠陀》中、在《普兰纳》中,在诗歌、神话、圣者轶事、语录和生活戒律中已从多方面有力地表出了印度教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中,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些训诫:要完全否定一切自爱以爱亲邻,慈悲不仅以人类为限,而要包括一切有情、施舍要不借散尽每日辛勤的所得;对一切侮辱我的人要有无边的容忍,不论对方如何恶劣,要以仁德报冤仇;欣然甘愿忍受一切羞辱;禁各种肉食。追求圣道的人则绝对戒色并禁一切淫逸之乐,要散尽一切财产,抛弃任何住所,亲人,要绝对深密的孤寂,在静默的观照中度此一生;以自愿的仟悔和可怕的,慢性的自苦而求完全压制住意志'等等等等'。这种自苦最后可以至于以绝食,葬身鳄鱼之腹,从喜马拉雅山圣峰上坠崖,活埋,以及投身于优伶歌舞欢呼簇拥着的,载着菩萨神像游行的巨型牛车之下'等等为手段'而甘愿自就死亡。这些训诫的来源已达四千余年之久,直到现在,尽管这'印度'民族已四分五裂了,依然还是他们所遵守的,个别的人还不折不扣的履行到极端。一面要求最沉重的牺牲,一面又能够在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民族里这样长期地保有实践的效用,这种东西就不可能是任意想出来的怪癖,而必然是在人性的本质中有其根据的。但是还有这么回事,那就是人们在读一个基督教和一个印度忏悔者或圣者的传记时,对于双方那种互相符合的地方还有不胜惊异之感。在各有着基本不同的信条,习尚和环境的同时,双方的追求和内在生活却完全相同。双方的训诫也是相同的,例如陶勒谈到彻底的贫苦时说:人们应该自求贫苦,而办法就是完全散尽一切可从而获得任何安慰或获得人世间任何满足的东西。显然,这是因为这一切东西总是给意志提供新的营养,而这里的目的原是要这意志完全寂灭。在印度方面,我们在佛的戒律里看到与此相对应的说法,这些戒律禁止忏悔者不得有住所和任何财物,最后还禁止频频在同一棵树下栖息,以免对此树又发生任何亲切或爱好之感。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和吠值多哲学的布道人还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一切外在的善行和宗教作业对于一个已经功德圆满的人都是多余的。——时代这样不同,民族这样不同,而有这么多的互相一致之处,这就在事实上证明这里所表明的,并不是象乐观的庸俗精神喜欢坚持的那样,只是神智上的一种什么怪癖或疯癫,而是人类天性本质的,由于其卓越故不常见的一个方面。
至此我已指出一些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人们可以直接地以生活为来源而认识到那些表出意志之否定的现象。在一定的范围说,这是我们整个考察中最重要的一点。然而我仍然完全只是大致地谈到这一点,因为指出那些以亲身经验现身说法的人',请人们自己去'参考,要比无力地重述他们所说过的而毫无必要地再胀大本书的篇幅好得多呢。
我只想还加上几句以便一般地指出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我们在前面已看到恶人由于他欲求的激烈而受着经常的,自伤其身的内在痛苦;最后在一切可欲的对象都已穷尽之后,又以看到别人痛苦来为顽固的意志的馋吻解渴,那么,与此相反的是那已经领悟生命意志之否定的人;从外表看尽管他是那么贫苦,那么寡欢而总是缺这缺那,然而他的'心理'状况却充满内心的愉快和真正天福的宁静。这已不是那个不安的生命冲动,不是那种鼓舞欢乐了。欢乐是以激烈的痛苦为事前,事后的条件的,譬如构成贪生的人们一生的那种欢乐;'这里不是欢乐'而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安定,是一种深深的宁静和内心的愉快。这种境界如果出现于我们眼前或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之中,那是我们不能不以最大的向往心情来瞻仰的;因为我们立即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超过一切一切无限远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良知'常'以“战胜自己,理性用事”这响亮的口号召唤我们到那儿去。于是我们觉得'下面这个比方'很对,即是说我们的愿望从人世间赢得的任何满足都只是和'人们给乞丐的'施设一样,'只能'维持他今天不死以使他明天又重新挨饿。而清心寡欲则相反,就好比是继承了的田产,使这田产的主人永远免除了'生活上的'一切忧虑。
从第三篇里我们还记得这一点,即是说对于美的美感,那种怕悦,大部分是由于我们进入了纯观赏状态'而来的'。在这瞬间,一切欲求,也就是一切愿望和忧虑都消除了,就好象是我们已摆脱了自己,已不是那为了自己的不断欲求而在认识着的个体了,已不是和个别事物相对应的东西了;而客体成为动机就是对这种对应物而言的。'在这瞬间,'我们已是不带意志的认识的永恒主体,是理念的对应物了。我们也知道这些瞬间,由于我们这时已摆脱了狠心的意志冲动,好比是已从沉重的烟雾中冒出来了似的,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幸福的瞬间中最幸福的'一瞬'。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的意志不只是在一些瞬间,如美感的享受,而是永远平静下来了,甚至完全寂灭,只剩下最后一点闪烁的微光维持着这躯壳并且还要和这躯壳同归于尽,这个人的一生必然是如何的幸福。一个这样的人,在和他自己的本性作过许多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完全胜利了,他所剩下的就只是一个纯认识着的东西了,就只是反映这世界的一面镜子了。再没有什么能使他恐惧,能激动他了;因为他已把“欲求”的千百条捆索,亦即将我们紧缚在这人世间的捆索,作为贪心、恐惧、嫉妒、盛怒,在不断的痛苦中来回簸弄我们的捆索,通通都割断了。他现在是宁静地微笑着在回顾这世间的幻影。这些幻影过去也能够激动他的心情,能够使他的心情痛苦,但现在却是毫无所谓地出现在他眼前,好比棋局已终之后的棋子似的;又好象是人们在狂欢节穿戴以捉弄我们,骚扰我们,而在翌晨脱下来了的假面具和古怪服装似的。生活和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只好象是飘忽的景象在他眼前摇晃着,犹如拂晓的轻梦之于一个半醒的人,这时现实已曦微地从梦中透出而梦也不能再骗人了。正是和这梦一样,生活的形形色色也终于幻灭,并无须越过什么巨大的障碍。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