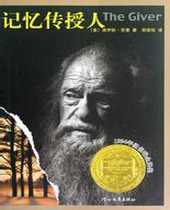记忆之莲-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解掉领带,走到她身边,在床沿上坐下来,换了一种更坦白的方式说:“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了?”
没换衣服就坐在床上,这举动让李孜觉得心烦,她停下手里的事情,推推他让他快起来,一边反问:“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Terence还是坐在那里,他顿了一下,看着李孜说:“那天跟你父母吃饭,你说女人年纪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李孜回了一句,话刚说出口却已经想起来,这话她的确说过,不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早就忘到脑后,Terence倒记住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两肘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握在一起,眼睛看着床脚边那一小块羊毛毡,“想弄明白你只是不想跟我搬去洛杉矶,还是根本不想结婚?”
这番话让李孜觉得刺耳,她合上电脑,放到一边,看着Terence说:“你早就知道我不想去洛杉矶的,何苦等到现在我辞呈也递了又来问。”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直说你不愿意?“Terence的声音里也带着火气。
李孜很少看见他生气,心里也知道这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事情,但她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也跟着叫起来:“你失业一年半了,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洛杉矶有间公司要你,你要我怎么说不愿意?!“
Terence一下子站起来,撂下一句:“Fine!你现在改变主意也还来得及。”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李孜没去拦他,也来不及做什么回答。她突然发现一个怪现象,他们这样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说英文可能更自在些,比如床上的dirty talk,又比如吵架,自以为说了就好像没说,其实全然不是这样的。
Terence走了之后,她仍旧坐在床上加班,连姿势都没换过,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刚才总算想起来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决定结婚的了——Terence问她愿不愿意跟他去洛杉矶,她说愿意,他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就顺便提出来结婚。如今回想起来,她当时可能只是想表现的supportive一点,因为那段时间他一直为了工作的事情心事重重。而Terence提出结婚或许也只是为了回报她的好意,毕竟放弃纽约的一切,对她来说不是个很轻松的决定。
就这样一直到午夜,李孜带着一种半是解脱的伤感入睡,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嘴巴里满是苦味。
上午九点半,她到了事务所。有人告诉她,Ward来找过她,他们约的人已经来了。
她赶紧去Ward的办公室,还没进门,就看到玻璃隔断后面,Esther Poon和一个深栗色头发的男人坐在房间一角。Esther占了三人沙发的一头,男的则坐在另一边的一把扶手椅上,两人离得很远,显得有些刻意。她敲了敲门走进去,Ward作出一幅欢天喜地的样子跟她说早安,把她介绍给那个男人。
“这位是Lance Osler,”胖子夸张的说到,“刚刚晋升为首席演员,三月就要在一出新戏当中担纲主角。”
李孜也在那一圈沙发上坐下,趁Ward说话的当儿,留意看了一下Osler,他和Han差不多年纪,长相也很漂亮,但看起来更随和,也更开朗些。
Osler听出了Ward的言下之意,质问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李孜连忙开口打圆场:“我们之所以约你来,其实是为了了解一些Han过去的事情,毕竟你们认识许多年了,而且你还做过他的伴郎。”
Osler轻笑了一声:“他那个人恐怕也找不到其他人来做伴郎。”单看那表情倒像是回忆起许多快乐的往事。
李孜便也附和着笑了一下,又问:“Han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一个叫G的女人?”
“我听他提过这个名字,许多次,”Osler回答,“但从没亲眼见过这个人。”
“Han说他婚礼前夜的派对上,G也来了,你没看到她?”
Osler摇摇头,似乎想起了一些让他烦乱的事情。他看了一眼坐在斜对面的Esther,说:“他们结婚的那天早上,我去找他,发现他还躺在新居起居室的地板上睡觉,我叫醒他,他有些恍惚,问我她去哪儿了,说前一天夜里G和他在一起。我以为他只是喝多了,后来才知道没那么简单,他一直就有病,根本就不应该结婚。”
“他应不应该结婚不关你的事。”Esther突然插进来打断他的话。
Osler却也没有退让的意思,反而看着Esther说道:“至少我没有说过任何和事实不符的话,有些事情,是不是要说出来,不是我能做的决定,对不对?Esther?”
大约两秒钟没有人讲话,只有Ward作出一副饶有兴味的样子看着所有人。
Esther低着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Osler站起来,对Ward说:“我应该说的都在上次开庭的时候说了,都是事实,没有什么要更正的地方。”说完就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了。
Ward也赶紧起身跟出去,只留下两个女人坐在办公室里。
Esther转向李孜,看着她恳求般的说:“能跟你单独谈谈吗?”
16.Vows 誓言
一年半以前,曼哈顿
二零零八年五月,Esther花了短短两周时间准备她的婚礼。
小时候,她也曾幻想,有一天结婚了会是什么样,裙子的颜色,头冠的款式,还有鲜花和蛋糕,她都曾仔仔细细的计划过。至于和她一起站在圣坛的那个男人,她倒是从没想过,小时候是不关心,后来则是认定了一个人,没必要再去想象。
现在,她真的要结婚了,婚礼却不是原先梦想中的样子,很小,很仓促,阻力要比祝福多得多。只有那个认定了的人没有变,Han,只有这个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她记得三年前那个深秋的午后,她在东三十二街的街角找回了她的Han,距离他们分手的日子,正好是整整十个月。一场阵雨之后,几片银杏的落叶把那条路染上一些温润的金黄色,她看到Han从街对面那栋玻璃建筑里走出来,他抬起头,也看见她了。
那个瞬间,Esther又记起G最后对她说的话:“别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
“那应该说什么?”Esther记得自己这样反问,面前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让她觉得气恼,他们只相处了不过几个月,却来告诉她应该怎么对待他。
“就告诉他你的感受。”G回答,“他是个很敏感的人,只是不喜欢把话说出来。没人真正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心电图或者超声波能证明他病了,也没有手术刀可以切掉病灶,但他只是病了,并不是他自己宁愿陷身在这困局里,你必须记住,他只是病了,而且,他需要人感同身受的明白这种困境。”
“你就是这样做的?”Esther看着G问,语气里仍旧带着些挑衅。
G笑了一下,摇摇头:“我恐怕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做这些事情,幸运的是,还有你。”
Esther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说出这样话,但那之后的三年,整整三年,她始终都是这样做的——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只是把自己心里的话说给他听,并试图感同身受的了解他。
Han回来之后最初的那段日子,各种各样的传闻充斥泛滥——有人说他完蛋了,有人说他仍旧是个疯子,甚至有个退休的女演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暗示,曾在Han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安非他命类药物。他从原来周身泛着纯白色光芒的王子一变成为危险人物。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又遇到什么样的阻力,他没有退让,Esther也始终都站在他这一边,一遍又一遍的告诉他: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在你身边,我了解你,你的执着,脆弱,每一个秘密,天赋,抑或缺陷,我知道你恨这一切,却又着迷于此,你不怕艰难辛苦,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普通人能得到的东西,妻子,孩子,爱好,无论什么,因为他们没办法染指那种无与伦比的天赋,它伤人,让你不停的思考,变得偏执,也让你成为最棒的,你可以错过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爱人,家庭,吻和爱情,但却不能错过它,因为当它结束,就是真的结束了。
现在他们总算要结婚了,Esther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快乐,却又隐约有些难过,她始终都不知道Han的求婚究竟是出于爱,还仅仅是对她的一种报偿。她试图甩掉那个念头,用各种各样麻烦的琐事填满每一个空档,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要她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Esther的爸爸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这件婚事,她妈妈本来是个很喜欢办婚礼的人,但也因为Han过去的那些事情,宁愿牺牲选衣服、买东西、办派对带来的乐趣,决定放手不管了。至于Han那方面的家人,则都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行程住宿也全都要靠Esther来安排,好在他家在美国的亲朋也真的不多。
未来的公公是个极其沉默的人,Esther曾一厢情愿的把他想象成一个内向的老派男人,把对儿子的情感埋藏在心底。接触了几次才不得不承认,他心里什么都没有,即使曾经有过些什么,也早已经空了。
而她未来的小叔子Russell,二十出头,两颊长了些青春痘,显得脸色不太干净,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Russell没有读完高中,也没正经工作,偶尔在嬉哈风格的运动衫牛仔裤外面套件肮脏的白制服,在他爸爸的小餐馆里打临工。婚礼的前一天,Esther把一些外地来的客人安排在举行婚礼的酒店过夜。她在酒店大堂看到Russell,笑着朝他招手,他却没有反应,带着他俗艳的女朋友径直朝客房电梯走过去。
这些事情倒还不至于让她难过,这许多年过去,她觉得自己已经变得足够坚硬,只有一个人能敲开这层外壳,伸进一只手,伤到她的心。Han,只有他,没有旁人。
婚礼前夜的Rehearsal Dinner还没结束,Han就已经走了,甚至没有跟她道别。Esther安慰自己说那只是Bachelor Party的惯例,转头却看到做伴郎的Lance Osler还坐在长桌边的老位子上喝酒。她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躲在洗手间里一遍又一遍的打Han的电话,却一直没有接通。这件事她谁都没告诉,因为如果让她父母知道了,这场婚礼也就吹了。
那一夜她本应该好好睡一觉,结果却是一夜无眠,坐在厨房里,漫无目的地按着电视机遥控器,好几个台都在播放奥巴马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街头演说的新闻。临到早晨,她终于下决心打给Lance,装作随便的问,他们昨晚去哪里疯了?
Lance却说他不知道,昨天他们一帮人准备出发的时候,Han已经不在那里了,本来安排好的活动也只好算了,弄得他很尴尬。
婚礼仪式下午两点钟开始,Esther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等着那个时刻到来——她一个人站在礼堂里,穿着白纱,捧着花,没有新郎。
总算,这场面最终没有成真,Han准时到了。Lance特地跑来告诉她,Han不过就是喝多了,躺在他们新居起居室的地板上睡着了。
听到这消息的时候,Esther正坐在化妆室的镜子前面,默默的念着自己的誓言。她松了一口气,却也感到一种被抽空了一般的疲惫,她记起几天前偶然看到Han写在一张请柬的背面的Vow:“我从十岁开始远离人群,至今需要吃五种处方药来保持理智,但我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