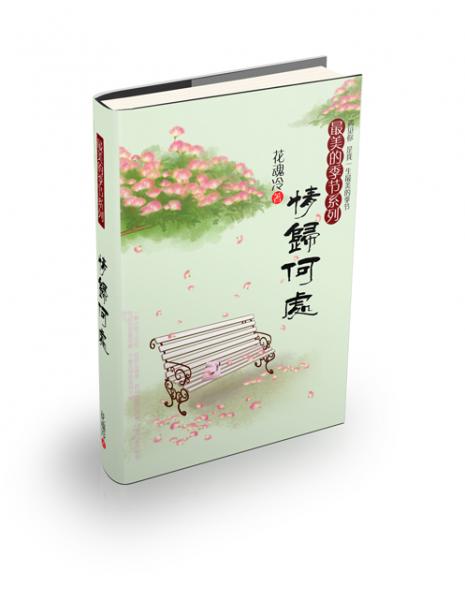(瓶邪)毒+三年(番外之一)-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片黯淡无光的黑幕,如今重又横在我面前──在吴邪的眼里。想不透我为什麽会把两张毫不相干的脸孔联想在一起?多可笑的想法,连我都想消遣我自己。
他跟他之间,是不是隐藏著什麽我所看不到的连结,从三年前到三年後的今天,一直是根要大不小的刺,扎在心头上;我要嘛不去理会它,以为装作看不见,也是种有效的麻醉。
眼前,既然有个机会明摆著,让我去求证,那,我就求证。
“你只当我找你肯定有事,我就问你件事儿,” 我向店家又要了一瓶啤酒,扭开後灌了一口,放回桌上,”还记得秦岭遇过的凉师爷吗?”
吴邪的脸色瞬间变了。
果然,我在心里暗想。见他这反应我很满意,对於自己一击命中准心,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了起来;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份自满有多悲哀。
吴邪一把抓住我准备再抬起来的手,晃了好几滴啤酒出来,“你问这个作什麽?为什麽提到他??”
我看了看被溅湿的袖口,再看看他,只见他前一秒钟还面如死水,现在却一下子涌了好多情绪上来,就跟瓶口不断溢出的泡沫一样。
当下,我几乎是立刻将眼前的吴邪、等於 ”师爷” 这项假设给否决掉;虽然我正面接触那家伙,不过就这麽一次,但,即便是身份暴露吧,我怎麽样也不认为,那人有可能出现 “冷静” 以外的表现,比方说扣在我手上的这股激动。
面对吴邪的激动,倒让我想起他第一眼见到挂在我耳上那只六角铜铃,他也是一把揪住我的耳朵,不管我疼得哇哇叫──那个时候的他,雀跃远远大过於震惊,有点像玩拼图的小孩,总算找到缺角的一块。
可现在的他…我说不上来,我和他中间只隔著一层白雾,可我竟然看不透他了;很显然 ”师爷” 是那个关键词,是拼图最中心的那一块,不是吗?这层觉悟却让我产生两种极端的矛盾,一是,更加急切的想拼出事实,一是,就此打住,永远不要让我看见事实的全貌。
这样的矛盾扯得我内脏发疼,但,吴邪质疑的目光从右方直逼而来,看来没给我选择的馀地。
我只好咂了咂嘴,接著说,”其实没什麽,就我想起了当年和你去秦岭,咱一路上碰的那些人,什麽李老板王老板泰叔,意图都很白,不就为那棵铜树而来吗?
只有那凉师爷,你说单纯考古嘛,凭他那猫样,还不在半路就给折了;干这行是玩命活儿,不是靠一肚子文墨就能跳进来混,那个李老板也像大风大浪过来的,还不是给鱼一口吞掉,更何况是他。”
一口气说上一串话後,我突然间想到了什麽,连忙收声──事实上,在第一次从 “本我” 分裂出来时,我犯口吃的毛病,就已经不存在了。
为了不让吴邪起疑,当年出号子和他见面时,我照样装结巴,装得还挺累;刚才光顾著一个劲儿丢话,竟把这环节给忘了。
吴邪依然直勾勾盯著我,脸色比刚才更难看,我还以为他是察觉到这一点,然而他却──
”你要说的应该不只这些吧?”
有种钢钉打穿了脑门的感觉,我看著他,我很认真的看著他,耳膜里反覆著刚才那句话,确定我没听错半个字。
就连浇灭心火的语调,也可以冷得那麽相像…我想我是真正的绝望了;看样子,比起和我有关的一切,对他而言,还及不上一个虚假的名字。
“好,我就直白了说吧,” 如今我已当是破罈子破摔,也没什麽需要再欺瞒,”那个自称凉师爷的,确实留藏了好几手,在我看绝非省油的灯;你跟王老板上树那时,他不过用手指头敲了几下崖面,便警告我那座岩里渗了大量的水流,很不牢靠,後来山壁果真坍塌了。”
“当时他还说了,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平安的带出去,但是我没作到…我很想,但我确实没能作到;所以我才想,那人对你的关心,看来很不一般,甚至有没有可能…你是认得他的?”
现在我所干的事,叫作搬石头往自己脚上砸,就为砸出个我不一定想要的真相,还有没有人能像我这麽狼狈?
这一砸,同时也砸出他更多表情变化,好像有什麽硬冷冷的东西,在他脸上崩解了开来,很多我看得懂看不懂的情绪,同时间回流到他身上,他的五官甚至看上去有点扭曲了。
讽刺的是,这样的他,终於开始像吴邪了,那个有血有肉的吴邪,只是我还来不及多看几眼,眼皮一眨,前一秒他还坐在我面前,下一秒只剩个空荡荡的座位,我一转头,发现他正用非常快的速度,往巷子头走出去──
朝著他的背影大喊好几声老吴,他头也不回,脚步还加得更快了;我正想起身去追他,手臂却被一个力量拖住,让我才刚站起来、又被迫坐了下来!
我定睛一看,抓住我的人,竟然是──吴邪?!他正坐在刚刚还空著的位子上,一边笑咪咪的替我挟菜,边问我,老痒你打算上哪儿去?我们这不是还有很多话没说完呢。
他那张过度夸张的笑脸,怎麽看怎麽虚伪,我先是愣在原地,见著他挟进我碗里的菜越来越满,怎麽也挟不完似的;而他的嘴角,则是一路笑咧开来,横过了两边脸颊,几乎快裂到耳垂下方去──
我发出一句怪叫,一伸手就去扒他的脸,啪啦一声,他整张面皮被我撕了下来,连著两颗吊在眼眶的眼珠子,鲜红的血液,从微血管里一丝丝爆出。
碰的一声,他上半身和那张血脸都倒在了桌面上,我惊叫著跳开,椅子也被我一脚踢倒;我知道、我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吴邪,一边这麽想著,我一边拔腿就往外狂奔──
然而当我跑到了巷子口,还是慢了一步,吴邪早已消失得不见人影。
我往前看,街角尽是黑茫茫的一片,只有三三两两的路人经过,到处都没有他;我再回过头,看向刚才自己跑过来的地方,不禁呆住了;
那里不过是一条空巷,尽头是封死的,看上去,已经废弃了很长一段时间,哪里还有什麽摊贩、店家,更不用说前一刻还倒在血泊的那张脸。
【盗墓笔记衍生】痒邪 / 瓶邪 …三年 06
我想我长久以来都搞错事情的重点,一直都搞错了。
当我找上吴邪,陪我深入那片折返秦岭的丛林时,不是没想过,这将会对他造成多大的危险──这风险他本人不止一次向我强调,那麽我,让我如此固执的理由,又是什麽呢?
失去母亲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从裁缝机上快速打下来的针头,我还来不及搞清楚它的路数,手指头上就已车进了一排线,我想扯掉它们,却只能扯出更多的血肉和疼痛;硬是扎进骨头的事实,我无力更改,我能作的,就只有从既定的现实中,找出自我解脱的方式。
比方说,我让我母亲再度活过来──虽然那一度成功,但是那混进了我曾经失去过她的恐惧,导致结果变得不三不四;再度拥有她的喜悦、以及她实际上已经离开我的痛苦,融合交织在我虚构出来的梦境里,重覆著上演,每一天每一天。
所以我想到了吴邪,一个不管在我印象中、以及他本人所彰显出来的价值,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如此纯粹。
他并不在意陪著我翻山越岭,追寻的只是一个和自己毫无关联的利益回馈,哪怕这过程可能赔上他一条命;把自己的性命,和这段旅程画上等号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他对我的信任,真的就只有那麽简单的动机。
我以为我的决心已经够坚定,虽然我处心积虑,不让吴邪发现我的意图,偏偏世事无法从人所愿──当他认清了我,能给予我的只会有失望和憎恨,这是我早就预料到、也准备好要全盘接受的部份。
我以为我能假装若无其事,用一只手臂就挡下它们,反正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坐在缝纫机前那个温柔的笑脸,以及再熟悉不过的饭菜香味,如今正在距此不到数百哩外的地方等著我,我只要回到那里,一切都将告止於终;你对我的情、对我的忠,累积到最後瘀结成的心灰意冷,我以为我都可以用这份得偿宿愿的满足来弥补,不再有一丝悔恨。
所以,当我从蓝田的河床底部爬起来时,我很惊讶,看了看上方坍塌的土石,上一个本我正在那里被压得支离破碎,而我早知道,自己会再活──
令我意外的是,我以为自己睁开眼会站在家中,我的母亲会围著那条眼熟的蓝色围裙,从厨房的门口走出来迎接我;可是我,却还在这里。
站起来拍掉满身的泥土,左右张望了一下,我很快就找到,那把依然将我锁在此地的卯钉:
吴邪,他和我之间还有一大段距离,远远望过去,我只看得见他横躺在地面,从杂乱的草丛间露出一半的身体;由於我眼里只注意他,导致背景物都变得模糊,导致我往前奔跑了好几步,才赫然发现,在他身边还站著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像张白纸。这是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唯一产生的印象;不是因为他穿得一身白,而是从天边射下来的阳光,看起来就像直接从他身体穿过去,彷佛他只是个平面的倒影。
我并不认识那个侧影,他被黑头发遮住的脖子、尖削的下巴,对我来讲都是十足的陌生;我只是纳闷那身装扮怎麽看上去有点眼熟,白纸就对摺成一半,在吴邪身旁屈了下来。
他接著伸出一只手,搭在吴邪有点发白的脸颊,两只特别突兀的长手指,透著阳光贯穿了我的视线,伴随他下一秒转过头来,看向我,那双眼睛,就像埋在土里的冰种黑曜石,走到哪都不可能被认错;
我立刻就认出了他是谁!再看回他身上的衣服,一连串早先发生在秦岭上的记忆片段,以破冰之势被拉拔出来;那人跟著我们爬上爬下、让人以为他弱不禁风,变起脸来却比翻书还快,怎样也翻不出他确切的意图──
明明这些事都发生在距今不到几小时之前,我和他此刻面对面站著,不知怎的,竟像在看一幅古代的壁画,从两双脚边横过去一大片时间的鸿沟;
我盯著他的脸看,他的目光也没有移走,我们就这样打量著对方,貌似在评估到底谁还是存在现实之中的产物?有种不知名的气场在流动,在这空间里,唯一被确认真实、且不受影响的个体,就只有吴邪了。
他还是静静的躺在原地,无意卷入这场战争;我靠著一眼的馀光,看出他还在微微起伏的胸口,证明他没有失去呼吸。
从那一刻起,我的世界其实已分裂成两种版本;一种只绕著我的母亲旋转,另一种,则是悄悄滋生出一个轴心点,叫作吴邪。
我一直有种错觉,以为只要死守住我拼命想挽回的那块疆土,其它的部份因此被毁掉,也无所谓。
当我第一次感觉到後悔,这两种世界,早已经没有并行的可能;当那个人脚踏在原本属於我的领界边上,看著我,他一句话也不用说,谴责就像早先山洞里落下的石雨,毫不留情把我再次活埋。
顺著他的指尖望过去,一道触目惊心的红痕,划在吴邪原本乾净的脸上;一声枪响砰地在脑中响起,吴邪的脑袋从我眼前一歪,一发子弹削过他耳垂,再偏离一寸,就会射穿他的太阳穴。
再往下看,缠绕在他手臂和肩膀上,一圈圈渗出血迹的纱带──刚才我到底置他於什麽样的险境里啊,而此刻我竟好端端站在这里,他却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