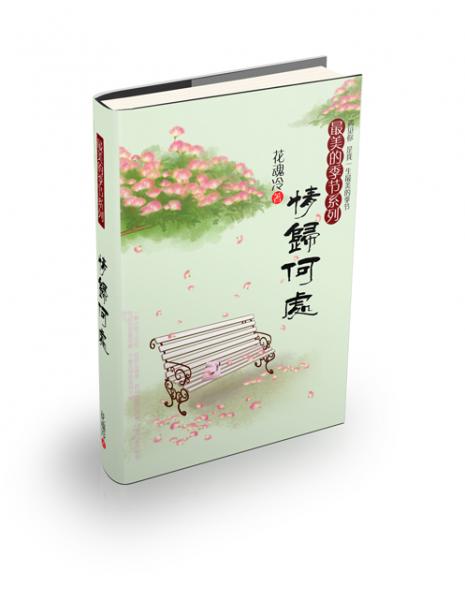(瓶邪)毒+三年(番外之一)-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曾经在你离开後杜绝著爱,在他人的拥抱中泄露对你的呐喊,所以我也杜绝了所有可能的爱,所有近身的抱拥,当下看也许惋惜,旁人的眼中或许愚不可及,但,莫不是背著这一路的可惜行走至今,我又怎会有如此的自由,独自躺在这里,只负责回忆你。
今天的阳光有些刺眼,虽然我不站在窗边,眼前无故的亮白,有些混淆了我的视野,不清楚此刻是白昼或黑夜,喧哗或沉静,我试图清空脑中所有杂讯,为了和你的对白。
下意识揉著掌心,上面残留的是疤茧脱落後的痕迹,为了不扎痛娃儿们稚嫰的脸颊,你再度握上它时,还认得我吗?
我悄然对著空盪发话,并不等待会得到解答。
看似毒害的选项,却早早解答了我的一生。
所以我要谢谢你。
张起灵。
…End
此文为 ”毒” 系列番外
时间点为张起灵离开後,吴邪重返回蛇沼之前
老痒视角。
在此特别说明一下,虽然这是毒的番外
因为是由解子扬的视角出发,说的自然是解子扬的故事
正确来讲,是解子扬和吴邪的故事
至少当事人自己是这麽认为,也这麽希望
除非他将吴邪的情绪看重大於自己,要不,对於吴邪的心情
大多数他还是只能看到片面
毕竟对吴邪跟张起灵的故事,解子扬知道的太少了
简地来说,解子扬是说故事的人,当然也希望故事单纯属於他和吴邪之间
但因为他介入的太晚,导致在这场故事里,解子扬永远只能当配角
虽说如此,仅次於瓶邪,我对解子扬算是满有爱的
也很努力要融进他的心境当中,尽管它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望天)
原本想一篇打死,看样子我果然不是写单篇完结的料 orz
痒哥出人意料的很难搞
在我的定义里,他是属於破坏性跟毁灭性很强那种
如果张起灵是慢性毒药,那解子扬就是一把枪
===
嗨,老吴,还认得我吗?
认得啊。
你是解子扬。
【三年】
吴邪不是个会演戏的人。
至少在我记忆的断层,每一个角落,不管清晰不清晰,他的机灵都是属於半生不熟那一种,能成就无伤大雅的诡计,要写成套的剧本就行不通了。
所以,当我站在离他不到五个脚步的地方,看著他,问他还认得我吗?他回看我的脸,语气平板报出我的全名,再来就不说话了。
那就表示在他眼里,我真的跟一张名片一样,除了写著解子扬三个大字,再来就没了,风一来,轻而易举就能把我吹走。
我们俩伫在他的古董店门口,貌似两尊风化的石像,堵住了原本想凑过来看热闹的游客,反正古董街向来没什麽游客;
我忍不住低头看自己的电子表,为的不是知道现在几点,而是几月几号;确定距离上一次我们见面,直到今天,只过了三年,不是三十年。
三年前我见吴邪,还没见,只是听,光从话筒另一边认出我来,他整个人乐得像掘到座油井;再来见了面,我们花一晚不到的光景,倒出足足有一辈子那麽多的话来。
三年後我见吴邪,没打电话,因为我记不得他的电话号码;我只是在心里想他,双脚不知咋的,飘悠悠就落在了这片土地.西湖孤山,西冷印社,哪个角拐过哪个弯,完全不需要思考──
紫杉大门前,两个铜制的门环,我的手心比脑袋还先认得它们,所以还没握上,就已开始发汗;吚呀一声,门向内,跟我印象中差不多的角度,自己打开了;
一双磨得有点旧的皮鞋,跨过那不高不低的门槛,对方头低低的,刚好对上我的裤脚,他一抬头,见了是我,先是愣下,接著定在原地不动了。
矮我半截的脑袋,没变,往左转弯的发漩,没变;就他那双眼,被暮色中和的一点光泽也没有,我以为至少会看见震惊、或者不屑,甚至愤怒的火焰;这麽异常的平静,反而把我储得满满的气魄抽了底,导致我早先预备好的几套词儿,突然一句也说不上来。
不管这人是怎麽回事,至少他还识得解子扬,倒是我,竟不认他是吴邪了。
【盗墓笔记衍生】痒邪 / 瓶邪 …三年 02
还以为三年不是多长的时间,起码当初蹲号子的时候,我是这麽想的。
原本我也害怕会度日如年,直到我发现,每一个挨到鼻尖前的拳头,都会自动偏掉、去砸背後的墙;喂猪吃还差不多的伙食,也莫名奇妙变作跟娘亲煮出来一样的味儿。
如此日子久了,除了心还挂在外头,脚板蹲在里面,墙上的历纸撕掉几张或换过几本,又有什麽太大的差别呢?
这也是为什麽,一见从号子出来的我,他会用变了调的嗓子,大笑道:他娘的,你在那里竟然还给人养肥了!
从那一句话出口之後,很多事,也确实变了调;当年从秦岭回来,我在把写给他的信寄出时,特意留了份影本,毕竟我的记忆力早就不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今天,来见他之前,我将那封发了黄的影本拿出来,一遍又一遍的读──
最後看著落款的日期,再望望表面,前後加减起来,虽然不是整足了三年,事实上我还迟到了一点,反正,眼前这人看上去,也不像有在等待的样子。
无所谓,既然我来到了这儿,也站在这儿,就表示,信里的某些承诺,将被我吞回肚里。
所以我当真把那封影本撕了,揉成一团,塞进喉咙给吞下去,这会儿我的胃部,倒真是有点隐隐发疼了起来。
我只当是被饿的,接著伸手去扣他的手腕,说认得就好,走,吃饭去。
俗话说的好,要掩盖心虚,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当成理直气壮;因此我的手劲很强,而他,竟然也出乎意料,没有拒绝或反抗,就这麽被我拉著走。
杭州的街上永远拥挤得令人作呕,人潮像海浪一波波流动,我拖著他,从人群里刮出一条路,不去管投在我们身上好几双怪异的视线;
这里曾经也是稻田,没有高楼跟号志灯,只有高过人的稻米,在身旁一字排开,到了夜晚就黑漆麻乌的。
我打小方向感好,敢一手拽著老吴…那时还喊他小吴,在充满蛙叫的田间整夜乱窜──他的视力平均一点五,偏就怕黑,所以一路上不停用呛著哭腔的嗓音问我,田里是不是有鬼,简直比青蛙还吵!
现在,他的腕骨突出,而且结实了许多,不再像以往那样,软棉棉一捏就会碎似的;可我还是有种预感,如果不拉好他,会被风刮走的,是他不是我。
两条黑影一样在地面拖得老长,可我等了很久,背後的人始终很安静,没有丢过来一连串他应该要有的质疑,只有鞋跟叩、叩、叩的声响,敲在半根稻草也没长的柏油路上。
我感觉胃好像越来越胀疼了,就在这时,刚弯进巷口的左边视线,恰好扫进了一家路边摊;
我朝那摊贩瞥了一眼,便转头示意他跟我过去,只见他顿在原地,望著摊子,心里不知在琢磨什麽,不过没一会儿他也跟上我,往摊边的座位坐进去;
我向店家要了菜单,点上炒青菜蒜白肉笋子鸡,还有啤酒,没记错的话,这些也是他爱吃的。
可一顿饭吃下来,我简直比蹲了趟号子还难熬;一开始,我还天南地北跟他扯,不挨重,净拣些不著边际的话──是,我就想试他的反应,而在试掉了半桌的酒菜之後,发现我像个跳梁小丑,在唱独角戏。
你朝山谷丢话,好歹还有个回音,而我更像是对著团空气自言自语,或是他把我当成空气,貌似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人坐在这里,数著切白肉盘里的蒜头有几颗,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
这下搅得我火大了,我把筷子啪的按在了桌上,推推他,让他倒是说句话。
他也放下手中的筷子,不过动作很轻,今晚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我,停滞了几秒,问,你来找我,有什麽事?
灯黄色的灯光下,身旁的面锅不断飘白烟还有油味过来,弄得我眼镜都起雾了,可我还是看得清楚,对面的那双眼里无光,就跟他的人一样。
”见你,” 我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再推回鼻梁,用一种轻佻的表情看他,”我就想见你,还不行吗?”
我心里所想的是,他有可能挥几个拳头、或者淬一口口水过来,我敢担保的是,它们会一个不漏的落在我身上,绝不转弯,而这正是我想要的。
没想到,他所作的下一步举动,竟然是低头沉思了起来,好像这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等他再抬起头,我还以为他要给什麽令人惊喜的答案,结果他只是淡淡说: “那你见到我了,还有其他事吗?”
我操!
到此为止,在他之前所展现的一切举动,尽管没一样是在我预想好的剧本之中,我只当他还惦著三年前的事,惦著那封信…
只要有个惦字,不管好歹,至上心上都还压个重量,可现在,事情显然不是我所想的那麽简单。
时间的力量很大,可以改变很多事,甚至改变一个人,这点,我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可是再长的时间,都不至於把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全掏了空,变成另一副完全不同的性格;
除非我跟他之间,有其中一人的记忆出了严重的差错──而这可能性,发生在我身上的机率,应该远比他大得多。
我所记得的吴邪不无情,或该说,他作不到完全的无情;
我所记得的吴邪,嘴巴上能说恨你,那说出来的,却及不上心底的凉,那凉意,又盖不掉被撕裂的疼──
到最後,即使心凉也死透了,汇集而成的,还是一个替你送别的眼神。
那里头有没有所谓的舍不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有,因为还惦记那个眼神,所以我走了,又回来了。
回来看他现在看我的样子,他的目光,的确直直注视著我,没有回避,但与其说他在看我,还更像是穿过了我,看向我身後的不知什麽地方。
我甚至转过头,察看我背後是不是有坐著人,确定了没有,又转回来。
再跟他四目相接时,不知咋的,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假设──
会不会坐在我面前的这人,根本不是吴邪?至少,不是我认得的那一个。
要知道,一个人戴著面皮去伪装成另一个人,这事我不是第一天见过,甚至我还干过,用的是比面具更简便的方法;
所以,换作其他人是我,只会怀疑眼前这人是砸了脑袋或中了邪,而我,却能很自然联想到这一诡谲层面。
当这样的想法成形,另一条脱轨的线路很快接了上来,刺穿我脑子里某一块陈封已久的区块;
见他这样,双眼空洞的像没装进任何东西,竟让我莫名的想起…某个人。
【盗墓笔记衍生】痒邪 / 瓶邪 …三年 03
三年前在秦岭,我顺著那根不牢靠的绳索滑下山壁时,给撞折了腰,疼的够戗;
那个自称是凉师爷的家伙,看似不靠谱,救急常识倒很充足,他用了一把拍子撩作成临时固定器,替我绑上,暂时缓解了疼痛。
当时,我心底十分苦恼,毕竟伤到脊椎,可不是闹著玩的事,眼看我们树都爬上一半了,真要为这伤给栽在了这里,我肯定不甘心。
这麽想著想著,原本一翻身就会传来的剧痛感,不知怎的,竟一次比一次来得不明显了──没有疑惑太久,我很快就明白到这是物质化的能力,正暗自在体内奏效,我的潜意识对身心同时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