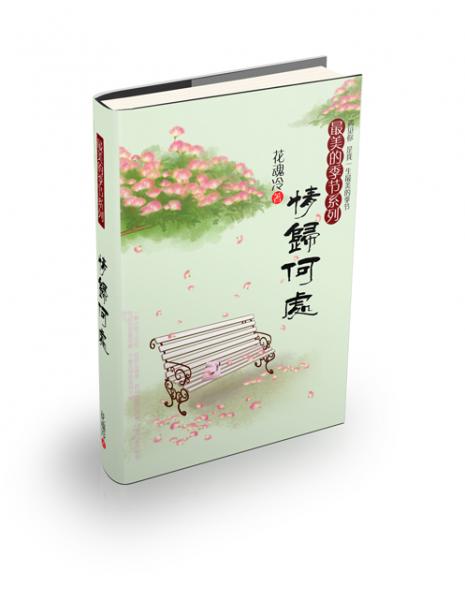(瓶邪)毒+三年(番外之一)-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开始毫不间断的发送讯息和信件,给珊瑚公司中我所熟识的成员,有电话号码的,我直接打电话,虽然回应我的人没有几个,我继续打;
QQ上倒是有几个人回讯给我,简略的表示:在那之後,公司的确有再派出另一组人马,前往当初我们止步的地点,试著再往前深入;然而,一来定主卓玛不肯再提供更进一步的讯息,二来,能够解读古文的乌老四,竟在上一趟行动中给大蠎蛇绞死了(这事是和我们分散後才发生的,所以我并不知情)。
简单来说,能够引导团队前进的几条线,到此几乎全断光了;他们也曾试图再联络陈皮阿四,这人却在第一次行动结束後,就此行踪成谜。
为此,打著珊瑚公司的名号,所出动第二批数量可观的人马,几乎可说是徒劳无功,只能再次空手而归。
我试过说服阿宁公司的人,在第二趟行动时带我一起去,虽然我骨子里没有半点信心,能扮演好称职的引路角色──
事实上,存活下来的同伴也很清楚,当初要不是阿宁他们的护航,我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够格渗进这麽大规模的组织活动;对此,我颇有自知之明,但,还是不放弃一丝一毫的可能性。
根据第二次搜索行动後传回来的消息,我得知,珊瑚公司事实上的确一无所获;
也许和利益有关的线索,他们不便明确的告诉我,但是,如果寻获到属於同伴的遗体,比方说阿宁,这群人也没有隐瞒我的必要。
倘若有个人,他已经失去了生命,那麽他的躯体被找到,便十分容易;相反的,若那人还拥有生命,这世上任何一人要想找寻到他,都不可能。
所以,我便开始了等待,就只是等待,没有上限的等;
我每天怀抱著同样的假设,又在第二天醒来,发现这项假设并不成立时、推翻了再重建一个;就这麽一来一往,没有定数的日子,在十指指缝间流逝而去。
信任感,一天比一天少。即使我没有放弃从微薄的管道打听消息,但是不管是从谁口中说出的信息,在我看来,都越来越像是一套精心策划的谎言;
在我害怕的同时,却也渐渐失去对人们的信赖,要我再拿什麽相信他们?我连自己都快不相信自己。
当我再回过神时,我的手正重重拍在店里那张香檀木制成的柜台桌上,而站在我眼前的,则是一位刚才讨价还价失败的中年男子。
那人涨得满脸通红、气呼呼拢起手中的古董包巾,从门前离开了。王盟很识趣的将左右两扇店门拉上後,信步移动到我旁边,什麽话也没多说,不过就放上一杯冰好的凉茶。
我往那沁凉出水的茶杯看了一眼,再看看王盟,印象中,上一次他问:”老板,您今儿个是怎麽回事来著?” …貌似也是个把星期前的事了,或者更久。我记不清楚,也懒得记,只见王盟一脸战战竞竞,站在那儿开口也不是、离开也不是。
我喊了声他的名字,王盟抬起头来,看向我的表情,貌似我并非那个向来以和为贵的吴老板,而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厉鬼。
叹了口气,我用自身最能挤兑的平静口吻,和王盟说,今天下午他可以早点收工回家,反正店的大门都给他关了,我们也用不著在这儿相看两不厌。
王盟一听这话,活像领了道免死符似的,拎起外套和钱包,一溜烟儿就往大门的方向退去。
当活人的气息都离开这个空间後,此地只馀留下古董的陈旧气味,还有我;我睨著眼横视了一圈周围,上等的青瓷、圆润的红玉,在我看上去却是同一个色调:令人生厌的晦暗灰;
甩甩头,我一转身往楼梯的扶手走去,几乎是用跑的上了二楼,砰地关上门。
靠在门板上,我仰起下巴闭上眼,心说吴邪吴邪,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不用任何人来提醒,我也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的情绪一天比一天还要暴躁易怒──有时我大清早醒来,走进盥洗间,拿著漱口杯和牙刷抬起脸,都会被镜子里的我自己给吓一跳。
那个人根本不是我,我打从心底想啐他一口口水!我用背紧紧压著门,貌似这样就能阻挡从身後追赶上来的怒气,但是没有用,怒意就像啃蚀木头的白蚁,一只只往我脊椎里钻,很快爬满我全身。
我的目光这时投向房间中央那张古董级的书桌,桌面上搁著一个翠玉制的烟灰缸──它的缸面很乾净,就和平常一样,不过静静地躺在原处,没招谁惹谁;但,这会儿一看见它,我内心的无名火又升上来了。
几乎是强迫性的动作,我的两只手、开始朝上衣跟裤子的口袋翻掏起烟盒和打火机,没有、没有,这是第几次我又忘了我早就他妈的不带这两样东西在身上!!可我为的是什麽?为的是什麽?!
我一跨步冲向桌前,在我的理智来得及阻止我之前,我已经一把抓起那个烟灰缸,往最近的那面墙砸过去──
啪啦一声,质地甚好的翠玉,在坚硬的墙面上摔成四分五裂,造成不小的声响;看著它的碎片一块块散落在地,我暗自庆幸,好在早早把王盟支走了,要不他在楼下,肯定被吓得不轻。
让我戒烟,我戒了。让我活命,我活了。
再来呢?再来还有什麽??我知道,一定很多人会想说,看这世上捧著大把钞票、从枪管或是手术刀下换回自己一条小命的人,繁不胜数,怎麽就有这麽不知好歹的龟孙子,人家免费让你活,你还活得不痛快,还要天天摆个讨债的脸色去吓唬人,还要在这儿抵毁无辜的古物来泄忿。
都说只有日子过得太爽太閒适的人,才会胡思乱想和没事找碴;
只要让我有一个重心──等待可以是重心,但老子我已经等烦了、等腻了!绝望也可以是重心,但非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想倾注全身的心力往那份上去。
若说等待是桥头,绝望便是尾端,我已经厌倦了只能站在起点枯等,偏偏又不甘这麽快走向结束;
於是我像个傻子杵在那桥梁中段,进退皆不是。要问我此刻最大的心愿是什麽,那便是,直接从原地消失,乾净俐落。
消失?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作法。
就这麽办。
心中一有了准头,刚刚还占据我的烦躁瞬间一哄而散,整个人勤奋了起来──我抓了车钥匙冲下楼,开上那台破金杯,先往大街去买了个尺寸中等的行李箱,接著驶回家;
一进门,晚饭也顾不得吃了,只管把眼睛看得到的衣服裤子、日常用品,一股脑儿的全往箱子里塞,直到塞不下为止。
第二天清早,我把古董店的店门和保险柜钥匙,串成一大串,悬在王盟那双还没睡醒的眼前,晃了晃。
他没多久就被吓醒得彻底,脸上的表情,像是宁愿每天见我打破一尊唐代釉彩,也不愿相信,接下来他所听到的话是真的。
我硬是将钥匙塞进他手里,说了,你高兴时来开店,不高兴就锁了大门回家多陪老母亲,就当这家店是自己的;卖出去的古物有赚,算你一份,赔钱,也没你的事儿。
好说歹说,估计花了一盏茶的时间,王盟确定了我不是开玩笑或者脑中风,这才面带菜色的把钥匙收进掌心。
我也留了随身联络的手机给他,这组号码是我昨儿个才办的,让王盟尽量别给除他以外的人,这段期间,我不想让任何熟识的人找著。
那…老大,这一趟出去,你还回来吗?
王盟语含忧虑的问。
一定回来。
只是,不确定那是多久以後。
【盗墓笔记衍生】瓶邪 …毒 21
到了机场,我径直走向询查柜台,服务员笑咪咪的站起来,我和她问了离起飞时间最近的、还有空位的班机,飞往哪里是哪里。
一上了飞机,我就著空服员端来的开水,吞了一颗半的助眠药,倒头就睡;一直到降落地面,机长透过广播器,用不太标准的英文念出千遍一律的欢迎稿,我才迷迷糊糊听出目的地名称,至於是哪个国家,那并不重要。
有的人出门旅行,会拿著地图和旅游手册规划上大半个月;有的人背了背包就上路,随波逐流;
这两种大相迥异的人,还是拥有个共同处,那就是,他们会享受这一趟旅程。
我想我两种人都算不上。每当上了飞机,我便吃药睡觉;脚一踏上陌生的土地,我则拿起挂在胸前的数位相机,开始到处拍照;
拍了些什麽,我也从没去留意,举了相机按快门只是种本能行为,一种能够不让我閒下来…大脑得以完全放空的行为。
当记忆卡显示空间已满,我也不买新的,直接切换到选单模式,把上一批的照片(也许里头有风景、有小贩、有机场外观、有路人,不清楚,我不曾回头再看过它们) 给全数删除,清空了卡片,上述的举动重新再来。
DELETE键真是项方便功能,人脑里也能安上一个该多好。
除了囤积照片再清除照片,还有另一项有助於放空的活动,就是看天空。
不管是,坐在充满盐巴味的海岸旁、陡峭悬崖突出的石块上,这个地点到那个地点,相隔开多少万英哩,在你头顶上那块巨大的氮氧组合物,你知道它都是同一个。
大部份的时候,它心情好,便会赏你一片看上去舒服的天蓝色──只不过有时候变脸比翻书还快,印堂才微微发黑,一道雷可能接著就打你旁边了。
你被它搅得气结,却也不能像对付那个翠玉烟灰缸一样,抓了就砸个稀烂。
久而久之,和它相处的时间越长,我越抓到一个窍门,对抗天空的最好办法,就是放弃对抗;出大太阳时就让它晒,下雨便让雨淋,一旦你全盘接受,绝大多数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个尽职的随扈,不罗嗦一句话,走到哪都无声陪伴,你只消抬头,一定看得见它。
我终於能够明白为什麽有人总喜欢望天。
真要说,旅途中完全没有令我印象深刻的事,说穿了还是有,也就那麽一件。
那天,我刚接完王盟的长途电话,这小子平时倒挺能忍,生意场上狗屁倒灶的事也和著血跟牙齿硬吞了;今日会打给我,我几乎能看见来电萤幕上闪烁著 “S。O。S” 三个大字。
不意外,跑得了人跑不了铺子,果真是我那打进店里都被王盟含糊带过、打了个把月手机却转到语音信箱,索性直接杀上店门要人的老妈。
虽说王盟意外有种的没供出我的手机号码,估计日子再拖上几天,他的小命会先交出去…至此,我不得不被迫面对,再怎麽不情愿,都必须回家一趟的事实。
久违的躁郁感,在那一晚再度像飓风袭卷住我;当时,我人在离家有半个地球远的墨西哥,光想到订机票、退房、打包行李,等种种繁琐程序,我头就疼。
於是乎我把手机关了,往床上一扔,套了皮鞋,走出旅馆的房间。
夜晚,只要避开几条藏污纳垢的小巷子,墨西哥的街道上,还是十分热闹明亮;
我信步晃进了一间酒吧,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我还刻意避开某些桃色地带,挑上这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吧;没想到,脚才刚踏进店门,充斥在吧里的,竟是另一片我料想不到的光景。
酒吧里清一色几乎全是男人,就连顶著盘子满场跑的侍者也不例外;吧场正中央是座舞池,劣质音响正播放听了就发晕的重金属乐,数十组男人对男人、勾著对方的腰、或脖子,跟随著节拍,作出毫不避讳的亲密动作,有几对甚至大剌刺热情的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