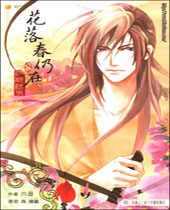木棉花落尽光年伤-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经年会特地跑到那条街上,仔细看四处张贴的牛皮癣。
除了办假证。
除了开假发票。
除了通沟渠的。
经年最后在一根电灯柱边停了下来。上面的牛皮癣写着:青春玉女,芳年十七……和援交论坛上的自我介绍一模一样。只不过后面多了地址。
住在三十六号。
是莫莫住的那栋楼吗?假如连这个也符合,那绝对是几率很小的巧合。
之前并未知道,那栋楼的门牌号。只知道那栋楼就在那里,好像学校外卖羊肉串的那个新疆人,他就在那里,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是一样的吗?
经年抬起脚,从街头开始数,凉茶铺的门牌是一号。
接着数下去。
二,三,四,五,六,七……
他从不知道数数可以让人心情如此沉重。每个数字的递增,心脏就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水分都被挤干,干燥得不想说一句话。有时候,他不堪重负地停下来,靠在某个号码的门牌下,喘着大气。
像把自己累成一个心脏病人。路人投过来疑惑的目光,连他也觉得自己奇怪。
鼓起勇气,准备再数下去。已经不远了,那栋楼就在前面。经年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门牌,二十八号了。
按距离计算,差不多三十六号就是那栋楼的门牌。
想到这里,他连脚也抬不起来。
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又顿住了。
他看到莫莫住的那栋楼,依旧熟悉的阴暗的楼梯口,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绑紧皮带,满意地朝他走过来。他赶紧转过身,装作在看贴在墙上的招租启事。
那人没有看见他,经过时经年闻到浓得令人作呕的酒气。
是酗酒的男人。修车铺的男人。
突然又想起那天晚上去找昔草时,她一个人在家,说男人去找小姐了。
突然明白了莫莫怎么会这么清楚昔草的事情。
突然明白了好吃懒做的莫莫会做什么工作来养活自己。
是他想的那样吗?
或许有些事情,无需要证明就明白其中的真相。
漫长得几乎要沉睡过去的雨季。
走在街上的人们,一颗颗潮湿的心。晾在阳台上的衣服,任微风也吹不动。
雨快下光了吧。
涌动在云层之上的阳光蠢蠢欲动,慢慢地,慢慢地,撕开灿烂的伤口。
一旦倾泻而下,便是一场盛大的涅槃。
莫莫拉开窗帘。二楼。她看到一个夏天的早晨。
城市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像让开一条难得的缝隙,她看见远处的山峦。淡淡褐色,高耸的山顶微微发亮。那是整个城市最接近阳光的地方。它摸着被阳光触摸的额头,告诉山下的人们,雨季就要过去了。
所有的潮湿都在撤退。
当她来到街上,她发现白天里的空气开始干燥起来。
她好久没在白天时出门了。这些天,她都上夜班。她去工作的地方,是本市一间繁华的娱乐城。她在那里做陪酒小姐。
不是能够骄傲说出口的职业。虽然比清洁工赚得多好多,虽然比服务员工作时间少,但是,缺少的却是尊严。所以,当经年问起时,没敢说出来。
生怕对方会误会。误会她跟妈妈是同一样的人。
偏偏不知道,对方已经误会了。
莫莫曾经遇到过住在自己隔壁楼里的一个同龄少女。听说以前也读同一间中学。不过早早退学了。现在,每天在幽暗的房间里,接待形形***的男人。莫莫是听街上的女人说起那个少女,那些女人的语气里并无鄙视和嘲讽。
都是同样的人。没有资格说别人。
有时也看见,那个少女站在门口,一脸的麻木,抽着劣质的香烟。只有等男人经过时才咧开嘴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
忽然觉得,那是一个比烟花更寂寞的少女。
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每夜穿着性感的旗袍,必须露出光滑的大腿,辗转在纸醉金迷的男人堆里。一杯杯地喝下烈酒,恍惚地察觉到男人们不安分的手断然地推开。耳边不时听到那些“装什么清纯?”“还不是婊子一个?”,如此肮脏的话,雪崩似地将她灭顶。
下班了,就跑到厕所狂呕不止。
一边呕,一边哭。
然后,生活仍旧在重复。
其实,不是肮脏低贱的女孩。
也想干干净净地拥有一个值得回忆的青春。
我们都希望操控人生的轨迹。可生活太巨大,***控的,竟往往是渺小的我们。
有时,清晨下班回家。
莫莫会在楼梯口遇到修车铺的男人。对方色迷迷地打量着她。她抱紧身体,就像身上的衣服被剥个清光似的。
她冲他叫起来:“操你妈!看什么看?!”
男人嘻嘻笑:“让叔叔看一眼又不会死嘛!再说,我跟你妈都这么熟了,就别装了,多少钱?开个价!”
“我装你妈逼!”
她咆哮起来,拍掉男人伸过来的手,然后脱下高跟鞋,要砸过去。男人吓得连忙跑下楼,在楼道里大声咀咒:“等你什么时候出来卖了,看我不整死你!”
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小至消失。然后,静谧的楼道又隐隐约约地响起哽咽声。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住同一层的女人打开半条门缝就破口大骂:
“哭什么!你全家死光光了是不是?!”
她就擦干眼泪,提着高跟鞋,赤着脚走上去。
是不是忘了告诉经年?
她之所以知道昔草的故事,是那个修车铺的男人来她家找她妈妈的时候,她在隔壁偷听到的。
是不是忘了告诉经年?
有关那个吉他少年的秘密。
可是,好像没有机会告诉他了。
今日闲来无事,一大早就起床,莫莫走到十字路口。走着走着,竟发现这条路通往学校的方向。赶去上学的学生们,风风火火地从身边经过。她就站在那里,仿佛看着青春拖着沉重的尾巴逃过去。
路灯从红转到绿,又从绿转到红。
看起来,滑稽可笑。
莫莫忽然跑起来,冲着停在斑马线上的人挥手。
“喂!喂!”
我在这里,你没看到么?
经年显然见着了她,可他依然拙劣地掩饰。红灯还在警告,他慌忙踏起自行车,迅速地冲过了车流密集的斑马线,似乎是,用寻死一般的决心逃离她。
莫莫扬着停顿在半空的手。再多的呼唤,也叫不出来。
不是看到我了么?为什么还要逃?
是不是不喜欢了?
可能是连分手也不干脆的男生,生怕被她缠上,便一直逃呀逃。她忽然觉得自己像西游记里的白骨精,而他是唐三藏。白骨精爱上了唐三藏,而唐三藏却以为她是要吃他的肉,长生不老的。
一个在追,一个在逃。剧情单调的故事,可以延续到年华的尽头。
她拨他的手机。只想问个究竟。
经年在课堂上接到。手机在抽屉里振动,他拿出来一看,是莫莫打来的。他于是又塞回去。
装作听不见。
装不了。听课的思维被无休止的拨打截断。他干脆关了手机。
然后蓦地发现,笔记本漏下了一大段空白。想了想。即使分手,也要说清楚的。
放学后,经年骑着单车再次去了那条街。
去得太早了。他停在街边,没敢上楼去。等待犹如长长的空镜头,他是那唯一静止的风景。荒凉的天幕下,他安静地等候着一个女孩的出现。
二楼的窗帘没有打开。不知道她在不在家。
一直等到黄昏。经年抬起头,看见夕阳那个坠落的光源,正在散发出最后的余辉。
昏黄的,温暖的,铺就了整条街。
回头就能看见,自己和单车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很长,喧嚣中微微颤抖。
是不是该回去了?
等不到了吧。
他犹豫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一直保持着同一姿势,当他想踩下脚踏时,发现大腿以下都麻了。他几乎和单车一起摔倒下去。
再等下去,全身都会麻的。忽然想起望夫石的故事。分析一下,不是没有可能。长年累月的等待,会使每根骨头每条神经慢慢地失去生命力,血液停止流动,皮肤不再柔软,于是就僵化成石了。
于是谁都能看见,那颗石头的等待。那是一份被世世代代所见证的爱情。
可他不是在等她的爱。他这样想着。
他是要与一份爱决裂。
人的身影在暗浓的黄昏里,越发朦胧模糊。褶皱的夜,正逐渐展开它的寂寞与孤冷。经年看见一辆名贵的宝马车,鸣着喇叭,慢慢地驶进街道。那辆车停在那栋楼下。
先出来一个中年男人。然后是一个旗袍女子。
霞光像蓦然明亮,刺激得眼睛都半眯起来。眼眶也湿了。视网膜被蒙上一层水汽。
不是哭了吧?
是太生气才对!
之前唯一幸存的狐疑也在此时此刻被粉碎得一干二净。毕竟经年正亲眼目睹,那个男人的手正不安分地搭在莫莫的腰上。而她没有拒绝,昏黄的光晕中泛出一朵浅笑。
谁拔掉了音响的插头,世界消失了所有的声音和喧嚣。
眼泪的流淌,是全宇宙唯一的声响。
男人坐回车里,傲慢地离开了。
虚伪的笑脸立刻被卸下来。莫莫厌恶地看着宝马车穿梭在鄙俗的市井间,慢慢消失。那个男人是娱乐城的客人,某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丧妻很久,对她有意思。她知道一旦接受他,便拥有梦寐以求的金钱和地位。
可她没有答应。做梦都想成为有钱人,如今机会就在面前,她却退缩了。莫莫知道,自己会永远被困在这条街。慢慢地守望着这条街日复一日地变得颓败,而她将会在某日突然发现自己竟白发苍苍。
莫莫叹了一口气。她把视线慢慢收回来,就看见深黄的霞光抹亮了每一扇窗。天空中的鸽子拍动灰色的翅膀,纷乱地,凌厉地撞碎一窗又一窗的荒芜。
视线转到某个角度,她便看见了骑单车的少年。
霞光和潮湿的空气仿佛拧成了一条粗粗的线,顿时扯住了他们。她看到他那么厌恶地瞪着自己,她吓坏了。是被他发现了么?自己穿这么暴露的衣服……莫莫拼命地合拢双脚,可风撕开旗袍的下摆,使她漂亮的大腿裸露出来。
男人们朝她吹起挑逗的口哨。
噢,也许他跟他们一样,认为她是那种女人。
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
你就是贱!
很贱!
他似乎这么说。明明没有张开口,空气却清清楚楚传递来如此残忍的话语。你贱!跟你妈妈一样贱!他那无形的声音就这样缓慢而疼痛地涌过来,鞭笞着她瘦而长的身躯。他只用一种目光,就杀死了她。
“不。不是这样的。”
莫莫哭着说出来。声音很小,传不到他的听觉范围便夭折。她只能拼命地摇着头,用这种固执而否定的姿势对抗他那鄙夷的眼神。可他竟转过身去,把单车调转到一个绝情逃离的方向。
别走!听我说!
所有说不出来的千言万语,被锁在心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