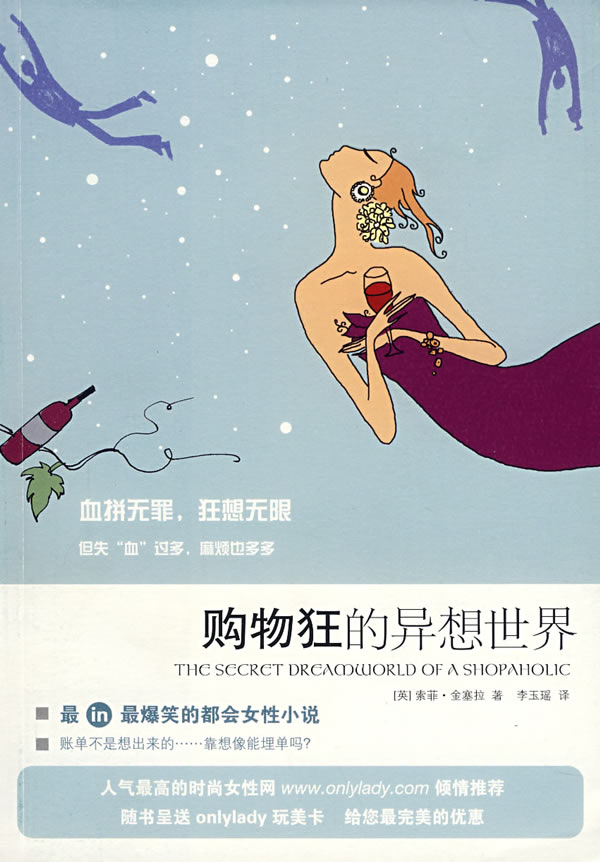北京人在纽约-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海外,找个活儿做,挣上俩我儿,可真是不容易。这么大拨大拨地退货,我可受不了,你们也该明白!”他说,“愿意干的,这两天加班加点,开夜车,把这点活儿赶出来;不愿干的,甭说别的,给我走人,我欢送!”
这一番火爆爆的训说完,他一转身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临进门,他把办公室的门摔得山响。
大伙放下手里头的活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静静地,谁也不吭声。
王起明如此凶神恶煞、暴跳如雷,这是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的。他们都被这一阵狂风暴雨震慑住了,没人说话,也没人动作。
郭燕知道,这个时候她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
她笑了两声,对大伙说:“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说了就好,说完了就过去,大伙谁也别往心里去。话说回来,这事也难怪他发脾气:饭碗要是砸了,你们说谁不急呀!”
她这么解释两句之后,又说话儿:“这些衣服虽然说是让人家退货了,可也用不着重新再打,把肩拆开了,前片从腰部往里打,把肩上的线换过来就行了。两天,我看能赶出来。
大家多受点累,就算是帮我的忙吧!“
说着,她先坐下,拿过件衣服重打起来。
这一席话,说的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都默默地做了起来。
办公室里,王起明双手捧着头坐着,不知道该想什么,也什么都没想。
过了半天,郭燕从外面走进了办公室。
“工厂,我来管。”郭燕对王起明说,“你出去找找。”
他点点头。
随后,他去了宁宁的学校,老师说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她了。
警察局他也去了。警官向他耸了耸肩,一摊手,表示这事警方无法介入。
这些预料之中的结果加重了他内心的烦乱。他钻进汽车,马上拨通了阿春的电话。
“有事吗?”
“有。”
“重要吗?”
“很重要。”
“来吧,我等你。”
这几年,王起明养成了习惯,遇见了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无法排除的苦恼,他总是去见阿春。在阿春的温柔婉转的音调里头,他心灵中颠簸的船只能变得平稳起来,他的烦恼愁苦会烟消云散。
“问题在于,”阿春手里托着半杯白兰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看见杯中的白兰地跳耀着金黄的颜色,“你自己。”
“我自己?”
“对,你小题大作了。”
阿春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平静地对他解释,“既然你下了决心把她从中国带来,既然你下了狠心把她推向社会,你又为什么为自己做的这一切而大惊小怪呢?”
“可是,他……”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淡淡一笑,“抽烟,脏话,大麻,性。可这又怎么样呢?这就是社会呀。你在决定让她走进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一切都早该想到的呀!”
“那不是太……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吗?”
阿春把酒杯放在自己面前的茶几上。
“要记住,”她说,“你现在是生活在美国。美国,表面上乱哄哄,实际上,它有它的规律,它有它的法则,它有它的——游戏规则——这都很严格。它的道德观念也只在这规则内起作用。你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你怎么能够要求你有又儿既生活在美国,又持一个中国的传统观念呢?那不成了畸形了吗?”
“可我是真的害怕,”他忧心忡忡地说,“她这一走,出现了些意外,我意想不到的事。”
“她不走的话,她的一切你都能意想得到吗?她吸大麻,你想到了吗?她在中国的怀孕和流产你想到了吗?”
他哑口无言。
“意外并不是昨天才发生的,只是你昨天才知道罢了。”
“我怕。”
“你怕什么,可怕在事情在后头哪!”不等王起明往下说她又接了下来,并离开了台子,手里拿着酒杯,来回踱着步子,“不错,是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书,因为它市场太小,不赚钱,中国移民毕竟在美国的数量太小了,有谁去真正的关心他们,研究他们呢?”
她走到窗口,眺望着蓝天说:“移民,移民子女的教育,多么深奥的题目呀。不要说小孩子,就是成年人也同样,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痛苦和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冲击,美国人叫cultural shock。移民就像断了肢体的人,再重新接起来一样,要骨骼对着骨骼,神精对着神精,皮肤边着皮肤,活生生的缝合起来,多么痛苦,又多么难熬哇。一些人,就是对付着接起来了,你也会发现他的走路,他的动作,他的神态是那么的不协调,那么难看。”
王起明听得入了神,香烟屁股烫痛了手指,他急忙把烟头弄灭,又重新点上了一支。
“至于移民的子女,特别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他们完全被新的环境弄糊涂了,好坏分不清了,标准全变了,价值观也靠不住了,象新衣服一样全换了。他们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他们舒服吗?”
“舒服?”她冷笑一声,“他们舒服得了吗?他们会反抗,本能地反抗这一切,又不自觉地去吸收这个新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他们一下子变得什么也不是了。既做不了美国人,又不再是中国人。新的生活完全陌生,旧的生活方式又被丢进了大海。”
王起明钦佩地望着阿春。
阿春接着说:“什么华青帮、青龙帮、鬼影帮,现在又加上了越南帮。
他们杀人、抢劫、贩毒、卖淫,这都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大灾难。他们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呢?只能睁着眼睛,看着他们的子女,这些本来是那么听话的孩子去杀人越货,他们对此束手无策。为了活命,他们拼命工作,没有时间去教育孩子,也没有能力去管教他们。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如这些孩子,社会知识也不如这些孩子,甚至连精力也不够了。怎么办?只好看着他们的孩子变成魔鬼。“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了吗?”
“没有。”
“一点没有?”
“对于这些年轻人,我们很难做什么事。因为这是历史,人不能抗拒历史。”
“可是……”
“就具体的人而言,你当然有事要做。”
“做什么?”
()
“防备。”
“防备?”
“对。”阿春十分有经验地说,“你要防备宁宁周围的人,隐藏在幕后的人。他们当然知道你是生意人,有几个钱在手上。他们会下手,向你下手。还有……”
“还有?”
“另一种可能。他们利用宁宁做人质,逼你交出巨款。”
他认真地听,一个劲儿地点头。说实话,他有点紧张。
他正因为紧张,他才要认真地听阿春讲,阿春是个老移民,她的经验比金子还可贵。
“其实,”阿春象是在总结,“你是在管闲事。”
“管闲事?”
“对。”
“谁?”
“你。”阿春肯定地说,“美国的法律,是以人的权力为基本,她18岁了,你就再也没有权力去干涉她的事情。”
“怎么是干涉?”
“是干涉。”
“可她还不懂事,没有成|人呀!”
“从明年开始,你的税务会有一个很大变化。她的一切开支,就再也不会出现你的税单上,你的各种保险,也再保护不到她的头上。她的名字也将在你的家庭里除去。”
“可我不愿意这样。”
“不管你愿不愿意,这是人权法。”
“人权法……”王起明自语。这三个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美国可是你自觉自愿来的,并不是谁请你来的。你来了,就得遵守它的法律。想开了吧!在美国,你是得不到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伦之乐的!”
“难道,中国的一切观念在这儿,都用不上吗?”
“也不是。中国有句俗话,儿孙自有儿孙福:哪儿的黄土不埋人!我倒是觉得,东半球,西半球,哪儿的土都是土。人死了,埋在哪儿都一样。”
这时,她把杯中酒全喝光了。那酒杯,盖住她的脸,在玻璃杯后面,她的脸是什么表情,谁也看不出,谁也猜不到。
王起明也跟着灌了一口。
“你该走了。”阿春说。
“你赶我走?”
“不。让你太太一个人支撑一个厂,不合适,尤其是在这个关口。”
“你的店怎么样?”王起明换了一个话题。
“唉,一团乱麻,一笔糊涂帐!”
“你的个性,根本不适合与人合股。”
()
“独资?钱呢?那两个混蛋股东倒是想卖股子,可他们头期就要十万现金,这不是成心难为我吗?”
王起明拉开房门说:“阿春,我觉得,生活里要是没有你,我很难支撑下去。”
“少说废话!”说着,阿春把王起明推上轿车。
几天之后,阿春收到了张10万美金的支票。上面的签字阿春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王起明。
她看着那龙飞凤舞的签字,站立良久。
15
Jerry,也就是王起明为宁宁买的那只小白狗,长大了。
这种狗长成之后,体重也就是在七到八磅之间。可是它的毛却能长到十英寸长。
它全身雪白,找不到一根杂毛,只有鼻头是黑的,伸出来的小舌头是红的。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室内玩具狗。
Jerry的血统是高贵的、无可怀疑的。在它的出生卡上,注明着可以追溯到宁的前六、七代都是一个家庭,一个血统。为了保证这一点的容置疑,在它的出生证明上,有饲养人的签字,有贩卖人的签字,还有狗的编码,政府有关部门的钢印。
因为这是美国。
狗,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人皆共知。不过,狗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恐怕只在Jerry进门之后,王起明和郭燕才真正认识到。
买狗的时候,王起明填写了厚厚的一打表格。
买主姓名、住址、电话,最重要的是在狗的名称之下,要填明王起明的社会安全号码。
从此以后,起码在表格上,他和这条狗相依为命了。
王起明当初买狗的动机,只是想借此把宁宁套在家里,吸引住她,不要让她往外跑。
女儿没有套住。
该留住的没有留住,狗却真正地在他家安营扎寨了。
狗带来的麻烦可是真不少,照着王起明的话,他们哪是买回一条狗呀,整个请回来一个活祖宗。
每个礼拜,他至少要收到二至三封信,有生物保护协会寄来的,要求他写出Jeery近况的文字报告;有Jerry的医生来的信,通知他哪天哪天又得带它去打防疫针了;也有的信是它的美容师寄来的,说它该去剪毛整容了。还有可乐可气的是狗俱乐部写来的,信上模信出狗的口吻,请Jerry去参加舞会,还要注意:请穿晚礼服!
郭燕不会开车,所以,他一天于晚就带着这个长毛的狗祖宗,东跑西颠,忙得不亦乐乎,哭笑不得。
最叫他头疼的是,有了这条狗,他们俩口子出远门就得合计半天。
带着它吧:狗食、狗衣服、狗笼子、狗玩具……加起来,比他俩带的行李加在一块还得多;不带它吧,那决不能把它锁家里,它一叫没人管就是他俩的罪过,得送到狗旅馆里去,一夜比住个人贵出去不少。
最后,他们决定把它送到狗旅馆去。尽管费用贵得让人咋舌,可总算轻松,总算是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