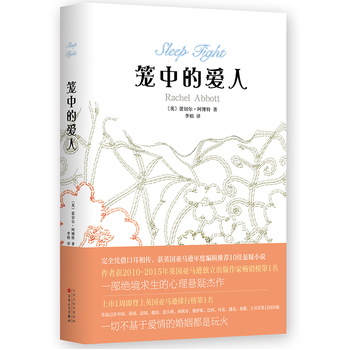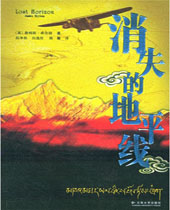消失中的江城-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毕业礼服,站在哥伦比亚的红砖楼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轻得多,面带微笑。他的胳膊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校园看起来明净干洁。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徐先生自豪地说。“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国人,但她在美国长大。”
“他们曾经来探访过你吗?”
“没有,”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弟弟。”
他说完后,那堆信显得更沉了。我正想问到他们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儿插话了,问到我觉得在纽约大学教书可以挣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说。“但那是个很好的大学。也许他一年至少挣五万美元。”
“他也有一辆车,”徐先生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我说。
“一辆车花多少钱?”
“看情况。通常是一万块多一点。”
“那他的工资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里他不怎么提到钱。”
“唔,我想他们的房租会很贵,你知道。在美国生活的开销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纽约。”
“他的岳父给他们买了套房子。也许他们可以存很多钱,是不是?”
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但看上去,他们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在美国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他们问我如何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还问我在美国教书是怎样。我们聊了一会儿政治,而徐先生问了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边上,没什么问题比这个分量更重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去过台湾,所以我并不了解。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想?”他继续加压。
“多数美国人也不很了解这个问题。我想多数人希望和平。”
“他们认为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不是?”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改换了发音——每次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总是想用“他们美国”,而不是“我的美国”。那是一个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区别,但我依然觉得很难回答他。
“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说。“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经济。但美国人知道它的历史与文化和大陆一样。也许他们觉得它应该回归中国,但只是在台湾人准备好了的时候。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满意了。我想向他问问那个兄弟的情况,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换个时候跟孔老师谈比较安全。我问徐先生丰都过去是怎样。
“当毛泽东当领导的时候,”他说,“所有一切都很糟。我们不能跟像你这样的外国人说话。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权利。但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现在好些了。”
这跟我经常从四川人那儿听来的一样,只是徐先生对毛的观点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邓小平的画像,显眼地挂在电视机上方。
在我们渡江时,徐桦告诉我她会开车。我们在一条老旧的电动渡船上往南岸区,那儿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设当中。当时我们正在谈些别的话题,突然间,徐桦告诉我她懂得开车。
我在涪陵已经住了很久,足以明白这一点值得钦佩。“是为了你的工作吗?”
“不,”她说。“我在业余时间学的。”
“就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爱好。”
“那肯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贵。”
“在厦门要贵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块钱,上培训课。但我想有一些我会有能力买车的,所以我想要现在就去学。这就像你们美国——美国人不是都有车吗?”
“是的。即便学生都有——我在高中时就买了一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上升那么快,最终人们也会有能力买他们的车,就像你们美国人那样。”
渡船的长江的心脏缓缓摇摆着前行。我眼前短暂出现了涪陵二十年后的交通景象,相当吓人。徐桦继续说着。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尤其是纽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出差,为我的公司。”
几个星期后,我跟孔老师上课,问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释说,徐先生的父亲是从武汉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国民党派了他去成都做电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后,他被调取了台北,那是台湾的首都。他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后,跟丰都的亲戚在一起。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孔老师解释说。“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
“两个孩子没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们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想要读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厂里找份好工作,他们都没机会。在政治会议上,每个人都批判他们,即便他们都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到了改革开放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写信,看看他父亲是否还活着。198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死是活。他们开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亲回到大陆,探访了他。他在台北有个好工作,在电信公司——他在那儿的地位跟大陆的高干差不多。他又结了婚,在台湾分离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迫害。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电厂里得到一份工作。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谈到文革。”
我想着那个丰都的老人,还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经历常常是这样——我和人们交流摩擦很久,才对于他们过去的混乱经历获得一点点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了今天这样子。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之前的,之后的——战争,台湾的分离,文革;大坝,新城;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手机,她的驾驶课。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从开始到结束,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挂在他电视机上的邓小平像,我记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国红酒时,他女儿从厦门带来的。很显然他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庆祝里昂贵的一部分,于是他担负起义务来喝了,直到空杯。在那之后他女儿又满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顺堂,涪陵上城区的要道。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他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们往往会听从他的话。偶尔夜里那儿会有争吵——有时在客人与摊贩间,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摊贩们之间,他们已经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划下了一定的地盘。在夜里,道上会有很多人,而一个像张先生那样卖烤肉的,可以一晚赚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儿卖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边利润低。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
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顺堂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
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
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
(有一个说法,来自电影学院一个老师,他叹道:中国人的尊严底线比较低。何伟的反应,正是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这大概也算文化差异的内容之一。可能那个侵犯何伟的人只当是开玩笑,虽然是一个很烂的玩笑,他却不会意识到,在何伟看来,这是触及尊严,而变得如此严重。
以我的经验,有些时候一群熟人聚会,往往会拿某人取笑,玩笑话会说到伤人的地步,但却不破坏气氛,从不会有人当场翻脸。这是否也算尊严底线不高的表现?)
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
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