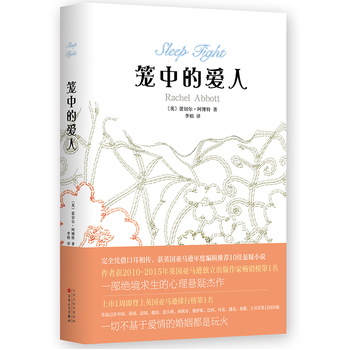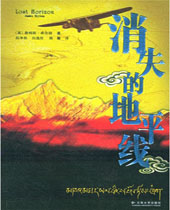消失中的江城-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时间,亚当最好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她远远超过其他学生,无法相比,这种智力上的距离所带来的某些东西,让她在社交中疏离开来。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一个人打发时间,她经常跟亚当或我说话,以练习她的英语。在那个学年的尾声,她看起来相当抑郁,之后,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错过了期末考。
在第二年初,亚当头一次上课时点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亚当问她是否病了。有几个学生摇摇头。没人说话。
“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
“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
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
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
(这些数字从哪里来的,何伟没有解释。关于女性自杀的数字,我觉得显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国信息不太透明有关。在全球来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
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
偶尔,她给我发较长的信,其中一封标题为“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她可以影响他,给他自信,带领他,让他兴奋,她可以让怯弱的人勇敢,让软弱的人坚强。这都归结于女人发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可以影响,鼓励,给你作为榜样,以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让你一生受益。男人应当进入这所学校,来修炼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强有力的。
涪陵的女性似乎远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丧,但我难以找出这不快乐的背后原因。两性关系是难以充分了解的,因为这些是敏感,私人的话题,而我是个外来者。但即便从我的这种远距离,我也察觉到了一个巨大鸿沟,在当地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体验之间。
我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与金钱关系上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钱乃是雄性的——我总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程度上,它还跟代表了当地男性气质的穿着规则产生了连系。城里的男人几乎从来不穿短裤,不管天气多热,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小心地穿着西式风格的外衣(西装),把牌子的商标显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穿着闪亮的丝绸衬衫,轻薄宽松的聚酯纤维的裤子。他们把B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
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
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奇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
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
(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