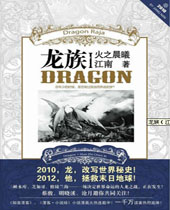龙族-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铁翼苍白的双颊抖然涌上几分血色,他知道潘志刚指得是什么。他觉得自己无法再
正视潘志刚夺夺逼人的目光,便慢慢地转过脸去看正被带进来的刘楠。刘楠拼命地挣扎
着想摆脱挟着他的那两个武警,并哭着喊着大叫冤枉。人怎么会哭?铁翼问自己。人不
该哭么?他不知道。陆仁伸给他一只温暖的手,他牢牢地抓住。陆仁的手坚定有力,他
很感激。
“我冤枉啊!冤枉!”刘楠挣扎着,他知道自己肯定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所以更
加恐怖,“我早就改好了!早改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死?为什么?!”
老警官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刘楠!你老实点,待会儿说不定给你个痛快!”
刘楠无助地四下望着,突然,他看到了铁翼:“他,他才是真正的坏蛋!为什么不
杀他?只要他在,这座城市就不会安宁!杀我有什么用?杀了他,杀他吧,东山做了六
七十年的黑道,六七十年。他们没有洗手,别信他们的,我才做了六七年哪,天哪,他
们……”
啪!
重而迅速,铁翼的动作的确让潘志刚佩服,他跟去年比起来有了很大的进步。当铁
翼踏前一步时,谁都不知道他迈着一步是要干什么。他走得从容,稳健,文明。而后他
扬手,刘楠便从紧抓着他的武警的手中飞出去,摔在地上。屋中的人都怔住,谁都想不
到他会当满屋警察记者的面打人。潘志刚和那位老警官都怔了片刻,他们明知道这是不
可原谅的行为,但也不觉得这个嘴巴打得有什么异样。铁翼的表情一直是默然的,他打
刘楠似乎不是因为冲动或是想制止刘楠说下去。他仅仅是要这个人冷静下来,看清楚面
对的是谁。这个时侯请铁翼出去才是最恰当的作法,潘志刚想着,但这里不是他的职权
范围。所以,他转过脸去看老警官。老警官若有意若无意地低下头,闭开他的注视。这
个潘志刚年仅二十六岁就升职围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不但本身才能卓越,背后还有
着强大的靠山,在军警两界都有着庞大的关系网。但老警官不怕他,去年局里自建国以
来最大的一次请洗都没能动摇他在这里的根基,他认为自己忠于职守,没做过对不起良
心的事。铁翼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财团,他对铁翼不得不禁小慎微,所以他表现出没看
到刚才那一幕的样子,低头做自己的事。
侯深在两名武警的看护下稳步走进来,他听着老警官为他宣布罪状,一直没说话。
在他看来,一切都不重要。也许是因为他过去的岁月足够的好,他不需要再多活几天。
终于,警官示意武警为他取指纹。他转过脸盯着潘志刚,似乎要把他牢牢地记住。潘志
刚咧开嘴笑了,去年他刚抓到猴子的时侯,这家伙在审讯室中舞舞扎扎地装老大,被潘
志刚打断了两跟肋骨。从那以后,猴子每次见到他都是这种表情,他早就习以为常,不
怕猴子在心里咒他。人他妈的要是能被咒死,这世界早就清静了:“操,你就是挨揍没
够,以为你还是市长秘书哪?”
侯深没理他,把脸转向铁翼,向平常见面那样打着招呼:“五哥。”
铁翼点点头:“深哥。”
两名武警架住侯深要把他带走,侯深猛一用力挣脱了他们:“我正跟五哥说话,不
给我面子,还不给五哥面子?”
武警们看看老警官,又看看潘志刚。老警官求助地望着着个年轻的刑警队长,他快
退休了,不想着惹任何麻烦。潘志刚点点头:“最后的要求。”
侯深盯着铁翼:“五哥,四十年前这座城市的人就给了你们家最高的敬意,我们延
续了下来,为的是你们维护着这里的道义。我就要死了,出卖我的人却有花不完的钱而
且可以好好地活下去。这公平么?”
铁翼慢慢地低下头:“深哥,公平这个词不是说给你听的,也不是说给我的。我们
本来就活在公平之外。所谓的道义,也是过去的人造就的。到了我们这一代,道义的概
念只剩下两个词:生命和金钱。一切都过去了,深哥,一切。”
侯深无声地笑了:“是的,一切。五哥,生命是短暂的,有时侯,我相信世界上真
的有什么天堂和地狱。我也相信,我们是同一种人。不用说什么永别了,再见。”
铁翼也笑了:“好啊,再见。”
潘志刚很有兴趣地看着侯深被带下去,又转过脸用同样有兴趣的目光看着铁翼:“
我在想,如果你现在就死的话,我可以陪着你。”
“你可真让我受不了,你能陪我多久?我要去的是天堂,你要下的是地狱。道不同
不相为谋,抱歉。”
“是我让你受不了还是你让我觉得恶心?我甘愿放弃光芒四射的天堂之路陪你,你
却拼命往好人堆里挤。挤得进去么?当上帝是傻子?”
老警官拿起最后一本卷宗,叫最后一个名字:“曾秋山。”
曾秋山曾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绰号:南三儿。铁翼和潘志刚同时把头转过去盯住押解
罪犯的那扇门。
两年以前,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明媚的阳光懒散地照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连
纯化区蹩脚的小巷也不放过,似乎在提醒路人看清他们所生活的环境。
上午十点半,市中心九盘区一条不算小的街道上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人匆忙忙
地向九盘商场走去。在经过一个棵树的时侯,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他回过头,身后
是四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其中一个拿着随便哪个工段都可以拣到的钢筋,那段钢筋的长
度也很扑通,越一米左右,它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钢筋的前端明显地保留着人类加工的
痕迹:打磨得很锋利,发着吓人的金属光泽。而这个尖端正逼在青年人的左胸上。钢筋
另一端的少年显得很羞怯,至少很有些不好意思:“大哥,您看,我们兄弟最近手头不
太方便,能不能借点钱花花?我们宽裕了就还您。”
青年人脸色苍白,一双手也在不地抖动。少年伸出左手在他干燥的唇边抹了一下,
又擦在钢筋的尖端:“大哥,您好象病了,烧得不轻啊。”
青年人用颤抖的手把钱取出来:“我,我还要,买点东西。”
少年大方地笑了:“萧重,给他留点。”
叫萧重的少年一把从青年人手中抢过钱,随手分成两份,把少的那份递回去:“够
么?”
“要,要三十四块。”
萧重又抽出十元塞进他手里:“留点钱坐车回家,别都花掉。”
“你走吧。”拿钢筋的少年始终笑容不减。他知道,借钱的时侯不能太凶,不要激
怒对方,也不要让对方受到过分的惊吓,这样被抢的人就会很快忘掉这事儿。就算是记
得,也会庆幸自己没被抢光,甚至四下里去吹嘘说他如何如何的机智,如何如何的处理
得当,不但没被放血,甚至还多保留了十元钱。
萧重看着那人走远:“你他妈傻呀还是颠呀?在这时侯叫我名字?小心点对你有好
处,把家伙收起来,人们早就看够了。”
王耀宾干咳一声,他不喜欢萧重说话的语气,但他却怕萧重。因为这一切都是萧重
交他的,萧重干这行时间比他长,经验比他多,而且最近还交他如何泡女孩子。所以他
收好钢筋:“还要干吗?”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各回各家,晚上老地方见。”
下午两点,陈加抱着一支台球杆在丰华台球室里转来转去。他盯上一个人,那是个
他从没见过的新面孔。那人长着一对环眼,络腮胡子,虽然凶巴巴的,但打球很投入,
每进一个球都要欢呼,甚至跳跃。但这大胡子的球技可不值得恭维。陈加慢慢地踱过去
,把台球杆依在窗下,扶着球案装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脸上还有很欣赏的表情。打
球的人见他这副神态当然很高兴,进球的积率也就高了些。又过了几分钟,他们终于打
完这杆,大胡子赢了,他高声叫着台主摆案子。他的对手在陌生人面前输了球有些不大
舒服,嘟囔着不愿再打下去。大胡子有些扫兴,问陈加:“打一杆?谁输了谁付钱?”
陈加有些不好意思:“我不太会打。”
“你拿着杆子,总要打球的,就案子钱。”
陈加思索片刻,点点头。第一杆他输了,第二杆也没有赢。但两杆都只输到一两个
球。似乎他同那个人的水平差不多,每次输得都很冤。陈加的脸红起来,眼中的光芒也
很复杂,分明是不服:“咱们挂一杆,这么打我没兴趣。你敢不敢?”
“哈,我不敢?十块?”
“十块!”
陈加赢得很小心,没人能看出他的水平很高,偶尔打个漂亮球,别人都认为他只不
过是运气好。
三杆过去,那人当然不服:“一百?”
“好。”
再开杆时,陈加拿出他所有的水平,他已经赢了三十,再赢掉这一百,足够了。他
急着吃庆功酒,不想再耽搁下去。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杆他居然输了,那人的点子很幸,
一杆竟然挑了七个球。陈加当然不能放这个人走:“再来一杆?”
再开杆陈加无言,他终于看出了眉目:对方可以打出五个点,而且力道掌握得相当
巧妙。他上当了,不是他在套别人,而是这个看起来对台球游戏很投入的人在套他。陈
加放下杆,无言地看着台主将一百元递给那个人——丰华是他的地盘,他可以留住这两
个人,但他没有,这不是钱的问题。
大胡子和他的同伴很高兴地回到自己的地盘,吹嘘自己的杆子如何如何之高,而丰
华的那个人不但杆子高,而丰华那小子输了钱连留都不敢留他——本来他是带着家伙去
的,结果没用上。他们正口沫横飞地说着,门被踹开,进来八个拿着军刺和菜刀的人。
菜刀是旧的,它们在表明自己的主人惯于此道。谁都知道旧菜刀切肉也许不太好用,但
砍人却是好家伙。屋中一共有五个人,全怔在那里。陈加面带微笑,既文明又礼貌地问
道:“您贵姓?”
大胡子惊慌的神态慢慢消失,他认为陈加既然没有马上动手,那么一切都还有商量
的余地:“我叫余富生,朋友们都叫我快手。兄弟别表现得这么冲动,我是三边的人,
你总该知道三边是什么地方吧?”
陈加点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你叫快手,是三边的人。我姓陈,叫陈加。”
快手脸上的微笑立刻消失了。他知道,近两年市里涌现出很多敢打敢拼的人:大阴
子,小阴子,李跃辉,王耀宾,金鹏展,再有就是这个陈加。陈加从兜里掏出二百三十
元扔在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