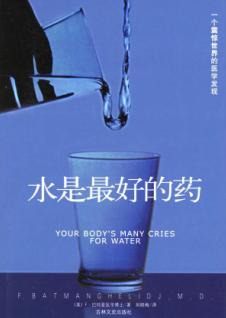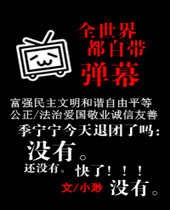全世界最好的你-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野猫也轮不到你多嘴。你以为你就比我好得了多少?余成东不要你,你也不过是条丧家之犬罢了。”南桥一字一句地说。
沈悦蓝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你说什么?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南桥拿起一本杂志,坐在沙发上埋头看书,不再理她。
沈悦蓝胸口大起大伏好一会儿,不知为何又平静下来。
她踏着高跟踢踏踢踏往外走,走到一半时又似乎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对南桥微微一笑:“哦,对了,不知道你看了这期的《时代》没有,报道里有易嘉言和罗格先生共进晚餐的消息。”
南桥没抬头,也没有搭理她。
“你都不好奇吗?”沈悦蓝挑衅似的抬高了嗓音,“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提前看一看他的新欢长什么样,又是什么来头,总好过不明不白就被人抛弃了,还连情敌是谁都不知道。”
她又一次趾高气昂地退场,仿佛这番话就代表她赢了,毕竟在她眼里,南桥也不过是条丧家之犬罢了。
店内又岑寂下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气息。
南桥起身往点外走,服务员叫住她:“诶,小姐,您的袖扣——”
“我一会儿回来取。”
南桥头也不回地走出商店,一路走到了不远处的报亭。
“一份《时代》。”
她气息不稳地展开那份新到手的报纸,时尚版块,头条新闻,彩色的照片上,易嘉言笑得温和有礼,一身灰色西装处处彰显着他的雅致从容。
而在他身侧,罗格先生的对面,有一个高挑美丽的女人挽着他的小臂,一身晚礼服将美好的身材凸显无疑。
她飞快地阅读着文字内容,终于找到了那句话——
“……陪同易嘉言出席此次晚宴的是风原集团的董事千金,卢雅微,年纪轻轻就已拿到剑桥的金融法律双学位硕士。听闻风原集团的卢总早有意向将女儿托付给易嘉言,如今看来,大概传言属实,小编认为两人确实很般配……”
南桥出神地看着那张照片,很久也没有动。
最后她合上报纸,一下一下把它折成了小方块,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报亭老板莫名其妙地看着她的举动,而她却浑然不觉,只是一边往回走,一边拿出手机再次拨通了易嘉言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她就直截了当地问:“昨晚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回我?”
那边的人一愣,听到是她的声音,又低声笑了起来:“是你打来的?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找我有事吗,南桥?”易嘉言的声音总是那么温柔,像是来自遥远的天际,那泛着鱼肚白的温柔黎明。
南桥拿着电话,定定地站在原地,问他:“昨晚接电话的人是谁?”
其实他答话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几秒钟时间,于她而言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心脏仿佛是搁在砧板上的鱼,待人宰割。
直到他说——
“卢雅微,我的同事,也是我顶头上司的女儿——”察觉南桥态度有异,他反问一句,“怎么了,南桥,有什么事吗?”
卢雅微三个字以后接的称呼是“我的同事”以及“顶头上司的女儿”。
南桥的心蓦然一松,仿佛压在身上的所有重担都烟消云散。
不是女朋友,只是同事。
不是未来嫂子,只是上司的女儿。
她忽然间大笑出声,一边笑一边跑了起来。
易嘉言在那头莫名其妙地问她:“怎么了啊,南桥,在笑什么?”
笑什么?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但她发誓,这一刻真的是她人生里最快乐的一刻之一。
不,不,没有之一!
☆、第19章
在你的生命里也许有这样一颗星星,它触摸不到,遥不可及,可是你一抬头总能看见它。
它那么亮,那么灿烂,好像有与全世界的钻石媲美的光彩。
很多年以后,南桥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
原来她想要得到那颗星星。
想要摘下它,藏起来,从今以后都不让别人觊觎。
易嘉言就是那颗星星。
拿到袖扣回家以后,南桥的脑子里一直回荡着沈悦蓝的话。
“南小姐,做人贵在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你别以为仗着易嘉言一时宠你,肯冲冠一怒为红颜,你就真的是飞上枝头的麻雀了。你顶着这张脸,难不成还真能拴住他一辈子?”
“他如今对你好,只是因为高高在上,生活无忧,所以看见路边受伤的野猫野狗,同情心泛滥了,忍不住拉你一把。像他那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他得不到?等他见得多了,发现你不过就是个摇尾乞怜的小野猫,你以为他还会继续留在你身边,吃饱了撑的保护你?”
她一边为易嘉言还没有女友而喜悦,一边却又反复想起沈悦蓝的这番话,心里像是傍晚的潮水,起起落落。
最后忍不住给沈茜打电话,却得知沈茜在远冬看靳远的演出。
“怎么想起去看阿靳了?”
那头一片嘈杂,南桥把手机拿远了一些,听见沈茜反问了一句:“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走就是那么多年,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不说,再见面也依然不把他放心上?”
南桥一怔。
“沈茜……”
“废什么话呢,赶紧过来啊,就差你了呢!”沈茜的声音一下子又大了起来,还是老样子,总爱嚷嚷,听着很凶,但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南桥松口气,刚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好,我来。”
已是晚上十点,南桥难得出门这么晚,临走前妈妈再三追问。
她只说:“沈茜和阿靳在外面吃宵夜,叫我一起去聚聚。”
并不敢过多透露靳远的职业,毕竟搞摇滚和混酒吧这种东西向来不为长辈所接受。
赶到远冬时,靳远已经没有再唱歌了。沈茜和大春胖子他们一起坐在角落里喝酒,靳远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南桥走过去,问了句:“阿靳呢?”
“喝多了,外面吐呢。”沈茜指了指侧门。
“你们都不去看着他?”南桥的语气有些埋怨的成分。
大春呵呵笑:“就指望你来看着他,我们看顶个什么用啊?”
胖子跟风附和:“那可不是?你又不是不知道阿靳的脾气,从来就没人真的能劝得住他,除了你。”
南桥没动。
胖子推她一把:“快去快去,真要他倒在外头你才去啊?”
南桥顿了顿,然后往侧门外走去。
大概是从初三那年,靳远的阿婆去世开始,大春和胖子就开始把她视为靳远的女朋友,不管她怎么解释,他们永远都乐呵呵地开着她的玩笑。发现解释没有用以后,南桥索性也就不再解释,随他们说。
那年夏天,靳远在某个黄昏演出完回到家后,发现阿婆已然没有了呼吸,只剩下床上那具干枯冰冷的躯体。
老人家其实病了很久了,医生也说过就是这几年的事,靳远早该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至亲离世这种事情,就算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又如何?有的伤口不是说不痛就不会痛的。
那天晚上,南桥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听见大春和胖子在外面叫他:“南桥,你出来!”
声音很急促,吓南桥一大跳。
她赶紧把手从淘米水里伸出来,在门口的帕子上随意擦了擦,然后跑出了门。
院子外,胖子满头是汗,大春的脸色也很难看。
“怎么了?”她迟疑地站在门口。
却听大春哑着嗓子说:“阿靳他,他阿婆走了……”
南桥扶着门框,心一沉,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最后她艰难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
“应该是下午的事。刚才演出完了,我们一起回家,阿靳进屋后我们就走了,没走上几步忽然听见他在屋子里大叫阿婆,赶紧跑回去看,结果……”胖子和大春面面相觑。
“那他现在在干什么?”
大春说:“他一声不吭,好像丢了魂似的,抱着他阿婆不肯撒手,我和胖子怎么拉都没用——”
“胖子那身肉是拿来干什么用的?阿靳那么瘦,拉他都拉不动吗?”南桥急道。
胖子委屈极了:“可是他打我!我去拉他,他又抱着他阿婆,阿婆差点就从床上掉下来,他回头就是一拳……”指了指自己那发乌的颧骨,胖子都快哭了,“他下手可重了,我根本不敢拉啊!”
南桥正准备跟他们一起赶去靳远的家里,却不料父亲忽然回来了。
醉醺醺的男人指着大春和胖子质问她:“他们是谁?在我家院子里干什么?”
大春说:“我们是南桥的朋友——”
“你不是桥头那个老王的儿子吗?搞,搞摇滚的?”男人揉揉眼睛,“你个小臭流氓,不读书,还来骚扰我女儿?”
拎着酒瓶子,他一个箭步摇摇晃晃地冲过去就想打大春。
“爸,爸爸!”南桥吓得赶紧冲上去拉住父亲。
“你,你给我少罗嗦,回,回屋去!”男人推推搡搡地拽着她往屋子里走。
“爸,我好朋友的阿婆去世了,我得赶去看看他——”
“他阿婆去世了关你什么事?他算哪根葱?这些流氓玩意儿,敢来找我女儿?”男人开始骂骂咧咧。
那一夜,南桥被父亲关在屋子里,压根出不去。
大春和胖子赶回去陪靳远,南桥就心急如焚地在窗口张望,不知如何是好。
这些年来,阿婆一直体弱多病,靳远四处打工,所有的收入都拿来给阿婆治病。可是他能力有限,阿婆的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他受了苦不说,阿婆的病还越来越严重。
南桥是知道的,阿婆对靳远来说就是人生的全部。
他的父母从他小的时候开始就去了北方打工,后来音讯全无,有人说是死了,有人说是过上了好日子,就忘了家里这两个无关紧要的拖累。
靳远从小到大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阿婆。
天蒙蒙亮的时候,南桥听见大春在外面小声地叫她,跳下床,她扒着玻璃窗朝外看。
大春说:“你能出来吗?”
“房门被我爸锁了。”南桥不知所措。
“能从窗子那儿爬出来吗?”
“窗户是锁死了的,打不开!”
大春像是急得要命,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四处寻找什么,片刻后捡了块砖,照着窗户就砸了下来。
南桥往后退了两步,听见咣当一声,玻璃碎了。
大春拿着砖又是几下,把周围的玻璃一起敲掉,伸手来拉她:“快点,快出来!”
南桥听见父亲的打鼾声停止了,像是被巨响惊醒了,他开始扯着嗓子喊南桥的名字。
她吓得一把抓住大春的手,也不顾窗棂上尖锐的玻璃碎片,想也不想地就往外跳,然后在沉沉的黑夜里不顾一切地狂奔起来。
就连自己的手臂被划破了好长一条口子都不知道。
凌晨四点半,南桥到了靳远的家里。
那个家阴暗潮湿,味道很不好闻。屋子里暗沉沉的一片,没人开灯。
她看见那个身躯单薄的少年直挺挺地跪在床前,抱着老人的身体一动不动,像是一株寂静的白杨,活得无声无息,活得卑微迷茫。
大春说他死也不肯松手,谁劝也没用。
南桥站在那里许久,才慢慢地叫了一声:“阿靳。”
靳远没有动。
她走近了些,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阿靳,你把阿婆松开,她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