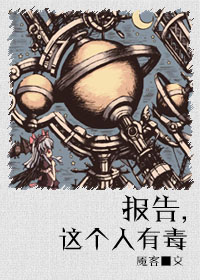巴黎之梦 作者:[法]乔治·西姆农-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序:西默农和他的梅格雷探长
乔治·西默农是比利时的著名作家。1903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列士市,1989年在瑞士去世。15岁因丧父失学,16岁进《列士日报》做记者,同年发表处女作《在拱桥上》,被誉为少年天才。1922年西默农赴法国巴黎,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一生共写了431多部小说,绝大部分是侦探小说。1929年他创作了第一部以梅格雷探长为主角的侦探小说《怪盗鲁通》,1972年以《梅格雷的最后一案》向读者交代梅格雷探长光荣离任。在这43年里,西默农共创作“梅格雷系列探案”小说112部,代表作为《黄狗》、《十三个谜》、《十三种神秘案》、《上帝的车夫》、《雪是脏的》、《骗局中的骗局》等。
西默农的侦探小说在欧美众多流派中独树一帜。在他的小说里,罪犯的心理因素上升到了重要的位置,他利用人类畸形的丑恶心理作为小说情节的悬念基础,对人物内心世界加以细致的剖析,从而使小说的人物形象充实而富有立体感,并增强了作品的社会性与审美性。阅读西默农的小说,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人物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以及由此呈现出复杂的人性图景。西默农的侦探小说,其悬念并非产生于案件本身,而是来自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变化,因此,西默农的侦探小说又被称为心理悬念小说。
由此,我们看到了西默农小说与古典侦探小说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在西默农笔下,梅格雷在破案中,不像杜宾与福尔摩斯那样在案发现场仔细寻找诸如脚印、指纹、烟灰、毛发等细微的物证,然后由此产生超乎常人想像的严密推理查处真凶。梅格雷破案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研究对方的心理活动,在他看来,只有那些不正常的人才会牵涉到刑事案件中。因此,在他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总是广泛地与案情相关的人接触,从中得到与嫌疑人或被害人相关的信息。他谈话的对象很广泛,有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亲戚、朋友,有佣人、出租车司机、店员、酒吧老板、邮递员等等,有时甚至还会悬赏寻求信息。当他得到充足的信息时,梅格雷就会在大脑中加以细致分析,理出头绪,把握住当事人的心理特征,从而为破案找到正确的途径。梅格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侦探也可称得上是一位睿智的犯罪心理学家,他深知那些罪犯的内心世界,因而他能以此为线索,顺利侦破一起又一起疑案。
诚然,梅格雷探长的凡人品格亦是西默农侦探小说的一大看点。梅格雷是以反传统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侦探小说的园地里。他既不是神机妙算的古典派侦探,也不是虎胆英雄式的硬汉侦探,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位长着肥嘟嘟的下巴与宽宽肩膀的胖老头,他与手下关系极融洽。他习惯称年轻探员们为“孩子”,而探员们也亲切地叫他“头儿”。梅格雷的情感十分丰富,当案情棘手时,他的情绪会变得很糟,而当案件有了进展时他就会到附近的酒吧喝上一杯庆祝取得的成功。他对朋友、被害人甚至罪犯都倾注了各种不同的强烈情感,使其凡人品格更显个性。梅格雷身为警察局刑事侦缉队的队长,在很多人看来,梅格雷应该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手下去破案,可是梅格雷总是亲自出现场。每次侦查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人生的经历。
除此之外,在梅格雷身上还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每当逮捕罪犯时总是带着无奈的情绪,因为梅格雷清楚地意识到,有那么多人为了不同的目的以身试法,其主要根源在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他对那些为生活所迫而犯罪者往往深表同情。他平易近人乐观敬业,平时这个老头并不比别人高明,可一旦在侦查中他常常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尤其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精确的把握更令人敬佩。读者在阅读“梅格雷系列探案”时,往往不会将梅格雷当做作品中的人物而情愿把其看成邻家的警察大叔。梅格雷身上体现的平民素质和闪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得他为全世界读者所喜爱与尊敬。以至荷兰人民为其铸造巨大的雕塑作为警探的象征,永远地伫立于德尔萨市广场。
第一部
第一章
为什么刚才脑海中浮现的尽是女儿的形象?他感到有点不自在,或者说,是在火车启动之后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不大自在的。实际上,这只是伴随着车轮的节奏在短时间内产生的感觉,而且立即就被眼前的景色淡化了。
明明他们三人一同站在透过阳光的晨雾之中,为什么眼前出现的只有女儿约瑟,而没有他的妻子及小儿子呢?
也许是刚才在火车站他女儿站在这辆即将启程的列车前面时样子不得体?她今年十二岁,身材瘦高,腿和胳膊又细又长。海水的洗涤和沙滩上阳光的沐浴使她金黄色的头发闪闪发光。
从他们寄宿的人家走出来时,多米尼克曾问女儿:“你开车送你爸爸去车站时不穿游泳衣?”
“为什么不穿?好多人都穿着游泳衣骑摩托。就把摩托停在车站对面吧。送走爸爸,咱们不是直接就去游泳吗?”
多米尼克身穿一条短运动裤,带条的短袖衬衫透出乳罩的轮廓。这衬衣是她在靠近运河的一条又挤又窄的街上买来的。他已经记不得这条街的名字了。
是因为他发觉女儿的胸部开始隆起而感到不自在?
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就象这晨曦的光亮,这水天之间亮闪闪、热乎乎、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水蒸汽。
他们是从利都乘船奔赴威尼斯的。到现在,他的肢体、他的神经还仿佛感到船在颤抖,感到船身在平稳的、长长的波浪中有规律地运动,感到迎面遇到一只船时船身的晃动。
突然,威尼斯映入眼帘。塔楼、圆顶、宫殿、圣·马尔克广场和大运河、威尼斯特有的轻舟以及所有教堂和钟楼上鸣响的大钟都出现在已经变暖了的晨光之中——这是个星期日。
“我可以买支冰棍吗,爸爸?”
“早上八点就想吃冰棍?”
“我也可以买一支吗?”只有六岁的儿子也紧跟着问。
他叫路易,可是从小大家就习惯地称他为“瓶瓶”,因为他要奶瓶时总是这样喊。
“瓶瓶”也穿着游泳服,外面套了件格子衬衫。两个孩子都戴着草编的威尼斯船夫帽,帽顶和帽沿都是平的。约瑟的那顶草帽上系有红绸带,她弟弟的是蓝色的。
也许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卡尔马不喜欢离家外出吧。确实,十五天来他始终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一种失去根基、飘浮不定的感觉,不知道应该依附在什么东西上。
主张到威尼斯米度假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妻子,当然,孩子们也都随声附和。
他对出发、离别这些场面也很反感。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包厢里的落地玻璃窗前。包厢里一点不干净,因为这是挂在这列火车上的唯一的一节从远处来的车厢,是从的里雅斯特或更远的地方来的。它的颜色与其它车厢不同,外观独特,连车厢内的气味也不同。
紧靠卡尔马坐着一位男人,他上下打量着卡尔马。也许在这节车厢挂到这列发自威尼斯的火车上时,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卡尔马的头脑中并没有很明确地在考虑什么问题。他下意识地、有些不耐烦地盯着沐浴在金色晨辉下的月台,站牌左边的书报亭,以及周围的人们。他们都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样,眼睛瞧着自己的亲人或朋友。
一切正常。火车应该在七时五十四分发车,七时五十二分时,一位身着铁路制服的人登上列车,关好车门。与此同时,一位机械师手持小铁锤在车下敲敲打打,依次检查车厢。卡尔马每次乘火车都会看到这种情况,他每每也都琢磨这个人在敲什么,可过后就忘记去问了。
站长从办公室走出来,嘴里含着一只哨子,手中拿把象雨伞那样卷着的小红旗。不知从什么地方喷出一些蒸汽。不,不是蒸汽。机头是电动的。不知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在清洗车闸,总之,它同所有火车一样放出一些气体,引起车身抖动。
总算响起了哨音。约瑟边吮着冰棍——她现在已经用意大利语来称呼冰棍了——边扬起一只手以示告别。多米尼克不停地嘱咐道:“千万要照顾好自己,要到艾蒂安纳去吃饭。”
那是他们熟悉的一家饭馆,就座落在巴第乌里大街,离他们家很近。用多米尼克的话说,那里饭菜干净,食物新鲜。
红旗展开了。站长举起了胳膊。此刻,“瓶瓶”也模仿起约瑟的手势。
火车该开了,时钟正指着七时五十五分。然而,面对着这长长的列车,站长的手势还没打完就又把胳膊放下了,同时还吹出一连串短促的哨音。
火车不能走了。站台上的人都往前面看。卡尔马把身子探了出去,可除了同他一样探出去的脑袋外什么也没看见。
“出什么事儿了?”
“不知道。”多米尼克答道,“我没看见有什么反常的事儿。”
她身腰虽然纤细,当然也不会细过她的女儿。即便她穿着短裤,却仍然不失风度。阳光没能把她的皮肤晒成孩子们那样的棕色,只是把它变红了。那双蓝色的眼睛被一副眼镜遮住。
大家的目光都汇集到站长身上,他却并不显得着急。他把旗子夹在腋下,只管盯着机头看,不慌不忙地、天知道在等什么。整个车站此时好象影片突然定在某个场面上,将一张日常生活的彩色照片展现在人们眼前。
人们简直不知道该把手上已经展开的手怎么办,挂在脸上的告别的微笑突然被打断,继而变成了一副可笑的摸样。
“在等某位来晚了的人?”卡尔马身边有个声音在问。
“不知道,没见到有人往这儿跑。”说话的人把报纸放在长椅上,站了起来。这是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对不起。”他把头和双肩都从窗框中伸出去,把朱斯坦的头和双肩遮住了好一会儿。
“跟意大利人打交道简直没办法。”
他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好好看看多米尼克及两个孩子了。
卡尔马重新坐好,脸上带着一丝勉强的微笑。他看得出约瑟和“瓶瓶”已经多么不耐烦地晃动起身子,急于要跑出这个极热的车站,好跳上车子驰向海滨。而多米尼克仍是忧心忡忡。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朱斯坦。”
“我向你保证一定做到。”
“我看这次火车要开了。”
还有两分钟。在这漫长的两分钟内,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脸上毫无表情的站长。
一位副站长从装有玻璃门的办公室走出来发了个信号,于是站长吹响了哨子,又稍等片刻才摇动了红旗。列车启动了。站台,连同上面一排排的人影开始向后滑动。朱斯坦把身子又探出一些,只见女儿的身影越来越小,她那红色的游泳衣渐渐地同车站上的各种颜色融为一体。
阳光一下子照在了两个男人的身上,并带着一股灼热的空气钻进了车厢。卡尔马叹了一口气,把蓝色的窗帘放了下来。窗帘鼓涨得象一只风帆,上下舞动了两三次才被固定住,启程了。
现在,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余暇来观察他的旅伴了,即便他并没有这样一种欲望。那个人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长椅下。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个男人都装成谁也不去注意谁的样子,所不同的可能是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