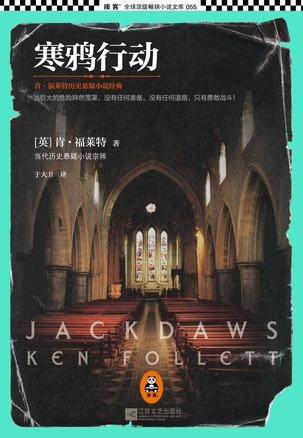烟水寒-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女人是田心,一个歌星!”黎群小声说。他不愿邻桌的之谆听见。
“我知道!”亦筑淡泼地说。她的脖子已硬僵,—阵阵田心的笑声传来,她的心在滴血,还有什么更大的伤害?更恶毒的欺骗?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那晚所做的,只是为了你好!”黎群真挚地说,“我的爸爸就是这样的!”
“我说过,我感谢你!”亦筑不看他,她怕他看见她眼中那些不受控制的泪水,“你对我太宽厚,太好,我想,我是会记得你的!”
“别说这些,”黎群脸上有了笑脸,“婚礼快开始了。”
果然,司仪开始一连串的报告,乐队也奏起乐来,四周的噪杂声低下去,不,是被震耳的音乐声所压低。什么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一个个的站上前面——之谆也不例外,他终于舍得摔开那个田心了。接着,新郎、新娘走出来,掌声雷动,仪表出众的雷文,配上比花更娇的黎瑾,谁不羡慕?司仪又在一连串地说话,但是亦筑什么都听不见,人来人往,盖印,鞠躬,似乎只是些晃动的影子,她眼中只有一个人,就是那含笑而立,风度翩翩,潇洒自若的之谆,他站在台上,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存在似的,哦!怎样的男人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礼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入席,亦筑一直是那么恍恍惚惚的,若不是身边的黎群,她知道自己必会失态,她不是个爱哭的女孩,但是,现在她有要大哭一场的冲动,不是为可怜自己,而是天下竟有如此丑恶的爱情!
新郎、新娘向来宾敬酒时,照例由双方家长陪同,看着他们越走越近,就要轮到亦筑这一桌了,她咬咬唇,挥去那抹恍惚,她个性刚强,绝不以弱示人,别人怎么对待她,她也怎么对待人!今晚第一次,她看清了黎瑾,她穿着粉红色的长旗袍,鬓边有一朵大红花,胸前垂着。—串名贵的翡翠颈链,光彩夺目,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颗巨型的钻戒,十分抢眼,虽是新娘,她已有一分豪门少妇的风韵。只是,她依然那么冷,那么傲,没有新娘的娇羞,却使那经过化妆的脸,突出了她特有的古典气质。
黎瑾被拥着已走向亦筑的这桌,全桌人都礼貌的站起来,亦筑举起酒杯,黎瑾冷冷的目光已射过来,她嘴角有一抹难觉察的冷笑,那似乎是示威,又像在讥嘲。亦筑故意不看她,新婚之日有这种动作未免幼稚。亦筑看见雷文,不由有些吃惊,他虽然在笑,却完全没有新郎应有的焕发神采,是怎么回事?她的目光再移,终于看见那个使人痛恨的人了,之谆也在看她,四目相投,中间似乎只是一片空白,亦筑冷冷的笑笑,不再看他,晃眼中,他的神色变了,笑容里再也没有那分得意。
菜很丰富,一道道的送上来,亦筑吃得很少,毫无心绪。没过多久,新郎新娘已到门口送客了,上千的客人来得慢,散得却快,亦筑跟着人群往外走,黎群始终站在她背后,有—个人气喘喘的跑过来,是雷恩。
“你怎么换了一桌?找了半天才看到你——”雷恩说。一眼看见黎群,他惊觉的,有些尴尬的转开话题,“对不起,我还有些事,再见!”
雷恩走开,黎群冷冷的哼了一声。
“姓雷的都是自以为潇洒,你认识他!”他说。
“不,刚才他替我安排座位!”亦筑没有回头。
快到门口了,亦筑发现之谆并不在送客的行列中,竟有些说不出的失望,她不明白这是种什么心情,她不应该再以他为念的。
“那个穿白衣服的女孩是淮?”背后忽然传来一种嗲嗲的好像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那个什么亦筑吗?”
亦筑和黎群都吃了一谅,立刻,他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除了那田心之外还有谁?他们忍不住回头。
“嗯!”之谆低沉的应着。原来他竟在亦筑后面啊!
“她跟你儿子很不借,对吗?”田心说,“看起来相当配对,就像你女儿和雷文!”
“嗯!”之谆仍不说话。
亦筑完全不能忍受了,她加快了脚步,匆匆朝门口走去,还是逃不开田心那一连串似哼的笑声。
黎瑾又换了衣服,是一袭白色拖地的晚礼服,虽然剪裁、手工都是第一流的,亦筑仍觉得旗袍更适合她些,走到他们面前,亦筑大方的向他们伸出手,她不会记住黎瑾的幼稚。
“祝福你们!”她微笑的、真诚地说。
“谢谢!”雷文握住了她的手。
她再伸手向黎瑾,后者勉强的、极不愿意的轻轻碰了她一下,算是握手。
“我哥哥就在你背后,爸爸在更后一点,我想,无论如何,你总有希望变成黎家的人,”黎瑾压低了声音,笑里藏刀地说,“是嫂嫂或者是妈妈?”她笑了,笑声令人发抖。
亦筑的脸变得发青,她虽然极力想不计较黎瑾,但是,那些话太伤人了,黎瑾以为她只是想做黎家的人?哦!怎样的好朋友?
黎群也听见妹妹的话,他把亦筑推前一步,发怒地说:
“你够了,若不是你今天结婚,我会教训你!”
然后,他拥着亦筑大踏步走出去。黎瑾呆一下,她被哥哥的话所伤,黎群从小没对她这么凶过,难道她做错了?她转头看雷文——她的丈夫,他的眼中也有怒意,这更激起了她的火,为什么男孩子都对亦筑那么好?甚至是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哥哥?
妒火佼黎瑾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的神色在傲然中加上冷峻,她看着之谆和雷文的父亲握手寒喧,看着之谆笑着拍雷文的肩,她扬一扬头,不理会站在面前的父亲,她是有意给他难堪,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
“小瑾,我想——我也应该说恭喜!”之谆向她伸出右手,对这个女儿,他从来都是失败的。
黎理把头扬得更高,她觉得对之谆的难堪就等于打败了亦筑,想着亦筑那次在吃烤肉时的神情,她冷笑起来。
忙乱中,只有雷文注意到她,在许多人的面前,尤其还有他的父母,他不能让黎瑾这么任性,何况,他一向对之谆有好感。
“小瑾,你怎么了?看见你父亲吗?”雷文压低声音。
她勉强的看之谆一眼,对雷文,她仍有—些忌惮,不想惹起他的反感,或者,他是她的丈夫吧!
“不快些吗?她已经出去了!”她冷笑一声,完全不理会之谆身边的田心。
之谆忍住要发的脾气,对黎瑾,他已容忍了二十年,现在她已出嫁,就容忍到底吧!他拉着田心,一言不发的大踏步走出去,似乎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那踩得高高的脚步上。
“你女儿怎么回事?谁惹了她?”田心不满地说,“她说谁已经出去了?”
之谆不理她,对这个眼里只有钱,贪婪而又虚伪的女人,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然而——不忍受又怎样?他的儿子,女儿已为他定了,他只配有这种女人。
通过大厅,他们出了观光酒店,匆匆朝停车那个方向走,之谆走得很快,使田心几乎追不及,他打开车门,正预备上车,一个熟悉的声音令他停住,黑暗中,有一个男孩正对一个女孩说话。
“我很抱歉今晚的事,希望你别介意!”男地说。
沉默了一阵,女的叹一口气,说:
“我虽不是小气的人,若说不介意——是假的,”女的在沉思,“世界上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欺骗!”
“他本是那样一个人,”男地说,“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是长辈,而且——我爱他!”
“也许我今晚不该来的,”女的又叹一口气,“我不知道黎瑾请我来——只是想羞辱我!”
“小瑾的心理永远不成熟,她只是在损害自己!”
田心也到车边,不高兴的拉开车门坐上去。
“怎么回事?失魂落魄的,还不上来吗?”田心嚷着。
之谆一震,下意识的坐回车上,又听见那女地说:
“谢谢你对我说的话,我要回家了!”
“我送你——”男的盼望。
“用不着,我自己回去!”女的明显的拒绝,“你得赶回黎园,而且——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男的失望的沉默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女孩离开了。之谆吸一口气,他用力关上车门,他早已听出来,男孩子是黎群,女孩子是亦筑,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他插嘴的余地吗?虽然他是那么向往的,然而,黎群,他的儿子,也深爱着那女孩,儿子才二十二岁,若他能替儿子做任何事,以换取儿子的终身幸福,即使是牺牲,是死,他都愿以,然而,事情看来并不那么容易!
发动了汽车,他下意识的朝女孩走的那方向开去。谁能知道他今晚是以怎样的心情来参加婚礼?女儿的忌恨,儿子的不谅解,深爱着的女孩又含恨而去,他的牺牲换得了什么?
路边有个踽踽独行的修长女孩,汽车灯光照出了她的孤寂,照出了她的失意,照出了她的落寞,一袭潇洒、飘逸的白衣,包藏着怎样一颗受创、受伤的心了点点鲜血,仿佛都滴在之谆手上,是他,是他,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是那样无意,无奈的撕裂了一颗稚嫩的心,他要负起一切,担当一切的罪过!激动的双手把不稳驾驶盘,眼看着就要向那白衣女孩冲去,田心惊叫起来——
“喂,你怎么回事,不怕撞到人吗!”
之谆一震,醒了,摆正了方向,踏足油门,汽车如箭似的射出去,白衣女孩的身影已消失在烟尘中。
“下面还有什么节目?”田心媚笑。
之谆皱皱眉,极不耐烦地说:
“我送你回家,我还有事!”
“有事?十点钟?”田心双眉一扬,“约好了谁?丹妮?还是香港来的那个迷你小姐?”
“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的,对吗?”之谆恼怒的。
“谁管你呢?”田心不自然的笑。眼前是—条人人都想钓着的大鱼,除了钱多,他还那么潇洒、英俊,然而,没有人能抓住他,他虽不滑溜如鱼,但却捉摸不定。“只是——明天我想去做两件晚礼服——”
“把账单送来,”之谆看也不看她,“你要的只是钱!”
“我也要人,我能得到吗?”田心自嘲的。
“哼!”他冷哼一声,汽车停在一条巷口,“下去吧!”
“真的不要我陪了?”田心试探的笑。
“两件晚礼服,对吗?”之谆毫不动容,“我只要你去参加婚礼,现在你的任务完了!”
田心耸耸肩,无可奈何的下车。
她的职业和交际生涯,使她早已抛弃了自尊心,现实,才是最重要的,参加一次婚礼,换来起码五千元的晚礼服,黎之谆,已算是十分大方的了,她了解自己的身价。
之谆等她没入黑暗的巷子,才重新开动汽车,他不想回家,也没有事,他心中有个热得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冲动,他的手不听指挥的把车子掉回头,朝刚才的来路开回去,他祷告着,紧张的期待着,但愿那白色的身影仍在,然而——在又如何?他几乎是没有考虑的!
马路上空荡荡的,台北市的夜,除了那特殊的几条街之外,仍然是沉静的。寂静的街灯,照着自己长长的影子,越发显出了寂寞。
之谆的汽车开得很慢,很慢,他焦急的在昏暗的路上寻索,他恨自己的视线无法到达更远的尽头——整条街走完了,那白色的身影似乎已被黑夜吞噬,他失望而颓丧,他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下决心?他甚至可以不送田心回家,只要多付一点钱就行了,不是吗?
汽车再一次掉头,他无意识的,漫无目的向前驶着,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