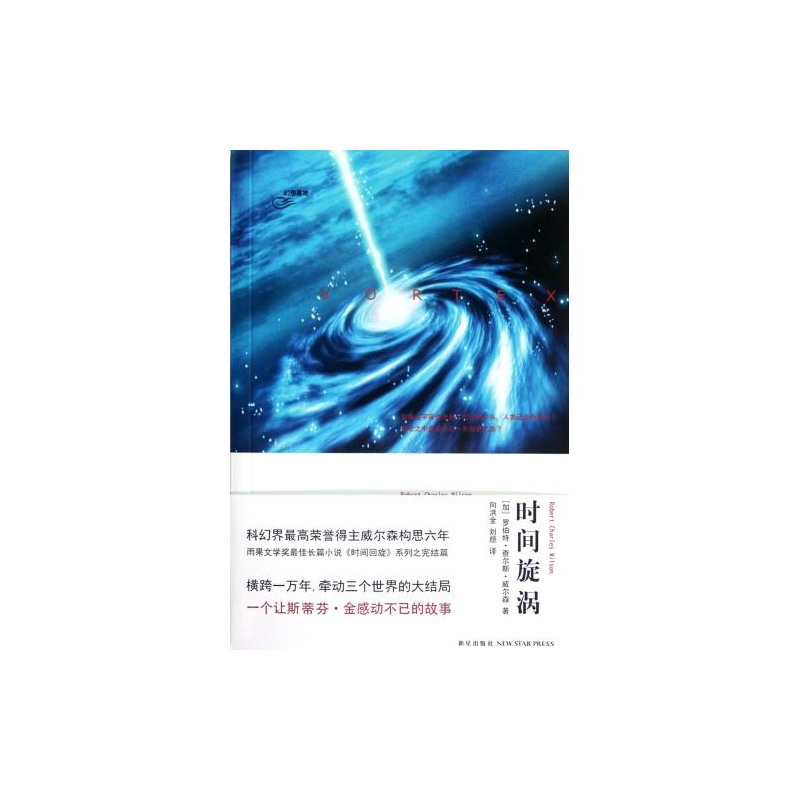谁在时间的彼岸-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转向左思安:“小安——”
听到他叫她,她仿佛被人重击一掌,从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看着于佳,再看向高翔,高翔正要说话'她挣脱他的手,摇摇头:“我什么也不想听,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她猛地转身,拔腿就跑。高翔与于佳一怔,连忙追上去,然而她飞快地进了电梯,关门下去。他们只得等另一架电梯,等他们下到一搂,左思安已经无影无踪。
高翔怒视着于佳:“麻烦你想一想,小安会去哪里?”
于佳沉默了,这是她没法儿回答的问题。
“她有没有带手机?”
于佳摇头。高翔心底一沉,他在纽约已经待了将近三个月,当然知道纽约地铁是全世界最庞大最错综复杂的公共交通系统,有20余条线路,每天载运着400余万人来往于五个城区之间,想在这里面找人,简直像大海捞针。他们能做的,几乎只有等左恩安主动回来。
“于老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对你女儿很残忍?”
“你什么都瞒着她,就是对她仁慈吗?”于佳反问,“如果你真对她好,就根本不应该再出现在她面前,扰乱她的生活。”
高翔气极:“我并不打算一直隐瞒,只是准备让小安慢慢接受这些事情。”
于佳表情阴郁地说:“恐怕有些事情她永远也没法接受的。”
“她只是需要时问。”
“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时间,值得耗费在这样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请问你理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是和你做一样的选择才叫有意义。”高翔怒冲冲地反驳,“于老师,不要用你的人生观来定义你女儿的生活。给她选择的权利,尊重她的选择,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难吗?”
“做出选择的前提是弄清楚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我带她来,就是让她看清这一点。”
高翔知道,某种程度上,于佳甚至比他母亲更固执、更难以说服,他也不想再徒劳地争论,咬牙想了想:“算了,别吵了。我们还是想想怎么找她。”
“这能上哪里去找?她英文没问题,也知道我们预订的酒店。等她自己冷静下来会回来的。”
高翔没她这么乐观,但也只得把自己的手机号码抄给于佳,再记下她预订的酒店:“有消息请务必马上通知我。”
7
左思安一口气从纽约长老会医院冲出来,根本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应该去哪里。
她漫无目的地走着,眼前浮动的全是隔着病房看到的那个小孩子。她当然一直知道那个孩子的存在,只不过上次闯到高翔家里意外看到,她能够马上移开视线;而这一次,她无法控制地呆呆站在那里,看得分外真切。
她的身体曾经被一种暴力的方式打开,一个小生命违背她意愿地寄居在她体内,一点点成形,慢慢长大,撑开她的腹部,微弱却理直气壮地伸展手足,再被取出,长大——成了她今天在医院里看到的那个孩子。
她甚至怀疑那个影像已经烙到了她的视网膜上,再也不会自行消散。她绝望她想,也许她根本不可能从记忆里抹掉这张面孔了,他甚至会闯入她的睡梦之中,成为她挥之不去的噩梦的一部分。
不知不觉之间,左思安走到了中央公园。尽管正值寒冷的冬天,又是圣诞节,但这个值于曼哈顿中心的著名公园并不冷清,有人穿着单薄的运动服沿着慢跑路在跑步健身,有人牵着狗在悠闲地散步,滑冰场上有不少人在滑冰,孩子们兴奋的笑嚷声传出很远。公园大得超出了她的想象,她茫然地走着,一直走到疲惫不堪,同时觉得有些冷,买了一怀热咖啡,在一个小小的湖泊边的长椅上休息。
湖面一半结冰,显得萧瑟而空荡。她突然记起上学期看过的TheCatcherintheRye(《麦田里的守望者》),生活在纽约的中学生霍尔顿曾关心当中央公园的湖面结冰以后,那些野鸭子会到哪里去。霍尔顿最后到底有没有找到答案?
她拼命回忆着书里相关的字句情节,想强迫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排遣内心那些翻涌的黑暗痛苦的回忆。只是她的努力十分徒劳,恍惚之间,她似乎回到了清岗县城宿舍那间小小的卧室,四壁如同牢房般挤压过来,让她透不过气来。这时身边发出塞窜的响动,她侧头一看,一只松鼠在枯黄的草地上跳跃,显然丝毫也没把她放在眼里,她从失神状态中惊醒,才发现暮色已经渐渐降临,四周光线暗了下来,手里的咖啡旱变得冰凉。
她尽管心情灰暗,电知道天黑之后仍旧独自逗留在中央公园里是不明智的。她站起来找到路标,研究一番之后,走回到市区大道上。
她继续信步游荡着,不辨方向,不管路牌,却走到了越来越繁华的曼哈顿上城,这里高楼林立,华灯闪烁,沿街橱窗布置华美,街道上车水马龙,各种肤色、各种口音的行人,过起马路来一拥而上,完全不同于左恩安住了两年多的安静小城。她无法习惯这样的喧闹,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地铁入口,便走了进去,买了张票,坐上刚刚进站的一班地铁。
地铁不停进站出站,乘客上上下下,空出位置,她便坐下,不知过了多久,地铁驶到了地面,横跨一座大桥,她才有些回过神来,意识到她已经出了曼哈顿,不过她也并不在意这条线路开往哪里。反正纽约地铁是一票制,管它开去哪里,大不了再坐回来,她只是不想回酒店面对母亲。
她神不守舍地坐着,突然闻到一股怪昧,才发现她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个戴毛线帽、穿皮夹克的拉美裔男人,而这节车厢竟然只剩下了三个人,提得异样的空空荡荡,他与她显然贴近得不正常。
她起身向另一节车厢走去,站到车门边,等进站后,马上下车。
与她上车的地方相比,这个地铁站光线昏暗,显得陈旧而逼仄,月台上没什么人,地面和铁轨上扔着垃圾,看上去十分肮脏。她正准备去找线路图,突然呆住,两只肥顽的老鼠竟一前一后从她面前快速穿行而过,跑进了隧道,这情景恍如她经常做的噩梦再现眼前,她吓得连连后退,一时不知道身在哪里。
突然一只胳膊从她身后绕过来,扼住了她的脖子,她刚尖叫出来,那只胳膊狠狠收紧,一个声音在她耳边恶狠狠地说:“别叫,把钱包交出来。”
她再度闻到了恶臭,呼吸困难,胡乱摸自己的口袋,记不起来钱包放在哪里,被掐到接近窒息的那一刻,终于摸到钱包丢到地上,这时月台上有个女人大叫:“嘿,干什么?放开她!”
那人松手,将她推到一边,捡起钱包一声不响跑了出去。她蹲下喘息着,一个胖胖的黑人女士走过来扶住她:“宝贝儿,别怕,我已经报警了,你没事吧?”
她讲不出话来,只能勉强点了点头。
警察很快赶到,那位热心的黑人女士滔滔不绝地跟他们讲着事发经过,加上大量惊叹:“天哪,一切发生得实在是太快了,他们站在那边,我根本没注意到,还以为他们认识,后来才发现不对劲;我实在是气坏了,就大叫出来,那个家伙捡了钱色就跑了;居然在圣诞节这一天抢劫,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一定是个嗑药嗑疯了的浑蛋,我要是有枪,我一定……”
左恩安站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话,警察只当她吓呆了,扶她坐下,其实她除了强烈的不洁感觉,并没感觉到多少恐惧,倒是在想,在纽约只大半天时间就被抢劫,足够让她妈妈更加认定她坚持要到这个城市来读书有多可笑了。
一个女警察问左思安有没有受伤,是否需要去医院检查,她的脖子上被勒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痛,但听到医院便马上摇头:“不需要,我没事。”她随后被带到警察局做笔录,时值节日,警察局内电话铃声还是不断响起,警察不时带着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看上去十分忙碌。左思安坐在一边,近乎机械地回答者警察的提问,不过她除了告诉警察钱包里大致有些什么东西以外ia,根本没法儿讲出比那位女士更多的信息。袭击来自她的身后,前后大概不到一分钟时间而已,她根本没看清楚袭击者的长相穿着,而她站立的位置刚好是摄像头拍摄不到的死角。案底录完之后,警察问她住在哪里,说可以送她回去,她身无分文,也没有其他选择,将酒店地址告诉了警察。警察开车送她,一边友善地告诫她:“尽管这几年纽约治安有了大幅好转,但地铁抢劫案仍时有发生,以后切记,独自走在某些偏僻的区域,一定不要逗留。”
她点头答应。
到了酒店,左思安谢过警察,去前台查到Peter预订的房间,上去敲门。于佳开门,她早等得焦急,正与Peter商量该怎么办,看到女儿回来,明显检了口气:“跑到哪里去了?”
“就在附近。”
“小安,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她摇头:“你们去吃吧,我累了,妈妈,把我房间的钥匙给我。”
她的房间就在于佳隔壁,她进去,锁上门,一口气将所有衣服脱掉,冲去浴室洗头洗澡,可是在热水冲刷之下,她的身体仍旧绷紧到了僵痛的地步,无法放松下来。
你真的做好了心理准备来面对这一切吗?母亲的责问在左恩安耳边响起。她不得不承认,高翔突然出现在波特兰,带给她的狂喜淹没了她.其他一切都被她刻意忽略了。
地穿上睡衣,正在擦干头发,房门被敲响,她不想理睬,但门外的人显然也不肯放弃,停了一会儿,有耐心,有节奏地再次敲着。她无可奈何,只得出来,透过猫眼一看,于佳站在外面,她一边打开房门,一边恼怒她说:“妈妈,放过我吧,我不想吃饭……”
她顿住,门外除了她母亲,还站着高翔’于佳冷冷地对他说:“你看到了,小安没事,请你离开吧。”
“于老师,我要和小安谈谈。”
于佳显然不赞成他们谈话,可是看看女儿扶着门默然无语,并无拒绝的意思,只得摇摇头:“小安,我和Peter出去吃饭,你们谈吧。”她转向高翔,“我还是那句话,高翔,请保持理智。”
高翔进来:“你去了哪里?”
“随便转了转。”
他突然伸手抬起了她的下巴:“这是怎么了?”她试图摆脱他的手,然而他一手按住她,一手拨开她的睡衣衣领,对着灯光仔细审视,那里是一圈青紫瘀血的痕迹,“怎么会伤成这样,到底出了什么事?”
“遇上了抢劫,不过没事。”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不是14岁,也不是16岁,我今年18岁了,不能一边口口声声讲自己已经长大,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一边又碰上一点儿事就打电话求救。”
她态度平静,他有异样的心疼,轻轻触摸伤处:“我带你去看医生。”
“不用,我真的没事。”
“对不起,小安。”
“不关你的事,我不该在那一站下车逗留的。”
“小安,你在医院看到的那个孩子……”
她的脸痛苦地扭曲了一下,打断他:“我不想知道关于他的事。”
“听我说完,小安。他是我儿子。”左思安怔住,高翔握住她的手,凝视着她,肯定地说,“他小名叫宝宝,学名叫高飞,是个很聪明可爱的孩子,从一学会说话,就叫我爸爸,我很疼爱他。”
左恩安的手在他手里微微颤抖着,讲不出活来。
“他一出生就有很严重的先天心脏病,在国内已经做过两次手术,现在刚刚在长老会医院动完第三次手术,还必须接受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