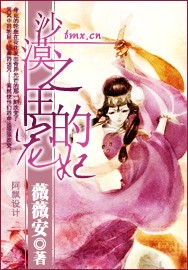荷花香残-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己不同,干净身子,一旦坏了便将成为永远的污垢,永远的耻辱。她急得想哭,但哭不出来。
胖子和瘦子已经码好了牌,搓了搓手,见她俩仍在发愣,胖子就不耐烦了,说怎么的怎么的,还愣着干嘛。瘦子态度更不好,把两撇难看的胡子摸了摸,突然吼了起来:“搓将,蠢里蠢气!”朱金银的心完全虚了,既不敢说也不敢动。盖丽莉这会也觉浑身发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场面绝对是张老板精心安排的。她的脑袋隐隐有点做痛,仿佛在膨胀,在爆裂。 胖子把两颗骰子放在盖丽莉面前,要她先摇。她迟迟不动手。他便叫朱金银摇。可怜见的,这位已吓得手脚僵硬,你抓着她的手她怕是都摇不动。胖子不耐烦老催,干脆自己摇了。他俩一起发出“七”的声音,数过去,又轮到盖丽莉。盖丽莉仍不动手,胖子便再次代劳,替她抓了两墩,然后自己抓两墩,瘦子便给朱金银代劳,最后再自己抓。他俩已经把牌打开整齐地码在面前了,她俩还是没动。胖子紧盯着盖丽莉问怎么回事。盖丽莉突然站起来要走。胖子想再次把她摁住,但这回看样子她铁了心要走,没摁住,他终于来了火,立刻站起来,挡住去路。她奋不顾身往前冲,嘴里还大声嚷嚷着,说你再无礼我就真叫警察了。胖子哂笑说,警察,你叫,你叫,他们正睡大觉呢,谁听得见。虽然知道没办法跟他比力气,可她仍竭力挣脱。瘦子在一旁幸灾乐祸:“敬酒不吃吃罚酒,人要犯贱真没治。”
胖子把盖丽莉摁到床上,用劲撕开她胸前的衫衣,崩掉了几颗扣子。她哭着叫喊了起来。他急忙用枕罩塞住她的嘴,说没见过你这么不知趣的婊子,今天非奸了你不可。他说到做到了。瘦子这时笑嘻嘻逼近朱金银,怎么样,感觉如何,你不会像她那样不知趣吧。朱金银一声不吭,浑身瘫软,对她来说,现在唯有从命而已。
不一会,房间安静下来,里面弥漫了一股难闻的味道,让人有点恶心。胖子和瘦子光溜溜地躺在床上抽烟,显得十分悠闲。盖丽莉赤裸着身子趴在床上,抽泣着。朱金银则仍显得很木讷,好像刚刚睡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场肉体大战使那笔钱撒了一床一地。
这时门又被人推开了,走进来一个警察。看清了房里的情景,警察返身关上了门。这里四个人急忙穿衣服,胖子和瘦子一边穿一叠声地喊:“侯哥侯哥!”盖丽莉和朱金银则惊恐万状,乳罩都不及戴,袖子套反了,扣子更是错了位。从胖子瘦子的态度看,这警察像是附近派出所的。他走近前把四个人轮流看了一遍,冷冷地说:“我早听说这里有人卖淫嫖娼,一直有点不信,拖到今天才想起来看看,以为会白跑一趟,哪知真是这样。好嘛,竟敢在我眼皮底下做这种买卖,胆子真够大的,一定是吃了豹子胆。走走,跟我走。”
胖子和瘦子急忙跪地求饶,齐声说:“侯哥,您老人家大慈大悲,放我们一回,以后绝不敢啦!”
盖丽莉指着他俩对警察说:“他们俩个是强奸犯,我们没有卖淫。”
警察的眼睛就瞪了起来:“什么,竟敢说没有卖?幸亏我抓了现场,要是没抓现场,还不知会怎么抵赖呢。走走,跟我到派出所去说,我看你到了哪里还怎么狡辩!”
胖子和瘦子仍跪在地上不起来,继续哀求:“侯哥,您老人家别听她的,看在我们两个老老实实的份上放我们一马,大恩大德,胜造七级浮图。”
“什么七级浮图八级浮图,起来,跟我走。”
话音刚落,胖子和瘦子突然一起向警察发动袭击,把他打翻在地,飞快地跑了出去。侯警察大叫着爬了起来,摸出大哥大跟所里打电话,说这里有人卖淫嫖娼,嫖客现在跑了,叫他们赶快出来抓人。盖丽莉仍在分辩说我们没卖淫,哪知侯警察挨了打,这会正没好气,见她死不承认,干脆几耳光抽了上去,抽得她晕头转向,眼冒金星。他怒气冲冲地问:“卖了没有?”
盖丽莉眼泪流了出来,摸着通红的脸,不敢回答。侯警察便又是几耳光,还加了三拳两脚,再问:“卖没卖?”
盖丽莉哪受得起这个,只得委屈地点点头。他接着又这样问朱金银。看见盖丽莉被打成这样,朱金银更不敢否认,只能点头。
“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侯警察说,“至少拘留半个月,罚款五千,然后谴送回乡。”
可怜两个女孩这时简直痛苦到了极点,不知该怎么办,分辩吧,势必挨揍,可如不把话说清楚,等会到了派出所,他向他的同事们说明了情况后,就更说不清了。噢,那实在太可怕了,明明是被凌辱,却成了贱货,还不如死了干净。盖丽莉和朱金银便不肯走,侯警察上前来拉人,她俩死死抱着床头。他问是不是还想挨几下,她俩便也学胖子和瘦子立刻跪下,苦苦哀求他别带她们走,她们是无辜的。他正想发作,忽然身上的大哥大响了,便先接听,似乎是他的同事打来的,说那两个家伙逃进了一条巷子,他们人手不够,请他赶忙去增援。他关了机,寻思暂时不便带她俩回派出所,便找出一根绳子把两人捆在一起,然后捡起散落一床一地的钞票,并把朱金银已经数好塞进衣袋的一叠钱也搜了出来,警告两人老老实实呆在房里,他抓了那两个嫖客再回来带她俩。
不久张老板来了,见她俩被捆在一起,故做吃惊的样子,问怎么回事。盖丽莉问他:“那两个人是你叫来的吧?”
“哪两个人?”
盖丽莉断定胖子和瘦子是他故意找来羞辱她们的,可张老板指天发誓,死不承认。盖丽莉懒得跟他哆嗦,只要他跟她们松了绑,拉着朱金银飞快逃离了这间房子。跑到大街上,经阳光一照,突然跺起脚来,说我们还是上当了。朱金银颤声颤气地问上了什么当。
“那个警察也是假的。”
朱金银想了想说:“我看他白白净净,不像坏人,应该不是假的。”
“你真笨,人坏是坏在心里,跟长相有什么关系!”
“那你说怎么办,去派出所报案?”
盖丽莉却又有点拿不准,觉得万一那警察是真的,报案等于自投罗网,决定先去找高青莲商量一下。朱金银的嘴巴就撅了起来,说她那个人不太关心朋友,找她又能商量出什么结果。盖丽莉心想这人还不笨,居然也能看破高青莲的为人,不过并不赞同她的意见,说高青莲毕竟是我们的朋友,除了她再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不找她找谁。
高青莲听了两人的讲述,大吃一惊,看似惊诧于朋友的不幸遭遇,实际是为自己庆幸,当时若跟她俩去讨钱,那她也完了。实事求是的说她当时推辞了盖丽莉的邀请不过是凭一种直觉,因为她始终不赞成用这个法子解决问题,总觉得跟那样的老板理论无异于与虎谋皮,但要说她早知道一定会有很大危险,她还不至于有如此敏锐的预见力。自然表面不敢流露得意之色,还故做愤怒地破口大骂张老板,以更加坚决的态度要她俩去告那个色狼。“绝不能再便宜他,他之所以敢同时对你们下手就是看透了你们的这种害怕心理。你们不告,他不仅逍遥法外,还不会破费一分钱。”盖丽莉说他如果反诬我们卖淫怎么办。高青莲觉得这确实值得谨慎考虑一下。她忽然想起也许自己这家店子的李老板认识张老板,便去向李老板打听张老板的底细。回来时脸色不太好,告诉盖高两人说听李老板讲,张老板以前在南门口一带是有名的霸王,经常聚众斗殴,曾被判过两年劳教,开店子后老实了点,但仍是一泡坏水,跟黑社会有牵连,一般人切莫惹他。这个情况直叫盖丽莉和朱金银毛骨悚然,尤其盖丽莉,暗暗后悔当时没听高青莲的。可是现在如听高青莲的再去告,她还是犹豫不决,因为当时只与朱金银有关,万一事情闹大,名声坏了,与已无涉,现在不同,自己也不干净,一旦事情传开,先不要说卖淫这一点是否能得到彻底的澄清,单说被强奸的名声,就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思前想后,这一步实在不敢走。高青莲这会也不像那天那样竭力鼓吹告状,因听说张老板跟黑社会有关,她有些怕,万一让张老板知道是她从中作梗,岂不是引火烧身。3 人坐在高青莲临时租的住房里沉默不语,灯也不开,都盼着黑夜早点来临,心里淌着不尽的酸水。过了很久,3人终于忍不住,抱头痛哭了一回。
四 绝望
朋友的不幸对高青莲的震动很大,她发誓绝不能步朋友后尘,平常干活很警惕老板的动静,尤其在房间里的时候,每次关了门窗总要检查5、6遍,跟老板在一起时如没别人,总是很快找借口走掉。然而她实在没想到,防范得越严,好像危险就越大,在她看来老板的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都是不轨之心的表现。还有店里其他男性成员的亲近,她无不在他们的脸上或眼中发现某种危险的信号。尽管她对自己的防范很有信心,但也知道夜长梦多,警惕性再高,难免有疏忽之时,万一哪天不注意被人钻了空子,可怎么得了。后来她想出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对盖丽莉和朱金银提议不要再住在各自的店里,出来合伙租间房子住,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哪知明摆着的好主意盖丽莉和朱金银却不积极响应,后来才知道原来两个朋友已经有了那种遭遇,已无所谓贞操,变得很随便了。有时她去盖丽莉和朱金银的店子玩,看见她俩已没有了过去的矜持稳重,越来越放纵,常常跟店中的男店员打情骂俏,有一天她甚至发现朱金银在餐厅里带着一种十分安详的表情坐在一位厨师的大腿上,笑得那个甜,她从没见过。盖丽莉和朱金银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行为上,还表现在语言上,起初高青莲说她们变坏了,她们尚能为自己辩护几句,时间一久也许觉得这没什么意思,干脆把这块语言的遮羞布彻底撕下,开始大胆的论证自己这种变化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并一起断定高青莲迟早也会有变化的。朱金银说:“我早想通了,一本正经的实在没什么意思,我们过去在小地方没见过世面,太不开化。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应该及时行乐,尽情享受,不趁年轻多玩玩,等老了再去玩呀!只要能挣钱,只要过得痛快,管他高尚还是堕落。”
盖丽莉也有相同的看法:“你现在看我们不惯,但我敢肯定你以后会跟我们一样。小地方来的女孩子,想完全摆脱城市生活的影响,根本不可能。你看看四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你能无动于衷?影星歌星,也许你有那命,但我认清了自己,绝对没有,不再做那个梦。现在我只想多挣点钱,挣了钱就花,买衣服买首饰,上高级酒店,吃山珍海味。即使我挣到了5000块钱,能够回去向父母交代了,我也不会回去。留下,一定要留下,永远留在城市,永远做一个城里人。”
高青莲虽然反对她俩的这种新人生观,但正如她俩预言的一样,很快她的反对态度就有所动摇。确实,想在快速变化、色彩斑斓的都市生活中完全保持本色,实在难乎其难。高青莲承认两个朋友以更现实的态度接近都市生活是对的,至少不能说错,或者说至少她没资格谴责她们,因为是她把她们带出三峡深处那座封闭保守的小县城的,结果却是受骗上当,而遭受这种打击后她又不能给予她们任何形式的补偿,她们不以这种方式在都市里挣扎又能怎么样?她渐渐理解甚至是原谅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