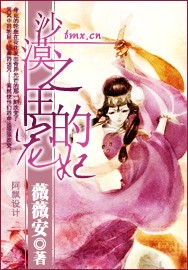荷花香残-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伴一生,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他所难以离弃的。他们的结婚计划早定好了,再过两三月,就举行仪式。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有个家,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简直没法说这感觉究竟是轻松还是沉重,只是常想,结婚是一个人生任务,总要完成它,不完成不行。
父亲在另一间屋里咳嗽,一串串的咳,仿佛恨不得把心肺咳出来,让他很心烦,也让他有点心酸。母亲走后父亲的身体就日渐衰老,看来也来日无多了。应该尽快生个儿子,让他在走之前看一眼,这样走得安心。父亲快把屋顶的瓦片咳下来了,他进去给父亲倒了杯水,然后回到客厅继续看电视。电视上是什么节目他却没看明白。他感觉今晚有点心神不宁,好像遇到的每一件事都跟他不谐调。严格说不仅是晚上,而是整个一天都这状态,仿佛哪个地方有问题。但不管他如何搜索,怎么也找不到问题所在。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电话,与平常每天好几个电话相比,这个情况似乎有点反常,他便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就是这个电话。
话筒里传来一个熟悉的清脆的女音。他一下就听出她来了。他喂了一声。那头便叽哩呱啦就是一大串。他握着话筒,久久一言不发。对方要他说话,他说没什么可说的。那头便哀求起来,又是叽哩呱啦一大串。接着是沉默,她等待他的回答。他足足5分钟没出声,连呼吸都很微弱,似乎觉得呼吸重了会影响自己做决定。那头好像很理解他的犹豫,温柔地说我们谈谈可以吗。他终于嗯了一声。可马上暗自责怪,我怎么就答应了,我怎么能够答应?那头很怕他变卦,又哀求起来。他有点烦,便说行,你等着我。他挂了电话,拿出烟来抽,坐着发了一会呆。他想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可实际上根本不行,他现在没思想,只有感觉。当一个人完全被感觉左右的时候是难免犯错误的。这个高尚而又可怜的青年,到底没能抵挡住内心深处的某种诱惑。
他走进里屋。妻子躺在床上,感冒使她像一只受了伤的鸟。听见动静,她睁开眼看未婚夫,无神的目光似乎在期待他的温言软语。然而她大失所望。
“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她很不高兴,想说我病成这样,你还有心出去。到底是一个很宽容的女子,她把话咽进肚子,又闭上了眼睛,只想弄清楚他出去干什么。他说有个朋友碰到了一点麻烦,想请我帮点忙,不去不好。马上就会回来吧。是的,马上。她就同意了。然而她的通情达理却叫他忽又迟疑起来,似乎对她突然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感觉,甚至是愧疚,便站在床前凝视她,竟希望她别这样通情达理。她当然万万想不到他有这种心理,以为他是怕自己有意见,倒催他走,快去快回。他恋恋地说你没事吧。她心里暖融融的,说我好多了,你去。
他出了门,却没有走,而是站在屋檐下想心事。这会跟刚才不同,有了一些思想,或者说是未婚妻的善解人意唤醒了他某种道德意识。那个女人是只什么鸟他是非常清楚的,论人品,她跟未婚妻根本没法比,唯一令人感佩的是她的羽毛太美丽眩目了,叫人虽恨其风骚,却是爱恨交加。苦甜参半的滋味最不是味,可往往又叫人最想品尝。他回头往屋里看了一眼,想从妻子的气息中吸纳一点正义的力量,拴住自己的脚步。可妻子的气息似乎太弱了,而此刻另一种轻浮的声音从心底慢慢响了起来。刚才打电话的时间太长了,那个女人一串串的声音仿佛在他头脑里生了根,这时又在他耳朵里回荡。虽然那会儿她回忆他们那些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些滑稽可笑,但不可否认都是事实呀,而那些事实实际上也是他经常追忆过去的根源,因此,要他因为她的可笑而不理会那些事实似乎说不去,他觉得自己不能因为怨恨她也一并怨恨历史,她再对不起自己,历史可没有对不起自己。再一个,她现在是名人,身份高贵,对她的回忆和要求,以自己这么低的社会地位,似乎也没资格不给她面子,更何况现在他耳朵里又响起了她摇晃金钱的声音。他觉得用初恋情人的钱来娶现在的未婚妻是一件很趣的事,既能解决经济问题,对她也是一种最合适的报复。他心里感叹,她确实是成熟了,不仅懂得利用昔日的感情,还懂得用最实惠的诱惑。真够毒的,知道我意志薄弱,就无所不用其极,看来我这一辈子被她算透了,她居然敢来求我,这也就意味着她知道我有可能帮她,我简直成了她前进路上可利用的工具。他心里是不愿的,然而真是这样吗,还真难说得很,毕竟那是他的初恋啊,而初恋往往对人的灵魂有着永难消失的魅力。他终于开始移动了,向街中心,向江边那座酒楼移动。嘴角便露出了一丝玩世不恭的笑,去看她吧,看看经过几年上流社会的打磨改造,她的美貌是不是更加迷人。
这是本地一家最豪华的酒楼,就在码头一侧,专为进出县城的商贾游客开办的。她怕人认出,坐在光线较暗的角落里,背对楼门,戴了副太阳镜,靠在长靠背椅上闭目养神。昨天累了一天,今天也丝毫不轻松,短短两天精神折磨,她好像瘦了一圈。既怕龙海洋答应,也怕他不答应,究竟希望什么结果,自己也说不清,只有一点很明确,事情既然已经干起来了,那就尽一切所能干到底,至于成不成,听天由命。打了个盹,被几下轻轻的响声惊醒。朦胧中看见对面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似乎很迟疑,显然在没有得到她准许的情况下他不知该不该坐下。她揉了揉眼才看清楚。龙海洋3年不见长胖了,脸上多了一分苍老,似乎很稳重,可他眼里游疑的光显示他还没有真正成熟。她把太阳镜摘下,跟他对笑一下,请他坐,又戴。他忽然觉得她有点愚蠢,以她的名气,回来应算荣归故里,县里的人常说只要她回来一定给予隆重热烈的欢迎,感谢她为本县人露了脸,可此时的她却像个夜总会里的三陪女郎,不时左右张望,生怕人家认出来。他心想你这是何苦呢,放着歌星不做,却来玩这种游戏,也不怕毁于一旦,胆子是真正的练大了,生活真能改变人,才几年工夫,过去的纯情美人就变成了魔女。她要他点菜。他双臂交叉放在,身子前倾,看一会楼前进进出出的客人,看一会她,始终不点菜。她只好自己给他点,要了一瓶竹叶青和一碟牛肉干。她知道牛肉干是他最喜欢吃的,至于竹叶青对不对他胃口,就不知道了,要他尝尝。他始终不吃不喝。她问他是不是还在生她的气。他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她就道起了歉来,把那年不能让他和他母亲住徐景升老屋的原因再细说了一遍。他直冲她摆手,说他早忘了,要她别放在心上,如果他计较不会赴这个约会。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喝酒吃菜呢,我只能认为这表明你还在怪怨我。他说刚刚吃过饭,一点不饿。那可以喝点酒吗。他笑了笑,拿起酒瓶直接灌,看样子酒量不小。
“你妈怎么样啦,病好了吗?”
“她不在了。”他沉痛地说。
她有点错愕,愣了老半天,问什么时候去的。前年。这个意外情况叫她现在一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她对他母亲没有感情,可这会却好像很悲痛似的。对于早已把所有友情、爱情、乡情从内心深处删除了的她来说,这种情绪真是难得的真实,心里泛起的阵阵酸水也不掺一点水分,不是竭力克制,可能酸水已涌出眼眶。但如果以为她是在为他母亲悲痛那可就错了。她是为自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面对一个有丧母之痛的男子,他母亲的去世或许还跟自己有点关系,她就感到实在不便再说服他为自己办事,否则简直没人性。这一会她觉得这一趟可能真是白跑了,对北京的事情开始有点绝望。她轻微颤抖着点燃了一支中华烟。他以为她是良心受了一点谴责,心里舒服起来,觉得她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尽管只有那么可怜的一丁点,但这对现在的自己来说够多了。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显得很诚恳地说她对不起他母亲。他再次冲她摆手,绝症,没办法。“让她安息吧,别再打扰她。”
她感到他在安慰自己,刚才那种沉重的心情稍稍得到了缓解,又恢复了一点信心,觉得或许事情还有办法,正如他刚才所言,如果对她有意见那就不会接受她的邀请,能来说明他不是完全拒绝帮忙。可还是不知该说什么,他不需要安慰,马上就谈正事显得急了点,她只是抽烟。假如她了解他现在的心情,她一定会骂自己愚蠢。她忐忑不安,他却在欣赏她的美。她以为几年来只有自己变了,以为他还是那样纯洁,其实他也有变化,只是没她大而已。他自以为使自己前来的原因是昔日的感情,实际更重要的是想亲眼看看她的美被上流社会蹂躏成了什么样子,自己曾那样深爱着她,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在如今她已成残花败柳,并有求于自己的时候,他盘算着是不是能捞点回来。他不禁暗暗惊叹,被上流社会的欲望之火焚烧了这几年,她的美竟完好如初,就像当年在峡谷山峰上所看到的日出,柔而娇嫩,灿如霞光。他发现撇开道德赏美色,纯情之美跟妖艳之美实在没法比,从性爱角度说,纯情之美中的羞涩、含蓄、自重等特质简直可以说一文不值。在欲望中,性爱的至上境界是放纵,唯有放纵,才能体验肉体的最大快感。而放纵的外部特征,或者说先决条件就是妖艳。这是上流社会的杰作,是一副有血有肉的活动的艺术品,他知道一般情况下自己是没资格如此近距离欣赏的,然而造化弄人,哪曾想命运会这样跟他开玩笑,用一种极特殊的方式把她摆放在自己面前,让他可以长时间的尽兴观赏。他相信这是上天的恩赐,应该倍加珍惜。
“你想好了吗,非要这样干嘛?”
“是的,非这样干不可。”
“万一砸了,反而毁了自己,知道吗?”
“如果成了呢!人生一世,有时需要冒点险。”
“一无所有的人冒冒险是可以的,可你现在名利双收还冒险,是不是不值得?”
“每人的追求不一样,我现在的名利对别人来说也许可以满足,但离我的理想还差得远。一个湖南歌手,走到外省去没几个人认识你。不能扬名全国,这碗饭就算白吃了。”
“那也可以慢慢来吗,为什么非要用这种过激手段呢?”
“张乙某是国际知名导演,在他的电影里演个主角,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这次机会这么好,我必须抓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他摸出一包襄樊烟。刚抽出一支,她就把大中华递给了他,抽这个。他深吸一口,使劲往肚里吞,憋了很久,半天才见一丝烟雾从鼻孔钻了出来。在这长时间的沉默中她一直紧紧盯着他。突然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他回答两三个月后。她说到时我可能来不了,就先给你两万块做贺礼。说罢她从皮包里摸出一叠报纸包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扔还给她,礼太重,我受不起。
“你给我把事办了,不就受之无愧啦!”
他瞪眼看着她,神情异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有点凶恶。“我再说一遍,你要想想清楚,如果事情坏了,我没什么,大不了进去几年,出来后我可以做生意干别的事,你可就真正毁了。”
“我豁出去了,就赌这一把。”
他觉得她确实下了狠心,但又觉得她显然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