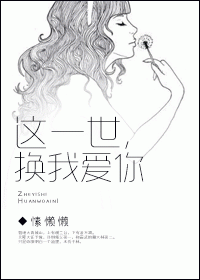这一世木已成舟-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琥珀道:“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不见得,你身上有种奇怪的亲切感,让我愿意亲近。还记得我们共同喜欢的那本童话书吗?知道它的人都不太多,碰巧又是自己心头最好,更是难得。琥珀,替我好好干,好吗?”
琥珀点了点头。
话虽如此,两人一起洗碗时,琥珀仍觉得有些不可置信,恍惚得感觉是在梦中,这么大一件事儿,怎么就这么快地敲定了呢。
她问:“你决定了吗。”
“当然。”
“你能告诉我,被追杀,到底所为何事吗?肯定不止你对我讲的那么轻描淡写。”
漓江把碗洗好,放到碗橱里,叹了口气:“我会慢慢告诉你的。”转了个身,望着琥珀。他系着围裙,十足的居家男人的风貌。
琥珀也望着他,突然很想走过去,轻轻地,轻轻地环住他的腰。
可她只是站在原地,没有动,慢慢说道:“我担心——你。”
漓江没有做声,琥珀接着说:“你看,你连买房、开公司这么大的事都不亲自露面,我很担心,你所面临的追杀非常严重。”
漓江仍望着她,眼睛很亮。
狭小的厨房内,两个人对望着,直到电热壶的水烧开发出鸣叫声,才错开目光。琥珀有些讪讪地走过去拔下电源插头。
漓江说:“我来吧。”又说,“你今天走了那么多路,脚一定不舒服,我倒水给你泡脚。”
琥珀乖乖地走了出去。漓江先倒了点温水在盆中,再加入热水,手探进去试了试,眉眼都笑开了说:“正合适,洗吧。”
琥珀又呆了,旧梦仿佛重温。仿佛眼前人是陈燃。她大学刚毕业,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刚开始的时候,业务开展得非常困难,硬是拿着地图,走路、乘公交车跑遍了整个上海,最厉害的记录是两个月之内穿坏了8双高跟鞋。做得那么累,那么苦,所幸有陈燃。
琥珀白天在外面奔波,晚上回来时,阿燃总是放好一盆热水,让她先烫烫脚,再怎么苦,再怎么委屈,好象都被热水消融了。
阿燃是温和体贴的男人,在细节上总能令人感动,分手后,琥珀仍然念念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已经习惯了他的温暖了吧。曾经有一个人,让她知道,降生在这个世上,原来是那么美好。
此刻是另外的男人,同样这样细心温存,同样有着暖人的笑容。
琥珀什么都没说,沉默着泡脚。漓江走回了客厅,坐到沙发上打开收音机,他把声音开得很大,她得以听到音乐声。她心里一动,喊道:“漓江,帮我调个台!”
辛夷的节目正播到中间时段,她的声音依然如昨,低沉的,有点沙哑。她正在讲故事:一场婚礼中,新郎的爸爸当场吐血。新娘扶着未来公公的头,哭着喊爸爸爸爸。新郎当天带了自己爱的另一个女人,远走他乡。他们都说罪孽啊罪孽啊。那场婚礼上,席间的蛋糕有很多层,最上面放着一对新人,写着百年好合。有人说,那个拐走新郎的女人,她真勇敢。他们一定很幸福。
辛夷说:“真像是个美得要命的爱情故事。爱,永远有理由背叛整个世界。”这句话她讲得平淡至极。
中间播放了片刻的音乐,只是一些排箫的声音,悠长,苍凉,像呜咽。乐声中辛夷的声音仍然低低地,平淡地讲下去:“多年后,逃跑的新郎独自从异乡回来,神态憔悴。”
往事八
漓江在A城大红,常常有客人慕名而来,指名要点他的歌。同事们开玩笑叫他魔之红牌起来了。起先他不习惯,脸上臊得难受,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适应了。也有相熟的同事羡慕漓江:“真是个聪明的人呢,这么通透。”
漓江就笑。其实他没有刻意钻营过,只不过向来知道什么是生意,无非是拿自己所有的,换自己所无的,拿对方想要的,换自己想要的,深谙此理,又能运用好自己的优势,自然玩得转。
他赚的钱,很快成了一缕轻烟。或者是一小粒药——这时候丁振中的病情已经十分沉重。漓江因他熟悉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SCS,血流不平均性。
这些术语取代了丁振中的姿容,他的姿态,他的语调,他的手势。
丁时常心绞痛。每日都要吃5片硝酸甘油以及其它一些昂贵的药物。加上许颜必需的白粉,漓江一日日往返于医院和酒吧之间,疲于奔命。
丁是个清廉的官员,手头上并无多少积蓄,得了绝症,家人知道无望,也不大管他,他们从前对漓江冷眼旁观,现在也不了,由了他们去。
丁已经从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在位和不在位之间,待遇差别还是蛮大的。单位还算仁义,给丁报销过一部分,到底杯水车薪。
漓江不忍在这个时候弃他而去,只得继续咬牙坚持。
他陪丁做过脊髓电刺激治疗。电极植入脊柱椎管内,丁痛得惨叫起来,一把抓紧漓江的手,声音回荡在漓江灵魂深处,放开时,漓江的手心手背一片青紫。
每当这时,漓江总会想起妈妈。那一年,家里没有钱,妈妈没拖多久,就去了。
丁的药物十分昂贵,漓江的钱不够,只能在许颜的毒品上克扣。他曾经小心翼翼地和她打商量:“小孩,你能不能忍一下?丁伯伯病体很沉重。”
许颜点点头。漓江抚着她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房子外红墙上的爬山虎枝枝蔓蔓的,把人心都钻遍了,绿得沁人。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伤,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漓江抬着丁到楼下做CT,央求着人帮忙。无比慌乱狼狈地帮丁换衣服,套上塑料薄膜的防毒拖鞋,没有人给他温暖的笑脸,也没有人给他善意的祝福。医院里时刻都有死亡发生,同情已是不必要的奢侈。
片子出来了,影像像是切开的核桃薄片。又去化验室,把血抽出来,装在一个薄膜袋子里封存,放到某种光波下照射。再拿回来,输入丁的体内。他的皮肤上洞眼多得数不过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了,他给丁擦洗身子,帮他接屎接尿,帮他翻身。可他还是没能好起来。
得知许颜去找了秦力的当天,那日有雨。漓江去医院探望丁振中,医生拉过他,忧心忡忡地说:“丁局长的病,需要用大量的药,要输液,做化疗,这些都需要钱。”他听了很难过,无心上班,找老板请了假,提前下了班,下午五点就回家了。
这个时候,就算是借,他也借不到钱了,他向熟识不熟识的每个人开口,渐渐沦落到连十块五块都要借的地步。有人碍于面子,借给了他,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别人都不知道,这个清高冷漠的年轻人怎么变成了这样。
没有钱,药就停了。付款处的窗口象只巨大的黑洞,每一次他把钞票像流水一样递进去,然后端着盆子扛着箱子把那些大瓶小瓶搬回来,塞到丁的床底下去,等着护士一件一件把它注射到丁的身体里。可现在,他已山穷水尽。
他走在路上,无意看到许颜和秦力相对坐在路边一间咖啡店的靠窗座位上。远远地看不清楚两个人的表情,可单凭动作就能看出是许颜在央求秦力。
漓江的心缩成一团。他看到许颜在哭泣,秦力把她拉到怀里哄着,不住地拍着她的背安抚她。又看到他塞了一大包东西给她。他当然清楚,那是毒品,虽然秦力是用了一个黑色的袋子装着它们。
他们在咖啡厅外的香樟树下道别,秦力拉过许颜,在她面颊上亲了亲,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开了,哼着小曲。他还是那副模样,没怎么变过,白T恤牛仔裤,把手插在裤兜里,嘴唇隐约有毛绒绒的胡子。
许颜独自走回家。漓江在她身后不远处看着,心如刀割。他能说什么呢,他甚至不能责怪她。抬头看到灰蒙蒙的天空,他突然觉得心都灰了下来。他不知如何让自己不那么难过。他只是知道,万万不能在大街上哭开了去。
古人可泣。他不能。陈子昂可登幽州台或歌或泣,可他苏漓江,不可立于市井之中当街痛哭。
他是个晴朗的男人,想要过上晴朗无比的生活。为什么,他会这么失望呢。这和他想要的那种生活多么远,多么地远。他不知道怎么命运对于他来说,是如此错综复杂的一出折子戏,在每个自以为会顺当的时候突生波澜,颠覆平静。一切又开始混乱起来。他无法以自身的力量去抵抗时间和世事。
漓江转身,去了上夜校的那间大学。正是黄昏时分,残阳铺天盖地,天空血红淡黄,远远地有一圈黑色的光,很诡异。他沿着操场走着,看到主席台处红旗猎猎飘扬,突然记起自己小时候很羡慕班级里的优秀生在周一早晨可以升旗。在幼时的他看来,这是最光荣的事情,比什么都值得自豪。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很多大学生蜂拥着去食堂,有人拎着不锈钢食盒,敲得叮当响,大声说着话,呼朋引伴,生命一派热闹繁华。
漓江看着他们从自己面前经过,他站在万人鼎沸的操场茫然四顾,心内很荒凉很冷。为什么阳光如斯暴烈,眼前却一片漆黑。
漓江看到有个年轻孩子,穿T恤仔裤,沉默地在篮球场上打球,许久投不进一个。球一下一下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笃笃的,孤单的。他看着那个孩子,嘴角露出微笑。若干年前,在某间中学校园的冬日早晨,他也曾经这样打过球,然后认识了这一生的爱人,从此不离不弃。
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漓江叹了口气,离开学校,向右转,前面不远处有一片排挡,经营各种廉价而美味的食物。他在其中坐下,胡乱叫了点吃食,又要了两瓶酒,喝了下去。那酒非常烈而且甘醇,喝下去血管里会突突地跳着,有着刺刀见红般的畅快淋漓。
不醉,酒就没有意义。如果就这么醉过去,醉过去,就好了。可是没有,他仍然清醒着。
他坐在那里发呆,直到排挡快要收摊的时候。
他用身上最后五块钱付了帐,故意砸破酒瓶,狠狠地砸到清冷的地面,瓶子发出清脆的破裂声。有人在旁边窃窃私语,说:“这人怕是醉了。”
漓江笑笑。他当然没有醉。不过是借酒装疯而已。他摔碎了两个瓶子,嫌不过瘾,又抓了几个来砸,哈哈大笑。
当他回到家中,许颜已经睡着了,她应该是刚洗过澡的,发丝湿漉漉的,散发出清香的气味。她穿着白色的睡裙,有种甜美而天真的诱惑,像小妖精洛丽塔。她的手边放着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漓江拿起来翻了翻,知道许颜看的是那篇《金锁记》。
许颜在这篇故事中间夹了一张折了四折的彩色信笺,她喜欢在漂亮的纸上写字,明星印在背面,那么好看。漓江展开看,是她摘抄文中的几段话,用天蓝色的圆珠笔写下,有一股清淡的香味,很好闻,也有点忧郁的感觉。她的字并不算好,字体舞舞抓抓,漓江看在眼里,只觉满眼温暖。
这个故事漓江看过,他还记得主人公叫作七巧,那个人物太鲜明了,她付出青春,到年老时获得金子,不惜人性扭曲。漓江想,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和自己相似,只是他没有那样直接明了,但他还是在花费多少好时光,为了更多的钱。
钱就是自由。这是金手指写在墙上的神喻。饥肠漉漉的人握着一块钱走进超市,除了果腹,没有挑选口味的余地。在漓江此刻,没有什么是比金钱更美好的东西了。他已经无路可退,只能不择手段,并且不给自己失手的机会。
漓江关了灯,坐在黑暗里抽烟。他想,也许必须做出决定了。
许久后,许颜醒了,随手拧开床边的灯,看到漓江坐在她身边,笑了:“漓江,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很有钱很有钱了,一起去北京旅游呢!”她笑得前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