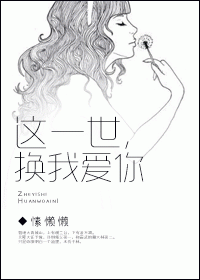这一世木已成舟-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院的手续也不复杂,很快,所长和管教就送他们出了戒毒所的大门,并且特意叮嘱了许颜几句。
走出大门时,漓江看到丁振中的车子泊在门口。
丁看到他们,缓缓摇下车窗,招呼他们上来,说:“王所长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没有用司机,自己开车。漓江听他说过,丁早年当过兵,在部队时就在汽车连里,当了局长,也习惯了自己驾车。
一路上许颜的心情格外晴朗,她大声和漓江谈笑,兴奋的表情溢于言表。
下车时,丁振中从后座拎出一个纸袋交给漓江。
纸袋有些沉,漓江提着,好奇地看了看。丁说:“来接你们之前搞了些戒毒资料,比如戒毒知识和国际戒毒治疗指南,你们要好好看看。”
许颜微笑着挽住漓江,客气地说谢谢。
丁拍拍她:“丫头瘦了好多。里面很苦吧?”
许颜大力点头。
丁嘱咐了半天,这才略微放心地走了。
许颜目送着车子扬尘开远,问漓江:“你和他很熟?”
漓江若有所思:“我和他一定有渊源。他会告诉我的。”沉吟了一会儿,含着眼泪道,“这一生,我只为两个人活着了。你和他。”
第13章
琥珀将位于浦东这处即将到期的房子退掉,和漓江另外找了一处。新住处坐落在豫园一带,从复兴东路转进去就可以看到,路面洁净宽敞,两旁的梧桐油绿着叶子。弄堂很浅,一眼可以望到底,还种了些花花草草。空中尽是纵横交叉的电线和晒衣竿。那些竹制的晒衣竿从这家人的窗口伸出,搭在对面邻居的屋檐下。墙脚上依附着一片片潮湿的地衣和稀疏的小草。
新家在三楼,朝南的房间,有两扇很大的窗户,是两居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加上地段不错,价格因此有些昂贵,两人各住一间。
琥珀常常坐在地板上晒太阳,对门院子里的白玉兰盛开得很茂盛,偶尔有几片叶子落到家里的阳台上。从阳台上看过去,一只金褐色的小猫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两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口一放一收的绕着毛线。有的人家就着微微的灯光洗菜,有时只看得到一双劳作的手,楼下的女孩弹得一手好钢琴,黄昏时她指间的旋律和白玉兰一同盛放,真美好。
今年的秋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才八月底,风就很沁凉了,早晨起来,空气里有芬芳的润湿气息。琥珀和一家公司约好,下午三点过去面试。她出门时,跑到漓江房间里和他说了一声,他正坐在床上看电影。
等公交车时,琥珀在24小时的便利小超市买了个蛋黄肉粽当中饭吃,热气腾腾的。学生时代,她常常和室友去校外的小面馆吃饭,3块钱的牛肉拉面,撒上葱花香菜,辣椒放得铺天盖地,哗啦啦地吃。或者是炒年糕,香香的,糯糯的。
公交车上竟然放着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是电视台为他做的一档子怀念节目,无数个飞速掠过的画面上,哥哥的容颜美艳如昔。琥珀捧着下地铁时买的刨冰,边喝边看,轻轻地和,一车人都沉默着。
刚上大学那年,熄灯以后琥珀经常翻来覆去地听这首歌,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当年真是年轻,十几岁,夜里睡不着,披衣起床,不惊动任何人地走出寝室,坐到阳台上,脚晃荡在空中,听随身听的这首歌,抽烟。当时琥珀并没有经历爱情,一样为这首歌断肠。
也许是因为这个男人,张国荣。总是这么爱他。只要是他的歌,就是好的。再如那首《风再起时》。其时琥珀在校广播台担任播音,有时做一档子节目,会配上这首歌。只因为哥哥曾在告别演唱会上唱过它。
画面一转,是一组电影镜头,张国荣对梁朝伟说,让我们重新开始。然后他们在厨房里跳舞,暗蓝色的探戈响起,伊瓜苏的大瀑布倾泻而下。
记得哥哥曾说过:“如果终身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保持这个生活水准,我算过了,要6500万港币。
可是身价过亿的他,照样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谢世。
也许生命真的不是每个人的责任。
有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就象张爱玲说的那样,会把自己吓一跳,竟然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大学毕业四年了,也就是说那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距离第一次在节目中用到这首歌的时候。这八年来,经历了太多,毕业,工作,恋爱,失恋,辞职。故人旧事,都已不知下落,也无意再问。
人生的大决断,只用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全部走了一个过场,现在无非只是重温,缺乏新鲜感,不过是让日子平缓地过,只要不再有新的遭遇,那就是好。
琥珀所要的,只是一份安稳罢了。这次她面试的韩国大宇公司的策划,薪酬福利都不错,她已经过了笔试、第一次面试两关,现在是最后一关,第二次面试,直接面对人事经理。
大宇面试的气氛很随和,应聘者和主考官仿佛是闲坐聊天,问题倒是刁钻的,颇有些绵里藏针的感觉,涉及到各种电脑游戏中的细微末节的东西,这主要是考察应聘者对游戏的熟悉程度。这么一路问下来,随着问题的深入,琥珀渐渐感到有些吃力了。
人事经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天龙八部》里马夫人的闺名是什么?”
“康敏。”琥珀从容作答。
面试官微笑着纠正她:“不完全正确,应该是温康敏。”
琥珀笑了笑。然后他们握手,道别,人事经理让她静候消息。琥珀心下明白,是没戏了。虽然从680余人中脱颖而出殊为难得,但面对只招聘一名员工的严峻局面,还是将功败垂成。只是她仍不知道“温康敏”的出处在哪儿,决定回家翻书查证一番。
面试回来已经晚上七点了,琥珀提前一站下了车,那里有一间大的超市,可以买到漓江喜欢的青岛啤酒和白沙——他只喜欢这两个牌子的烟酒,还有琥珀自己喜欢的光明芦荟酸奶,捧在手里沁心的凉。
家里一片漆黑,黑暗中传来细细的歌声。琥珀知道漓江在,这是他的习惯,喜欢不开灯听音乐。见她回来,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漓江拧开电灯,朝她笑了笑,站起身来,接过她手里沉甸甸的袋子,走进厨房,一样一样放到冰箱里。
转身的时候漓江问:“你吃饭了吗?我下午四点才吃的中饭,不饿。”
琥珀摇头,漓江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她,走进厨房,煮了一碗面条给她。琥珀吃着面条,微侧过脸,正迎上漓江专注的目光,她眨眨眼,问:“是否我有一点像她?”
漓江道:“不。你们丝毫不同。”
“她是你的幻觉,永远陪着你。”
漓江道:“人的心上如果扎了一根刺,会很疼,可如果把这根刺拔出来,会流血而死,你不明白吗。”
琥珀说,“也不一定会死,刺拔出来后,不过是一个疤。”
漓江说:“可那里是心。你愿意冒险吗。”
“有那么几个瞬间,生命对我来说,不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试过,没死成。”琥珀望着漓江笑,“并没有太多人知道,感冒药用酒送服,有死亡的可能性。”
漓江抽着烟说:“生和死,我们作不了主。自从那年我离开A城,生命对我来说,从此不重要。还活着,只是不方便主动去死。如此而已。”
隔一小会儿,他又说:“从来都是我讲故事给你听。是否能够告诉我,关于你的往事?如果你愿意的话。”
于是琥珀就讲了。
琥珀的初恋在18岁,那时她是快乐的大二女生,经常呼朋引伴出校门逛街买书,偶尔也买衣服,去附近的小饭馆吃拉面、炒年糕、蟹黄小笼。奖学金下来了,也会打点牙祭。这么些年了,她还记得校外某间小餐厅的厨子做得一手味道特别棒的川菜,水煮肉片、夫妻肺片、红油兔丁什么的,叫人念念难忘。她在那年和周智杰谈恋爱。周和她同届,法律专业,西安人,一口普通话说得动人心怀,是校广播台的台长。
刚进大学,就有人指给琥珀看,那就是周,很优秀,高大的球队中锋,10号杀手,高中时获过全国物理联赛大奖,大一刚入校那阵子,该小生风头无两。
大二时,琥珀考入广播台当主持人,负责“运动旋律”这个栏目,这是个体育版块。有时需要她自己动手写稿。其中有个栏目叫作“春风化雨”,琥珀给它配的题头曲是蔡琴的“是谁,在敲打我窗”,只这一句,反复地穿插在每个版头前面。
她第一次录播节目,周给她调音,看到节目单上所要求的是这句歌词,怔了怔。事后他对她说,这歌,我喜欢。她抬眼望着他,笑。他忍不住弯下腰来,捉住她的手。琥珀有一双很美丽的手,手指修长,手背上有涡,柔美白净。就这么开始了交往。象牙塔里的爱情,简单自然,聊音乐,或者梦想,再或者人生。青春无限快意。
那所校园里到处都是梧桐。它们长得太过浓密,遮住了整个天空。下雨时人走在下面,几乎感觉不到雨丝。周常常站在她宿舍楼外第6棵树下等琥珀。有时她靠在树旁,和他说着话,他的手就圈过来了,连树一起抱住,吻她。
夜里,两个人牵着手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散步,也会并肩在操场上一圈圈地走,抬头看星星,夜色温柔,空气里沁透了潮湿的花香,令人恍惚。常常说着笑着,他突然沉默下来,停住了,歪着头看着她,大力揽她入怀,紧紧拥抱,荡气回肠。
真年轻,那时。
也曾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商场胡乱逛,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座位,他坐上去,抱她在腿上,双手交握,旁若无人,看窗外华灯初上。青春在那时是件自有尊严的事情,爱情也是,不怕受非议,遭耻笑。
他们在一起无非是牵手拥抱接吻。周智杰提过进一步的要求,琥珀没有应,不是没有缠绵到很难自控的时候,到底还是坚守下来了,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害怕。总之有点惘然。
很久后琥珀会想,当年也许周智杰不见得有多么爱她,可身边一时也没有新的什么人愿意加入,只好将就。她甚至不确定周是否爱过。他是个粗线条的男生。这么一想,又会不甘心,总该有些什么痕迹,是存在过的吧?相处了那么久,未必就没有一丝真心。
她寒假归校,提前打电话通知他了。那时学校各寝室还没有电话,电话亭的老婆婆举着大喇叭在宿舍区里喊,某某某,有电话!找不到人,就写在小黑板上。黑板挂在通向食堂的必经之处,来来往往都看得见。
他必是在乎她的,早早地就在火车站里等。老远望见她下车,急急冲过去,替她拎起行李,开始拼命说话。说寒假看过的电影,说和中学同学的聚会,说小表弟有多么可爱,整个寒假的话都攒到现在,他慌慌张张,急于表达,以至于语无伦次,她也不计较,默默地微笑着跟着他后面走,不时附和几句。
寒假里自然是通过电话的。放假之前就约好了,每周六晚七点,他给她电话。在家里说话放不开,他买了电话卡,跑去巷子口的那间绿色的电话亭。她家的电话放在客厅,她坐在那儿,心不在焉地看电视,等他电话。铃声一响,就飞快地起身去接。
有时碰巧是父母的熟人打过来,她就怏怏地给了他们,心里焦急地想,他打不通,该着急了。那里下雪了吧,还是在下雨?他站在户外,会不会很冷?一旦接通,她就在父母的眼皮底下说话。自然是不方便的。如同暗语,我很好。你呢,还好吧?客气得几乎生疏的几句对白,每次都在重复,却乐此不疲。
他在那边说,那我挂了啊。那我挂了啊。
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