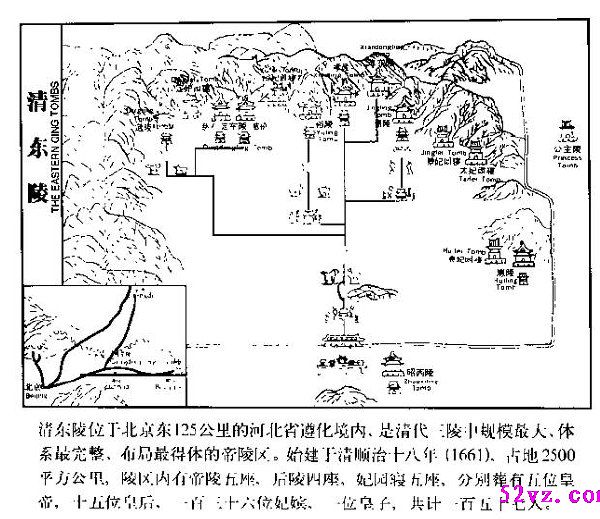日暮途远-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苏粼正往后院走,听得这话,不由得停了脚步,回头看时,但见江缓抚着阿黄的毛皮,笑容苦涩。一人一狗倚在门边,蓦然孤寂。
苏粼拎着肉出来的时候,江缓却不在。阿黄扑上去又是一阵乱舔,苏粼被折腾得一身唾沫,几乎气死。
他一边将肉扔了丈许远,一边忿忿地想:宁先生怎么会让这样贪食又粘人的狗守门,分明要请人吃狗肉!
正自想着,江缓从屋里走出,手里握着原先的那只竹筒,只是封蜡换了新,却不用尚书令的印鉴,同样也是一个字——“江”。
“叔父回了什么?”苏粼笑嘻嘻地问道。
“小孩子别问。”江缓给阿黄系好了竹筒的丝绦,抬眼见苏粼颇不服气的样子,又笑着添了一句,“尤其是尚未加冠取字的小孩子。”
宁谦正埋头趴在又硬又冷的长案上睡着,案上堆了一捆又一捆的谱录。
他只是这些天太累了而已,朦胧中听到一阵犬吠之声,慌忙抬了头,但见自家的黄狗蹲在屋外,冲他吐着舌头。
宁谦笑着走过去,摘了丝绦,正想把竹筒搁一边去,却发现上面又封好了蜡。宁谦疑惑着剥蜡,果然抽出一方白绢来——
“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
是不是誊录被人换成诗句了?否则湍之怎么回了这个。
幸好自己这里还有底本,哪天还是交给苏粼罢。
宁谦团着白绢,思忖半晌,终于把它蒙在了书架角落的樗蒲之上。
仿佛洛邑
第九章
京都的冬季,还是很冷的。
今冬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夜。余雪压得宫闱中的枯枝吱呀作响,又不时“噗”地落下一小堆来。
不知闽越哪里会不会下雪?简瑄一夜未眠,上朝的时候更是万分倦怠,好容易下了朝,此刻窝在榻上发怔。
简瑄有些烦闷地拨了拨面前的炭火,又挥手让宫娥们都退了下去。
炭火烘得四周温暖而沉闷,简瑄甚至感觉多年前的甜腻余香从椒墙檀木的缝隙间再次渗出。他跳下榻去,把窗开得更大了些,凉凉的风从那些空落落的枯枝之间挤进来,贴着简瑄的脸颊而过。
简瑄霎时清醒了些。
有内侍踮着小步走进来,说是新任侍中柳渊求见。
柳渊?
简瑄蹙一蹙眉——如果没有记错,这个人,是宁谦的长姊宁语的夫婿。
简瑄按捺住性子,示意地点一点头:“让他到外间书房等着罢。”
柳渊是辛城柳氏的族人,如今也逾不惑之龄,肤色苍白中透着灰败,如同冬末的残雪,颧骨处却泛着奇异的红。他的眉目间倒是还残存着祖辈们的风华,只是被浓重的阴郁掩饰了九分。因为江缓的严令,柳渊确是着了整套的朝服,交领却随意地半敞着,若隐若现地露了锁骨,虚浮的红。
简瑄不喜欢这样的人,偏偏朝堂之中又多得是这样的人。
柳渊行了拜礼,简瑄勉强地答了,又问道:“今日雪后初霁,正是天寒地冻,不知柳侍中踏雪而来有何要事?”
柳渊见简瑄态度颇为不耐,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恭谦道:“陛下,微臣昨夜忽有奇梦,不知何解……”
简瑄乍一听时几乎登时吐出口血来,正欲发作,又想到不知与闽越之战是否有牵连,便忍下怒意问道:“柳侍中不如说与朕听,解梦之事,朕倒略知一二。”
柳渊躬身拜道:“谢陛下。只是……”话并未尽,柳渊便看了看四周的侍臣。
简瑄哪里能不知其意,便挥手屏退了左右。
“昨夜微臣忽梦周平王迁洛邑,郑庄公窃周粮之事。”柳渊缓缓说道——他声音低哑,目光里满含暗示之意。
简瑄被他说得一怔——郑国发兵驱犬戎迎平王入镐京,功劳赫赫。后郑国做大,窃取成周城郊熟麦。此二事简瑄怎能不知?
简瑄蹙了眉,又蓦地沉下目光道:“柳侍中所指,莫非暗射江令吧?”
柳渊躬身道:“陛下圣明。庆宁末年江缓的确护主有功,只是如今江缓一人独大,倒行逆施指鹿为马,翻云覆雨极是猖狂!大小朝臣,除了那苏将军与他同流合污之外,哪个不受了他的极刑?臣等受其□暂且不表,只是陛下也受其挟制,实在令微臣痛心疾首……”
柳渊说些别的也罢了,偏偏说到了苏粼。简瑄听闻怒意更盛,冷笑一声道:“哦,同流合污,连苏将军也是逆臣了。柳侍中之意,莫不是要做那舍生取义之人,替朕除掉江令与苏将军的祸害?”
他话音又阴又冷,柳渊原本正说到兴头,原以为简瑄心中也是郁愤难平,才欲做痛哭流涕状顺水推舟,听到简瑄的语调,不由得僵住不敢再说。
简瑄顿了顿,又开了口:“然后,便又是如柳侍中一般的世家大族做了那中流砥柱了?五石散,髹漆琴,傅粉涂朱,若玉山之倾,如芝兰之放?——‘郑庄公窃周粮’,柳侍中,这含沙射影之事,可万不能做过了头。”
柳渊万没料到简瑄竟思忖到这步田地,一时战栗不止。
此刻,内侍在外头又道:“江尚书令求见。”
简瑄应了声,江缓脱下厚重的斗篷进殿,一身缁黑朝服规整端肃,简瑄怎么看也还是不顺眼。
江缓望见柳渊站在这里,略吃了一惊,旋即向简瑄行了礼。
简瑄抖了抖黼黻袖口笑道:“适才柳侍中与朕说了个‘周平王东迁洛邑,郑庄公倒行逆施’的梦,朕一时兴起,正与柳侍中拆解,不知江令可有意一解?”
江缓瞥了撇柳渊一眼,突然万分肃然道:“恕缓冒昧直言——不知柳侍中府上可有姬妾身怀有孕?”
柳渊被问得愣怔,嗤笑一声:“确是有一侍妾……与你何干?”
“的确与缓毫无瓜葛。”江缓说得暧昧又无辜,“只是柳侍中可要速速回府——这周平王姓姬名宫湦,姬宫湦‘倒’过来可不就是‘湦宫姬(生公鸡)’么?”
“……你!”
“哎呀,生、公、鸡。”江缓笑得更加无辜了。
简瑄尽量忍住笑:“虽说魂梦之事不可轻信,到底也与柳侍中的……的后嗣关系得紧,柳侍中还是早些回去看看罢。”
柳渊早被气得脸泛潮红,只得横了江缓一眼,一扫大袖,诺诺地应着退下了。
“陛下,这与政事无关之事还是少谈为上。”江缓礼毕,取出一册奏疏来,“这是苏将军的奏疏,大抵是闽越战事,臣知陛下心系苏,嗯,闽越战事——故踏雪前来。扰了陛下清谈,实在非臣所愿。”
简瑄哪里等得了他温吞吞地说完,亟不可待地伸手一夺。
江缓还未来得及松手,这么硬抢,差点没把那奏疏撕成两半。
简瑄展开奏疏上下前后看了几遍,苏粼的奏疏倒和江缓如出一辙,正经严肃地说了一堆,偏偏没有一句是简瑄想要的。
自己想要苏粼说什么呢?
简瑄垂了手,奏疏拉开微黄的长长纸页,“哗哗”响了几声,也蓦然静默。
说什么呢?
譬如一切平安,譬如下旬当归,譬如……思念甚重?
简瑄不敢想——他低头看见一双乌舄从下裳里露出一点尖来。
江缓笑了笑:“陛下,苏将军还留了一封……私信。”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双红鲤信夹。
简瑄蓦地抬了头,那红艳鲜明的颜色,映得满室黯然,仿佛那初霁的白雪也失了光彩。
简瑄一步一步挪着,乌舄此刻愈发沉重不已。江缓也不说什么,将信笺递过去,然后躬身悄然离开。
江缓行至门外,正往身上披那斗篷的时候,简瑄却突然叫住了他:“江令。”
“陛下还有何事吩咐?”
“苏粼不在,柳渊今日又说了这些,江令可要万分谨慎小心才是。”简瑄将红鲤护在怀中,目光里莫名多了担忧。
“谢陛下。微臣自当铭记于心。”江缓抖一抖斗篷上粘着的枯草碎叶,笑容平静。
简瑄叹了口气,又回过神来,忙忙低头专注拆信去了。
苏粼是在冬祀那日回来的,还是红袍猎猎、骄马凛凛的样子。只是迎在最前头的换作了简瑄。
苏粼慌乱又尴尬地要甩掉简瑄握得死紧的手,却不敢太用力,简瑄得了意,笑容比往常放肆了许多。苏粼一时情急,小声说了几句什么,简瑄才悻悻放了手,又回头瞥了身后一列又一列的朝臣几眼,倒仿佛要将他们生吞活剥了。
江缓站在众臣之中,朝苏粼笑着。
太祝江稷已经是两鬓白霜的老人了,历经了世事变迁,为人和蔼谦逊,江缓与他是远亲,冬祀毕了,自然留下来帮忙。
江稷很是喜欢这个同族的少年,却又忧心他将来处境可危,便与江缓多说了几句。
江缓也只是淡然笑道:“从父不必太过忧虑了。我自有分寸,只是恐怕无法魂归故土了,否则……扰了祖辈们的清梦。”
江稷一怔,也无话可说了。
月上中天。
江缓踩着满地的皑皑白雪往城中走去——苏粼应该已经回府了,他这个大将军,空留了偌大的将军府不住,偏要来自己这里霸占。说是“将军府是阿大的,我配不上”,其实江缓知道苏粼其实害怕空寂与孤独。
不止是苏粼,简瑄也怕,他更害怕。
江缓呵出一团白蒙蒙的雾气来,抬眼看它慢慢散开模糊。
冬祀在城郊十里,江缓徒步而行,脚下的余雪“嚓嚓”地响,似乎碾碎了雪下的枯草。
她本该乘车的,只是除了江稷手下的一干令丞们都没有车驾,夜深难行,江缓作主将车上的配饰拆了借他们乘用,自己走着回来。
江缓觉得脚底失了温度时,终于望见了灯火明灭的城楼。正待舒一口气时,他突然听到了极细微的剑刃划过空气的声响,伴着一缕明灭迅疾的银光。
不好。
江缓下意识地抽剑出鞘。
迎面而来的人并不多,江缓略略数了数,大约四五个——信之学剑的那几年,他也断断续续地跟着学了,只是多年未和他人比试,何况苏粼常年跟着自己,更是绝少练剑了。
事已至此,又有何惧?
江缓稳了心神,翻手上前。
雪又开始纷纷扬扬地下了。
守城的士卒陈耀盯着城门上半落的桐漆发怔——本来早该关城门的,只是因为今日冬祀,朝臣们都去了城郊,按律大开城门整夜大开,只进不出。
只是如今夜深,城内的灯火也都渐次暗了,守城的弟兄们轮了职,歇着的都在城楼里取暖,自己和其他几个杵在城门口,只能发呆。
陈耀想到这里,百无聊赖地垂头叹了口气,再抬头的时候,却发现远远走来的一人——看身影,应当是江尚书令。
江缓走得近了,步履又快又急,过城门的时候也不看他们,只是略略地点一点头,却将右手扶着左肩,宽宽的衣袖上落满了雪花。
陈耀行了礼,也不敢抬头去看,只觉得江尚书令似乎有些奇怪。他蹙了蹙眉,也不敢多问。
江缓拐过一道街角,踉跄几步,重重地倚靠在了墙上。他垂了右手,鲜红的温热的血,正从左肩涌出,在衣衫上染了大块的痕迹,触目惊心。
幸而没死。
江缓喘了几口气,把手掌上的血用衣袖草草揩干,向自己的府中走去。
离府门不远时,他已经有些眼花,定了定神才发现门口站着个人——是简瑄的内侍,只是换了衣裳,若不是江缓与他打过几次照面,根本认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