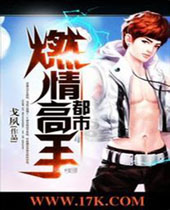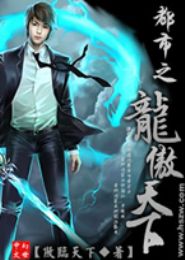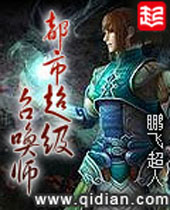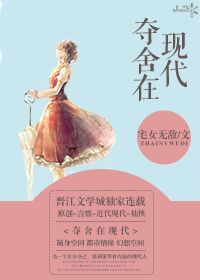现代都市的单身群落-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葛红兵 胡榴明
W女士,30岁,白领,独居,她谈到她的私人生活时说:
我不愿意留在家乡,虽然也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出生、读书到工作,都在那一个地方,家人、亲戚、同学、朋友、同事、熟人都窝在一起,有时候真是觉得世界很小。我一直都没有找一个准备结婚的男朋友,整天除了上班就是玩,父母着急,天天在旁边劝我。母亲说:〃我们倒没什么,也算是读书人,也不想太过问你。但是熟人同事见了面就问你家的女儿出嫁没有,弄得我们很难堪。你有文化又漂亮,何必让人议论我们呢?〃这样,促使我下决心离开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来到了现在这座城市。现在我很好,一个人打工挣钱,然后吃喝玩乐,生活得很自由,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我不是性冷淡,其实我对男孩子还是蛮感兴趣的,曾经真心实意地谈过恋爱,虽然并没有考虑结婚,但是也爱得轰轰烈烈。我认为爱情的结局不一定就是婚姻,婚姻太平淡、太世俗了,我喜欢浪漫的、刺激的感情。家里人说我从小就很疯,现在大了也一样。如果我爱一个人,我才不会管他结婚不结婚,或者他和我结婚不结婚。对这一切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爱那个男人的那种感觉,好像是一场战争似的,男人和女人你死我活的,说起来是爱,其实是互相残杀,爱过一次,人就好像是死里逃生一回。可能我这一生是不会结婚了,但是不能没有爱,也不能没有性。女人一生缺了这些,那就是白做一回女人了。我很高兴我生活在现在这个城市,生活在现代,听母亲回忆她年轻的时候,1960年代,那真的不像是人过的生活。
丁飞,34岁,自由作家,单身男人。采访的时候向他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有研究社会学的专家谈到单身男女的生活状况时说,现在所谓的独身其实是独身不独性,是对婚姻方式的拒绝,对性的不拒绝,其实也不算是真正的独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独身主义者,这样的提法很早就有。从西方开始的,开始也的确是拒绝婚姻和家庭,同时也拒绝性爱,是一种苦行僧主义。欧洲中世纪隐修士修道院制度,参见《基督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后来有加尔文教派,清教徒,最早一批乘坐〃五月花号〃到北美洲的移民,他们提倡禁欲主义。现代的单身者,也可以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很多的单身者,尤其是男性,不是因为宗教信仰,不是去做僧侣,只不过是对婚姻的拒绝,而不是对性的拒绝。单身,不过是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形式,和他生理上的生活应该是不相干的。性,是一个人最原始的生物性的要求,而婚姻和家庭则不是。那么我们当然有权利要求我们自然的生理性的东西,只要是没有违犯法律和扰乱社会,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得到性的,这是我的私生活。独身也好,不是独身也好,这是人们一定要对我们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也没有上哪儿都扯出一面旗帜来声明我们的身份。我觉得中国近几年还是很开放的,一个人怎样过日子,没招谁惹谁就应该算是可以了。我愿意独身,我愿意不独性,你能把我怎么样?还不得两眼干瞪着。
问:专家最后断言,独身永远也不会成为社会主流,西方的独身方式和性解放思潮联系在一起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答:(笑)真的用不着我说,现在社会在怎么往前走,谁心里都清楚。也不是一两个专家在那里道学几句就可以糊弄人的。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怎么做是自己的事,比如没人公开提倡性解放,但是性解放未必挡得住。报上报道的那些个贪官污吏受的教育还少?一个个包二奶养小蜜泡三陪嫖娼,他这也叫性解放,呸!解放什么?完全地倒退,地道的封建余孽,连封建余孽都不是,拿着百姓的血汗钱玩女人,搁到封建年头也是杀头的罪。我们和他们可不是一码事,不结婚完全是个人选择,符合中国限制人口增长的国策。独身也许不能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独身的思潮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你看看现在的婚姻,有哪一个家庭是真正幸福美满的?我很怀疑。一个单身者,他也是一个人吧?是人就有性要求,只要是两厢情愿,只要不是嫖娼不是养两个老婆,我觉得这应该属于中国国情允许范围之内。什么是国情?国情也是可以变的。欧洲中世纪可以随便对人施火刑,到了现代社会民主与法制还不是历史进步的结果?其实中国的传统在性这个问题上一向只对男人开放而不对女人开放,如今所谓的性开放也只不过是一个男女平等的运动罢了。近20年来,中国改变不少,其中性解放应该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听过这样的理论,说性解放是生产力解放的先趋,正确不正确我不知道,还是请专家来评判算了。
单身——我喜欢的生活方式(二)
葛红兵 胡榴明
韩津,男,40岁,某服饰公司总经理,服装设计师,未婚。有私家汽车,在市内和郊区有两套面积很可观的住房。下面是对他进行的访谈:
问:为什么没有结婚?
答:(笑)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才敢拿出来问人家。不过我们都是先说好了的,所以今天我有问必答。其实国外单身的人太多了,没有人稀奇,单身对社会没有妨碍,不是恐怖分子,也不危害社会治安。我嘛,觉得一个人过自由,没有拘束,用不着向谁负责,走哪儿也不用打招呼,心里也不用惦记着谁。我喜欢这种生活,过惯了,一旦改变反而不习惯。
问:你是否曾经在爱情或者说是感情方面遭遇到精神上的创伤?
答:没有,绝对没有。从小我的家庭条件和我的个人条件都挺好,我挺自信的。读书的时候,好多女孩子追过我。现在周围的好女孩也多,长得漂亮的就更不用说了,你们想想我这工作,一年四季都和模特打交道。总之我没有在这方面受到打击,至于女孩觉得受到我的打击没有,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似乎从来就没有很投入地谈过恋爱。
问:(笑)那么你是否是同性恋?前年被人枪杀的世界时装大师范思哲,据说也是一个同性恋。一般来说只有同性恋才会对异性不感兴趣。
答:(笑)肯定不是,我说我没有投入地谈过恋爱,不等于我没有恋爱过。只是觉得太忙,觉得有好多事要做,没有时间来慢悠悠地和女人拍拖而已。我肯定是有女朋友的,但是谁爱上了我是很吃亏的,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是我没有时间陪人家,所以不会有女人特别粘住我不放,因为我的确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情人,但是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服装设计师。
问:如果你有可能结婚,你有些什么条件(对女方)?
答:男人嘛,很自私啦,当然是要温柔贤淑的,漂亮是肯定的,但不要太过聪明,要能干,能理家,还要能够在交际场面上应付,不是电视里交际花的那种社交,是那种夫人的礼仪。这需要天生的内涵和气质,不是一天两天训练得出来的。模特可以训练,夫人是不好训练的,要有先天的素质,首先要看看娘家的出身,然后才是后天的教育。家庭教育是完美女人的基础,粗劣的人家断然出不了有内涵的女孩。所以我找老婆的条件也刁得很,不比交交女朋友,不好了拉倒重来。我这人还是传统的,如果结了婚就不想随便离婚的。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理想,现实中我这条件似乎高了点,所以不大好找,就这么耽搁下来了。
问:你说的女朋友是否指的是情人?
答:可以这么说,但是用〃女友〃要好一些,人家以后还是要嫁人的嘛。
章琴,女,36岁,某科研部门研究员,未婚,有单独住房。
问: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答:26岁那年读硕士毕业就来这儿工作,有十多年了。
问:你对单身男女这个社会现象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这是一件纯私人的事,不值得谁来关注,你就当没看见好了,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没什么不同的。很着意地强调这种区别,我认为这就是歧视。
问:那么你对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否很反感?
答:也不是这样,即使我已经结了婚,如果谁要做另外的调查还不是得做!所以不能说是反感。只不过我也有点好奇,放着那么多的社会现状不去关注,譬如毒品啦、艾滋啦、市场啦、腐败啦、加入世贸啦……放着那么多大事不去研究,没事抓我们干什么?你们调查不调查,我们这一拨人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我们不是社会的主流对吧,我想我们对周围起不了影响。
问:你认为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答:目前我还是愿意继续,不过今后怎样,谁也不好说。
问:一个人生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和乐趣?
答:乐趣因人而异。吸毒的人的乐趣肯定是吸毒。我喜欢安静,喜欢读书。不是说专业书,是文学哲学历史什么的。也爱看电视听音乐,一个人过得很舒服,可能两个人就合不来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目前我不想改变。
上面采访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单身是他们自愿的选择,对于现状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而且生活得很愉快。他们有文化、有思想、有钱、有自信,是地道的单身贵族,这样一批人将是中国单身文化潮流的领导者。
瓶子人与环境(一)
葛红兵 胡榴明
南京有一位女画家喜欢画瓶子,她画的瓶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体奇妙而抽象的意境其实,人世间的哪一个人不是被包容在(或者说是被囚禁在)一只瓶子中呢?环境与现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只瓶子,人们一生所经历的都在有限的空间中演绎。
前面有一节文字提到过因丈夫故世而至今单身的中年妇女王云,我们在对她的采访中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王云自己是一个单身女人,一个单身母亲,很巧合的是,她的母亲和她的祖母也都是单身女人,她们住在一起,成为一个由祖孙三代的单身女人组织成的特殊家庭,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将她们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王云的儿子身上,20年来她们一起含辛茹苦地将那个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关于这个家庭几代人数十年之间到底进行过什么样的人生教育,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测,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几代人组成的单亲家庭里的孩子,天长日久,很容易对婚姻和家庭(指夫妻组合的家庭)产生畸形的看法,选择独身的可能性会很大。从这一个故事来看,似乎女主角对她那个失去父亲的儿子的母爱,成为她选择单身生活的理由,但是,我们假设女主角在另外的一个环境中生活,一个极力倡导婚姻和家庭为社会主流的环境,而不是生活在一个祖孙三代都是单身女人的特殊的环境里,也许,王云再婚的可能性会大得多。所以每一个人身处的家庭环境对于他或是她的人生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
J女士,55岁,小学教师,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优裕的家庭,对生活的质量要求很高,从年轻时起就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自然她出生之后的数十年里,她的理想不可能实现。
35岁那年,因为觉得丈夫文化、职业、修养等各方面和她的希望相差很远,她要求离婚,带着一个10岁男孩独自生活。她苦心教育孩子,培养他上大学,读研究生。平时她对儿子的私生活也管得十分严格,不让他随便地交朋友,孩子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