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生来狂妄-第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挨了挨她,突然缩起身体滚到了草地上。
【好冷。呦呦,好冷!】
【主人全身都燃烧起来了!】
【好冷的火焰,好冷好冷!】
狄安娜难受地蜷缩起来,碧莹莹的草地上只看见一团淡蓝色的火焰在燃烧。蓝色火焰之中,莹白如玉的神之骨喀啦啦颤抖,泛着浅浅的银光,将周围的草地和森林全部封在了冰霜里。
阿波罗匆匆赶了过来,半跪在她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低声唤着狄安娜。
凤凰被拦在漫天漫地的冰霜之外,任凭它怎样扑打着翅膀,也无法突破那层淡淡的银色光芒。
“阿波罗……”
她艰难地叫了他的名字,拼尽全力睁开眼睛,长长的银色睫毛微微颤抖。
“狄……安娜?”
她费力地点了点头,低头看去,左肩处的银色纹路流淌着银色微光,长发散落在草地上,同样泛着碎冰般的光芒。
“我……”我这是怎么了?
她动了动手指,却依旧感觉到了五指骨节在喀啦啦响。
阿波罗轻轻按着她的肩,低头吻了吻她的前额:“你的肩膀以下,仍旧是亡灵。”
唔……
她的头和肩膀已经恢复了原状,肩膀以下,却仍旧是亡灵?
狄安娜粗粗。喘了口气,抬头问阿波罗:“你呢?有没有觉得哪里难受?”
阿波罗摇了摇头,看了一眼森林外的凤凰,默默计算着他还要承受多少次凤凰之火,才能让她彻底恢复过来。
狄安娜冲金角小鹿招了招手:“去替我拿件衣服。”她身上那件又长又厚的黑色斗篷,已经被烧得连渣都不剩了。
小鹿嘤了两声,乖乖地跑到旁边的月神殿里,给她叼了一件长裙出来。
狄安娜微微皱眉:“换件斗篷。”
“别。”阿波罗阻止了她,转头吩咐金角小鹿,“我记得你主人有两副长手套?替她拿出来。”
小鹿瞅瞅狄安娜又瞅瞅阿波罗,吧嗒吧嗒地又去叼了一双手套出来。
狄安娜瞪它。
小鹿软软地“咩~”了一声,转身冲狄安娜晃了晃小尾巴,撒开蹄子跑进森林里,瞬间就没影了。
阿波罗噗嗤一声笑了:“它还会学羊叫?”
“是啊,偶尔还会把自己当成只小猫,喵喵地叫着然后趴在台阶上晒太阳。”狄安娜颇为无奈,“我纠正了它很多次,结果它还是隔两天就会就忘记自己是头鹿。”
阿波罗一愣,笑得愈发大声:“宝贝儿,你的圣兽和你一样可爱。”
“我可没有健忘症!”狄安娜愤愤地伸出两根手指,抵在阿波罗的胸膛上,然后瞪他。
可惜在阿波罗看来,她的怒视根本没有半点威慑力,反倒带着几分别致的风情。
阿波罗细心地替她换好了长裙,又替她戴上了手套。狄安娜全身像是散了架似的疼,根本不想动弹,也就任由阿波罗折腾。阿波罗替她换好衣服后又转身去月神殿里拿了件长袍披上,才俯身抱起她:“我们回去。”
狄安娜忽然觉得不妙:“我的神殿里,怎么会有你的衣服?”而且是摧毁后又重建过的神殿!
阿波罗毫不在意地“哦”了一声:“上回顺便在你这儿住了两天。”
他说得越是轻描淡写,狄安娜就越是觉得不妙。这家伙连衣服也给打包过来了,该不会是有长住的打算?
在她说出心底的疑问之后,阿波罗又低头亲了亲她的眼睛,赞美道:“宝贝儿,你真聪明。”
狄安娜决定今晚一脚把阿波罗踹下床,让他乖乖去睡地板。
反正这大热天的,大理石地板可比那张小木床要凉快多了。
回到特洛伊城之后,阿波罗依旧去修他的城墙,狄安娜则不得不去买了一条长长的头巾裹上。毕竟她的发色和瞳色都太显眼了。除月神——以及科洛尼斯公主——之外,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头银色的长发,和一双银色的眼睛。
一位俗称“监工”的矮个子男人对阿波罗的临时失踪很不满。
阿波罗理直气壮地微笑:“我不过是去吃了个午饭。”
狄安娜无奈地摇头叹气,上前递给阿波罗一条擦汗的毛巾,然后去了特洛伊城外的森林里狩猎。不管怎么说,在成神之前,阿波罗的午饭总归是要解决的。
至于波塞冬?
……这种事情还是让海后来操心比较好。
不过令狄安娜意外的是,在森林里,她碰上了一个很久没见的神,不,两个。
瘟疫之神和……已经长成少年的医者之神,阿斯庇勒克俄斯。
第75章 初入特洛伊三
少年一见到狄安娜;立刻兴冲冲地扑了上来;抱着她的脖子蹭了蹭:“母……”
咚!
喀拉喀啦——
狄安娜连同少年一同摔在了草地上,全身骨头都散了架。她动了动手指,重新将骨头一根根接好,然后伸出一根纤细莹白的指骨;轻轻戳了戳少年的脑门。
少年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神。”
瘟疫之神摇了摇头;走上前抓着少年的后领,像当初提着白嫩小团子那样,将少年提了起来。少年极不合作地在瘟疫之神手里扭来扭去;垮着一张脸嘟哝道:“我不是故意的嘛……”他明明看见母亲已经长好了!……虽然那双长长的白色手套看上去很是奇怪。
“我本以为你已经足够大了。”瘟疫之神的语调平平淡淡,不带丝毫感情;“现在看来;还是得先用药将你变回去。一见面就抱着母亲撒娇;像什么样子?”
少年惨叫一声:“不要啊——”
“驳回。”瘟疫之神不知从哪儿弄出一把金色的药粉,朝少年兜头洒了下去。药粉纷纷扬扬地沾在了少年的头上脸上身上,将他的骨骼变得纤细又窄小,最终缩成了……一枚白白嫩嫩的小团子?
狄安娜瞠目结舌。
她费力地从草地上爬了起来,把几根错了位的骨头挪回去,又揉了揉不小心闪到的腰,突然怀里一沉,一枚白嫩小团子已经扑到了她的身上,搂着她的脖子,抽噎几下,小手指颤巍巍地指着瘟疫之神向她控诉:“父神最坏最讨厌了!母神要帮我报仇哼!”
瘟疫之神淡淡地撇他一眼:“还是等你长大了,再自己找我报仇,这样比较妥当。”
小团子委委屈屈地缩在狄安娜怀里对手指。
找父神报仇什么的,这辈子是不用想了。半年来他曾经无数次试图找瘟疫之神报那三巴掌的仇,最终永远是被瘟疫之神痛揍一顿,然后裹上厚厚的药泥,塞进药罐子里发霉。
“你要当心些。”瘟疫之神温和地对狄安娜说道,“这孩子鬼点子特别多,身上的东西也不少。一不小心就会中了他的招。”
小团子重重地“哼”了一声:“才不是呢!母神最好了!才不在母神身上下药呢!”
“哦?”瘟疫之神又瞥了小团子一眼,“终于承认你在我身上下药了?”
小团子缩缩脑袋,在狄安娜怀里蜷成一颗球,用屁。股对着瘟疫之神,完全是一副“我不认识你”的样子。
狄安娜安抚地拍拍小团子的背,转而问瘟疫之神:“这些天,你将他带到哪里去了?”
“不过是带他到各地去转了转,学些新的医术。”瘟疫之神答道,暗金色的眼睛里渐渐染上了一抹温柔,“你就这么放心地让他跟着我?”
狄安娜叹了口气:“阿波罗……”
“月神殿下。”瘟疫之神打断了她的话,目光在她恢复如初的面容上流连,眼中的温柔之色又浓郁了几分,说出来的话却依旧不留情面,“这是你第四次错认我了。我说过,我与太阳神殿下没有任何关系。”
小团子轻轻“耶”了一声,困惑地转过头,盯着瘟疫之神一阵猛瞧。
狄安娜再次叹息一声,总觉得她每次遭遇瘟疫之神时,叹气的次数都会远远超出平日。
“是,你与太阳神无关,可光明之神呢?福玻斯·阿波罗,永恒的光辉与荣耀,永恒的……黑暗之子。”
“黑暗之子”出口的瞬间,瘟疫之神微微僵了一下。
“他想见你。”狄安娜已记不清是第几次叹息,“阿波罗他,想见见他自己。”
瘟疫之神紧紧抿着唇,双手亦紧紧握成了拳头,暗金色的眼睛里暗流汹涌,汇成最浓郁的黑暗。
狄安娜不说话也不动,抱着小团子站在瘟疫之神身前,静静地看着他。
“……好。”
“我会去见他,也会告诉阿波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瘟疫之神渐渐松开了拳头,走到狄安娜面前,低头看着她,压抑已久的思念汇成滚滚洪流,如同岩浆喷发,烈得吓人,也烫得吓人。
明明已经将所有的思念尽数交付给了新生的太阳神,却依旧忍不住想她,每时每刻都在想她。
她太过聪明,也太过剔透。这件事情,根本……根本就瞒不了多久。
他抬起手,轻轻碰了碰狄安娜的脸颊,而后骤然将她抱进怀中,暗金色的面具骤然滑落,滚烫的唇紧紧贴着她的前额,又渐渐往下,小心翼翼地在她的长睫毛上轻轻碰了一下,然后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放开了她。
狄安娜渐渐抬起头,却依旧看不清他的脸。
“你不该这么做的。”瘟疫之神哑着嗓子说道,“我早已放弃了所有,也早已不再拥有那个名字。狄安娜,阿波罗他……”
“阿波罗很好,一直都很好。”狄安娜隐隐有些愠怒,又有些难过,“我不明白你这么做的缘由。可阿波罗,我想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爱你一切的好和不好,你的光明你的黑暗你的真诚你的犀利你痛苦时的冰冷和阴郁……”
“够了,狄安娜。”
“……我想要一个完完整整的你,而不是,而不是你为我创造出来的,虚假却又美好的梦境。”
“够了。”
“吻我。”
“你……”
“吻我,阿波罗。”她直直望进了那双暗金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
小团子轻轻“耶”了一声,看看对峙着的两尊大神,乖乖地捂住了眼睛。
瘟疫之神紧紧抿着唇,抬起手,却又在触碰到她的那一瞬间滑了下来。
“我该去找他了。”瘟疫之神后退两步,声音又沙哑了几分,微微有些颤抖。
“阿波罗——”
“你知道我身上带着些什么吗?狄安娜。”瘟疫之神艰难地开口,“痛苦、绝望、怨愤、不甘,更可怕的,是来自爱神的诅咒。我离你越近,对你的伤害就越大。你的死只是个开始,变成亡灵也永远不是终结。狄安娜,我——”
“你觉得我会怕?”
“可我怕,我会害怕。”他渐渐闭上了眼睛,不让她看见自己的真正的情绪,哪怕一丝一毫。
害怕她因他而受到伤害,害怕造成永远也无法挽回的结局。
她死过一次,已经够了;转过一次转盘,也更是够了。
如果他的存在只会给她带来厄运,那么,宁可,永远离开。
一连串沉重的远远传了过来,伴随着剧烈的呼吸和心跳声。狄安娜转头望去,本该在特洛伊修建城墙的阿波罗正在朝这边奔跑过来,额头上滚落了大颗大颗的汗珠,表情隐隐有些痛苦。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阿波罗好不容易才跑到了狄安娜身前,扶着一棵棕榈树站稳,一只手紧紧按着心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每次你见到狄安娜,我都会胸口闷得疼。老师——不,我该怎么叫你?阿波罗?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瘟疫之神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依旧平平淡淡地说道:“抱歉。”
“嗯,这回我能感觉到一丁点歉意。”阿波罗紧紧盯着他,抓了抓头发,直到把一头金发抓得乱七八糟,才烦躁地问道,“喂,说说你是怎么回事?我总不可能无缘无故把自己分成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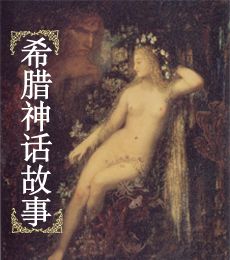

![[希腊神话]原来我是向日葵啊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9/9831.jpg)
![(希腊神话同人)[希腊神话]复仇者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12/12584.jpg)
![[希腊神话]女神的品格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13/13832.jpg)
![(希腊神话同人)[希腊神话]灰瞳女神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15/15069.jpg)
![(希腊神话同人)[希腊神话]冥府之主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22/22897.jpg)
![[希腊神话]生来狂妄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31/314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