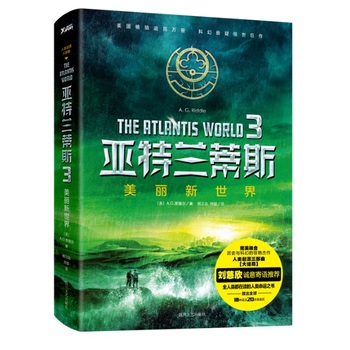世界三部曲1:世界在爱情中成长-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
大爷抬起头,目光里充满询问。
“不,不,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跟着八姐……”
“你就别问了。”
大爷像拥着一只小羊羔,声音幽幽地说:“杏儿,我们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杏儿拉了被子,盖在他身上,侧了身子,伸出双手,捧着他那张略显苍老的国字脸,嗲嗲地说:
“秀水,哦,我的……哥,我想去看看你的家乡,那条江,那条碧绿的,能捞起鲢鱼的江……鲢鱼的嘴,吞大江里的水,是啥模样?”
“哦,嘴,鲢鱼的嘴,红红的,吞吐出一条沸腾的水汪汪的大江……”
大爷接住杏儿热热的嘴,喃喃地说。
杏儿一动不动,咧咧嘴,听着远处的炮声,那双美丽的春杏眼,睁得很亮。
炮声
至今,表哥骆光雄可曾从神秘恐怖的仙女洞中逃出来?
……
轰隆隆炮声在这座城市的东南角震天巨响。军阀大爷的部队和攻城的部队,据说,在那片燃烧的山岭上成胶着状态。尸横遍野,岩石在燃烧,空气在燃烧。河里的水、江里的水、瀑布口的水,都在燃烧。飞机在空中盘旋,大地在炮声中震荡。大爷逃离这座城市的准确时间,也是在这胶着炮轰三天三夜的最后一个夜晚。春杏把裹着桃子头盖骨的小檀木匣子放进铁箱里。他们在炮声中晃动的卧室光影里,草草率率完成了在逃离这座城市之前,一个军长、司令和新近送来的盐商的小女儿之间繁琐畅快的生命礼仪,——之后,还没有“还阳”,恢复那时剧烈消耗了的体力,就匆匆奔逃。只有在那个时候,大爷总表现出一个军人,一个男人,猛虎一样的全部力量。很快地,他穿上了军装,扎上了武装带,腰间别一把
意大利手枪。自当了军长,大爷身上就很少带过枪。这天晚上是个例外。大爷和杏儿都分别带了枪。熟悉的道路在炮火轰鸣中时隐时现。他选了一辆美国人送给他的最好的越野轿车,开出风雨飘摇的公馆。“叭”的一声,公馆门前的电灯泡突然破碎。大爷刹住车,愣在那里,望着卧室窗户映现出的那缕他十分熟悉的灯光。在温柔的灯光下,他批阅文件发号施令、和他一个个女人,一群群儿女,度过了上帝给予他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走吧。”杏儿催促他。大爷闷着头不动。忽地扭住杏儿的衣摆,躬着身子,钻出驾驶室,走进公馆,摸摸索索好半天,找出一只电灯泡,安在公馆门前,然后拍拍手上的尘土,无比惋惜地环视公馆一周,脚步虚晃着,揽了春杏绵绵的腰身,蹩进了那辆黑色小轿车。
31947·红色青春(1)
铁窗内外
怀着一腔热血,梓茕来到汉英冰冷的铁窗前,聆听夜莺的歌唱,带着血丝。和军阀大爷文秀水同一家族,汉英也来自那条静静地流淌在莽莽群山之中的大江。大江蜿蜒曲折,云缠雾绕,含翠吐绿。分别的时候,汉英怀着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的孩子,和他一起行走在这座城市边缘的那截狼犬密布的小巷。他揣着购置枪支火药炸弹的密令和黄金,准备乘船回到苍茫起伏青云山的山峦中去,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迎接远不止这一个城市的黎明。
汉英停下来,一手叉腰,满脸惨白地对他说:
“蒋哥,等等我。我的下面……涨得不行,我要找个地方,撒泡尿……”
蒋哥揭下头上的黑色宽檐帽。揭帽时,挺立在黑暗中,黑衣长衫,高大的身躯,他的动作和身姿,很潇洒。他机警地环顾四周,向汉英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去吧,我替你站岗放哨。然后,汉英就去了。很涨的下面使得汉英没能来得及看蒋哥最后一眼,她也没能给他留下最后一瞥,就挺着肚子去了。从此蒋哥和汉英先后离去,消逝在这个城市的黑暗中,随寒风呜咽着再也没有回来。留下我们和他们一道,咀嚼吞咽如火岁月里的生命与爱情,和那一代战斗者壮丽的青春。
弹洞,硝烟。多少次死战恶战,多少次峰回路转,蒋哥始终没有忘记分别那一刻,汉英的脸,那张曾如花似玉的脸,怀着几个月孩子的孕妇的脸,灰白惨淡,恰如那时如晦的黎明,鸡鸣时的天空。
汉英是江边小镇川军师长文秀章的独生女儿。
革命
那个年代,“革命”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汉英万万没想到,扎着长辫子,拎了小皮箱,穿了咖啡色皮衣,白裤子,脚蹬黑色小皮靴,碎步走出闺房,亮亮的眼睛汪着泪水,红扑扑的脸蛋没有表情,白生生的细牙使劲咬着小嘴红红的嘴唇,强咽着说不出的羞辱和愤怒,使自己不要哭出声,向站在公馆石狮子门前的黄桷树下的父母,淡淡挥手告别,坐上驶向省城的那辆扎着红绸响着铃铛的四轮马车,沿着初春的江岸,一路风儿鸟儿花儿陪伴着她,穿过荒芜的田野,留下饥饿的人群,马鞭摔碎黄昏,铃铛摇醒黎明,然后,马蹄嘚嘚,清脆地敲响晨雾迷蒙的省城陌生的大街,神秘地转入舅父家那条黑墙幽幽的小巷,——就叫参加革命!的确,汉英只为躲避父母的包办婚姻,才决定离家出走,到省城找舅舅——开明中学费校长,继续上学。那时,她幼小的心灵对革命一无所知。父亲文秀章已是这个江边小镇上响当当的人物之一,川军师长。几十年征战岁月,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现实,使父亲明白,女儿只有找个有权有势又有钱的靠山嫁人,最稳当。他的同僚们家里的许多英气勃勃的男孩、如花似玉的女孩,吵吵嚷嚷到外面的世界读书,一个个都读出了乱子,弄得娘老子背着黑锅。政坛、军界、社交圈内抬不起头。于是,父亲和曾在省城戏班做过当家花旦的妻子商量,把年仅十六岁的汉英,许配给当时他驻扎的那个城市实业界银行巨头的三公子潘宪文。父亲用枪逼着汉英参加订婚典礼。她也说不出那个眉清目秀留了分头,穿了一套黑色西服,白衬衣,红领结,黑皮鞋的公子哥儿有什么不好。只是心里别扭,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何况,订婚当天,进入闺房,看她相片的时候,潘三公子就差点摸了她的脸,摸了她的胸。尽管只在她扎了蝴蝶结的刘海儿下凑了个亲近,尽管只在她那件小羊皮红色夹克衫外面碰了一下,她也愤怒地把潘三公子推出了房门,蒙头大哭。姑娘好比一朵花,她想,花还没有完全开艳哩,不适合也不允许野来的蜜蜂叮着花蕊嗡嗡叫。汉英坚决地以倒地撒野来回绝了潘三公子的订婚礼物,并以剪刀自残相威胁,直到父母同意她上省城到舅舅办的中学读书。婚姻一事,哪怕是和银行家的三儿子订婚,也要等读完了中学再说。
从闺房出来,跨进院子,一群小鸡从厢房前的花坛背后向她追来,黄花一样蠕动在她的脚下,唧唧喳喳,绕着她的小马靴叫着跳着不肯离去。汉英走得急了,一不小心,踩伤了一朵“小黄花”。姨母踮着小脚跑过来,拾起张嘴伸腿的小鸡崽,立即把那团毛茸茸的生命,掖进宽松的袖口里去。正在槐树下帮着表舅套马车的父母没有发现。马车摇着铃铛远去。姨母偷偷从衣袖里松出鸡崽,已经死了。她顺手把死鸡丢进厕所,埋头在房檐下走来走去,然后,进入汉英走后留下的空空闺房,在梳妆台上嵌着汉英相片的镜框背后系了一匹红绸。
“菩萨保佑我们的汉英姑娘,命,硬哩!”
姨母信佛。她想,系了红绸,汉英的性命就会得到佛祖的保佑。
……
山里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几年后,一个秋霜冷凝的夜晚,飕飕的山风,摇曳着帐前神案上那盏如豆的桐油灯。盘着头发穿着细碎红花小棉袄紫色裤子青布鞋的中心县委书记员文汉英,正俯案用小毛笔抄写各乡报来的起义军骨干名单,不时抬头望望油桐树背后黑黝黝的窗外那条通往山里的小路。脚下的铁盆里明灭着松木炭火,灶台上的铜罐里炖着一只老母鸡。月亮还没有出来,小学校内外静悄悄。隔壁姚婶家二狗子吆喝小鸡仔的声音隐隐响起。又一股山风从窗口灌进来,吹动她额前的头发。汉英打了个寒颤,连忙伸手挡住油灯,看看小闹钟,八点刚过。估计蒋哥还不会回来。她放下笔,站起身,搓搓手,关上厚厚的木窗板,拨拨案上的桐油灯,再弄弄盆里的木炭火,屋里顿时明亮了许多,温暖了许多。她直起腰扩扩胸,几步走至灶前揭开铜罐盖,一股浓浓的香味窜出来,满屋飘香。“呀!”她打心眼里乐了,不自觉的哼起了,“革命的青年……3·5│3·2│1—│”,她突然伸伸舌头,望望四周,“糟,又违反革命纪律了。”她想。汉英和蒋哥有约在先,在这里一定要把所有革命歌曲忘掉,决不能唱。不唱就不唱吧!她想。革命纪律是革命的需要,也是保护自己的需要。她嗅嗅鼻子,关上铜罐盖,轻轻揭开,用竹筷挑了挑,“真香!”她使劲吞了一口唾沫,挑起鸡背上一溜白嫩的肉,望望,想放进嘴里,但,想,嗨!偷吃,被他看见,多不好!把鸡肉放进罐里,夹起一块白萝卜,看看,再用勺舀起一口鸡汤,闻闻,又倒进锅里。她这么闻啊嗅的,反复做着吃鸡喝汤的游戏,一点儿也没有吃进嘴里。今晚的鸡一定要和蒋哥一块儿吃。汉英想,而且一定要让他吃第一口。这段时间,蒋哥没日没夜地工作,生活艰苦自不必说,这只鸡是蒋哥的表嫂姚婶特意送给他补养身子的。不久前,蒋哥进山“家访”,当然是为准备起义建立秘密组织,深夜,伸手不见五指,走细雨中的山路,摔伤了脚脖子……想着在山里开拓革命事业的艰辛,汉英心里沉重。想着马上就要举行的起义和暴动,她心里快乐。想着蒋哥和她之间一两年来的特殊关系,她心里又沉重又快乐。但,究竟沉重多还是快乐多呢?她心里混合着各种说不出的味儿。一想到这些,似乎屋里的温暖和鸡的香味儿,随着飘飘的思绪,带着惆怅,带着美好,带着遗憾,带着一想起来心里又像灌了蜜一样的甘甜,像猫咪抓挠一样痒痒……在这暖融融的秋夜,她芳心萌动。她坐回桌前,握着小毛笔,对着桐油灯,望着桌上镜框里,蒋哥和她的“结婚”照片,端起来看了又看。抿嘴乐了,脸蛋儿红了。嘻嘻!嘻嘻!我和他算什么夫妻呀?这是他们到地下党省工委接受新的任务之后,别别扭扭地在一家私人小相馆照的。当然,那家小像馆也是秘密据点。那天,蒋哥被任命为这个青云山区十多个县的中心县委书记。组织决定,由他们二人假扮夫妻,到他的亲戚,也就是姚婶家——大山深处,有一条小河的断桥边,祠堂里的小学任教,主要任务是建立组织,适时组织武装暴动。那时这个中心县委机关只有他们二人。你想,对一个二十不到的黄花闺女,要和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心县委书记一起,以这样的身份度过这样“革命”岁月,多难多别扭,而且,表面还要装得多自然。山外狼犬遍地,保甲制度严密,山中匪患横行,无数次清乡,他们都化险为夷。没露出一丝破绽。他们的生活是艺术,像演戏演电影。汉英笑了。他们曾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摩擦。油菜花黄的春天,蒋哥接受了中心县委书记的任命,春燕衔泥垒窝的春夜,姚婶过生日,给他们送来一盆鸡汤。恰巧,那天是汉英十九岁的生日,她买来一瓶白酒,说是庆祝他当上中心县委书记。庆祝他们的事业顺利成功。他们喝了鸡汤也喝了酒。一瓶酒喝完之后,汉英想到了父母,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