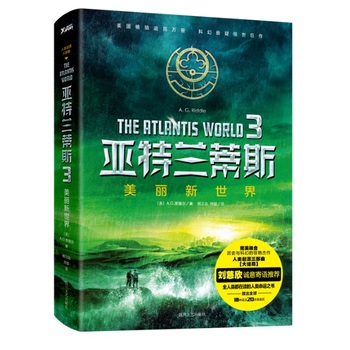世界三部曲1:世界在爱情中成长-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娘的遭劫,自然只好忍气吞声。
出去之后,又到哪里?去军统,二娥不愿。再去公主家,二娥不肯。她只好再次回到战时保育院,继续做保育员。令美国大兵不解的是,姑娘恢复了往日的神态,脸上露出了笑容,保育院里又响起了她清亮的歌声,不再靠他用强奸来拯救她了。她被谁强暴了么?
杰姆纳闷。
战争中的人们啊!
二娥心底的秘密,只有她自己知道。毕竟,她已到了十九岁的年龄。
她应该有爱,应该有对爱的向往。
大轰炸
心里揣谁也解不开的爱情秘密,二娥在轰炸后的保育院忙个不停。她似乎忘记了那遥远的山乡,吕梁山上的朵朵白云,汾河水里的点点浪花,汉口那条人流拥挤车马践踏的泥泞道路,炸弹轰鸣,死里逃生……如云烟飘逝的往事和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处于同一世界,好像是上辈子另外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朋友呢?干练女孩呢?二娥甚至淡忘了那栋金壁辉煌的小楼里,红色幕帘下彩灯照耀中翩翩起舞的那只娇媚的裸天鹅,……彩云一样轻软的锦缎里度过的那个使她全身崩溃撕裂的春宵。二娥再也不能依偎在父亲胸前,呼吸那一阵阵生命的芬芳,感受到他心脏强有力的搏动……哦!男人,中国男人,美国男人,黑脸男人,白脸男人,二娥忘不了父亲手挥大刀一头扎进吕梁山中那挺拔的身影。战争年代,也许眼下的日子,那样伟岸苍然的身影才像男人。她不知目前的日子怎么过去,将来的日子怎样来临。她机械地教孩子们唱歌,给他们洗脸喂饭洗衣裳。然后,默默地听保育院同事们讲前线传来的悲讯和喜讯,城里的官僚政客军官歌女妓女的故事。听过之后,相视一笑。笑中含着苦涩。保育院的老师们吃着粗糙带渣带泥的霉米饭,那饭苦苦难咽,咽下之后,心里有时也会生出别样的甘甜。
这个世界,有男人,就有爱。而爱和男人究竟是什么,二娥觉得像她的世界本身一样,朦胧而茫然。
那天上午,阳光拂煦。保育院门背后高高的山梁上,先是响起汽车喇叭声,接着传来敲锣打鼓声,小车后面慢腾腾地跟来一辆大卡车。那是给保育院送衣服和粮食的汽车。车至门前停下,黄桷树的浓荫里走出一队杂七杂八的人马。曾帮助指挥孩子在轰炸中转移的坚强女人嫱干妈,笑容满面雍容华贵地走下车来。妇人、太太、小姐、军官、卫兵,还有高举镁光灯的记者,众星捧月般的簇拥着她。二娥清楚看见杂乱的人群背后,跟着那位高大的美国大兵杰姆。他怎么……也来了!她的心,又开始阴郁下来,她深深吸了口气,……心,像被毒蛇咬了一口,怎么她们都来了?……几天前,二娥隐隐感觉这天将会到来。玛丽院长脸上挂了一丝灿烂的笑容。她丈夫过去的部队在滇缅前线又打了个大胜仗。战时保育院在战火硝烟中成立已有三个年头。她们买来大红彩纸,写了标语,扎了花。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抗战老歌新歌,同事们排演了新的话剧,院长弹奏着抒情味十足的苏联歌曲,二娥的节目依然是和孩子们一道表演《水兵舞》。这些天,她不知跳了多少遍,每跳一次,她都尽情舒展,青春四溢。上午,开会,欢迎,照相。中午会餐。肥肉烧萝卜。下午,开会,来宾和保育院师生联欢。简易舞台上,挂着孙中山画像。高高屋檐和黄桷树的树梢之间,拉起了一幅大红的标语。黑压压的院子里,集合着两三百个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化了妆的儿童。他们上台合唱,音乐伴奏。催人泪下的话剧。热烈鼓掌。优美的舞蹈。她的独舞《小天鹅》博得了阵阵掌声。小小舞台上舞动着洁白的精灵……遥远的孤儿院……白色的日光灯……猩红的帷幔……浅蓝色的幕帘……二娥似乎比过去高出了一头,白嫩的脸,汪着水的眼睛,油亮的辫子,浅蓝色的蝴蝶结,洁白的短裙……翩翩起舞,像炎热夏天从遥远的山峦掠过来一阵轻风,又像灿烂阳光中缠绕在黄桷树梢上的一缕云霞。一双黑色的布鞋,套在她纤细的小脚上,轻轻点地,像蜻蜓独立荷花,轻捷地点过平静水面。玛丽院长弹奏钢琴的双手像起伏的波浪,优美的乐曲在她十指间流淌。记者举起镁光灯,美国大兵的目光久久停在她身上,孩子们的眼睛里射出一条条彩带,随着她的舞步旋转萦绕。她们忘却了天空,忘却了夕阳,忘却了天空和夕阳下燥热的黄昏。
黄桷树梢头,知了鸣叫。古老祠堂,木板搭成的舞台上,一束清亮的光芒在闪烁,一片纯净的云霞在燃烧。
……
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怪叫声撕破了夏日黄昏山峦的宁静。
敌机来了!
小铁箱
这次轰炸突如其来。没有警报的嘶鸣,没有激昂的动员,没有惶惶的奔跑,没有奔跑惊叫之后,躲在防空洞拥挤的岩石门前,望着轰炸机黑乌鸦一样的翅膀,铲断树梢上的枯枝败叶,蜻蜓似地栽进抖动颤栗的山峦那边去——那种惊恐之后未被轰炸的狂喜。庆祝战时保育院成立三周年的舞蹈表演正进入关键的、忘情的、如雏鹰展翅、如疾风盘旋的关键时刻,“呼——呲呲——噼里啪啦——嗵!”一枚炸弹从山峦上空呼啸而下,劈断黄桷树粗壮的枝丫,重重地栽进树基下的沟坎,发出一声闷响,没有爆炸!紧接着,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响彻山谷,炸弹在山谷中四面开花,掩藏在岩石中的兵工厂和兵工厂前面的一大片征做文物管理用的民房,立即罩进浓烟弥漫的火海。
舞台上下的人们惊呆了!短暂沉默之后,他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也许,这段时间空袭的训练,使他们懂得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要保持冷静,而将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早预料到的。台下的嘉宾首先起立,台上的保育院院长、教师则快速而有秩序地把排好队的孩子带出大门,带往保育院背后的防空洞。轰炸机的怪叫声、炸弹落地的尖叫声,远处人们的呐喊声,在黄昏的山峦中震荡回响。防空洞里,大人小孩屏声静气,耳朵里塞满了洞内外混合着恐怖的声音。
“回来!回来!危险——”
守在防空洞门口的玛丽院长,挥动手臂、张嘴高喊。众人望去,只见通往保育院的石梯小路上飞快的跑动着身穿白舞裙的人影。轰轰隆隆的爆炸声在远处响起。人影儿不顾一切地跑回保育院。敌机在山头上俯冲下来。不一会儿,在众人凝视的目光中,那个白蝴蝶一样的人影儿紧抱着一口小铁箱,跑出保育院大门。敌机的尖叫声更响了。炸弹接二连三在山沟里爆炸,浓浓的烟雾弥漫着保育院,黄桷树被炸断了,大火呼呼燃烧。她的身影在烟雾中时隐时现。又一架飞机从山头上俯冲下来。
“二娥!卧倒,卧倒……二娥!”玛丽院长急得大叫。杰姆箭一般地冲出防空洞,向那人影儿跑去。炸弹声笼罩在他们周围,千万种声音在树梢上、山峦里怒吼咆哮,炸弹从低黑的空中沉闷落地,四面开花。
杰姆猛跳过去,狠狠一把,把二娥推进他们身旁的山崖。炸弹响起,山崖剧烈震荡。杰姆山一样的身躯紧抱住她,沉沉地滚下背面的山沟。她的怀里,依然死死拽住那口精致的小铁箱。
浓烟滚滚。爆炸声,防空洞里的呐喊声,飞机的鸣叫声,响彻山谷,久久回荡。
血日黎明
那次轰炸,从黄昏开始,延续了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又一个黎明,这个城市无法醒来的黎明。阴云低垂,大地无声,硝烟滚滚,一幅惨绝人寰战争图画,展在昔日的青山秀水间。据载,那场轰炸,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无人收尸的乱坟岗,把一个能容纳上万人的防空洞,变成了塞满尸体的太平间!那是怎样的战争年代的太平间啊!因窒息而死亡在防空洞里的人数,官方记载一千六百到八千人,真实的死亡,远远成倍地大于这个数,以至于当时的官方不敢明确公布死亡的数目。
黎明,满目疮痍,弹痕累累,瓦砾断墙,尸横遍地。黎明,本身就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大地静默。直到中午时分,冒着青烟的断墙残壁间,才慢慢蠕动着些许人影儿。那些没被炸死的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默默清理他们面前不成形的道路上瓦砾丛中的尸体。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自发组成搬运尸体的队伍,像蚂蚁搬家一样,把残缺不全的尸体从防空洞里拖出来,堆在紧靠大江边的那一大片乱石滩上。那些窒息而死的是怎样的尸体啊!青紫肿胀,龇牙咧嘴,上上下下,盘根错节,像坚硬的面团,僵直的木棍,抓扯在一起,扭曲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拖了三天三夜,拖也拖不完。当初他们修筑这个防空洞,从洞里拖出的岩石和泥士,整整拖了一年多。这些尸体难道就是当年那些岩石的化身么?人们在死亡恐怖笼罩着的城市里,苟延残喘。
据说,轰炸停息后的第二天早晨,一辆黑色小轿车,从遥远的青山那边,向这座死亡的城市艰难地开来。朝霞把遥远的天际涂抹成一片绛红,映照着尸体横陈浓烟滚滚的断垣残壁。黑色轿车停在一大片瓦砾堆前,从车上钻出一个高瘦的人影。他就是戎干爹。干爹披了一件黑色大氅。一身黄呢将军服,紧紧套住他坚硬的身躯,给这幅悲怆的画面平添了几分军人的悲壮。他神情肃穆,锃亮的马靴,小心翼翼地绕过面前的尸体,踩着燃烧的房梁,向浓烟丛中的尸堆走去。他的腮帮在频频颤抖。望着那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突兀的白骨,折断的四肢,打掉的牙颌,一张张含着石块泥土的嘴,干爹流泪了。在血红的朝霞中,干爹慢慢褪下白手套,把干瘦的右手,举向帽檐。浓浓的焦糊味、钻心恶臭的尸味,裹着清冷的晨风,向他袭来。不知因为痛苦,还是被脚下的尸体瓦块绊了一下,他高挑的身躯,重重摇晃,险些跌倒。小车边的随从,踩着石块尸体向他跑来。他突然坚强地立起,转过身,挥舞着手中的黑色拐杖:
“不许靠近我!”
干爹尖利地叫喊了一声。
随从远远望着他,不敢向他靠近。干爹慢慢转过身,艰难地一步一步绕过堆堆尸丛,摇晃着走向这个饱受战火摧残——死亡恐怖笼罩着的城市——早晨,血染的黎明,他举臂大叫:
“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一个声音在他心灵深处高叫:
“强盗,等着吧!我要和你们血战到底!”
晚上,刚修复的无线广播电台的电波里,立刻向全世界传达出了戎干爹那战栗而痛苦的声音。
这个城市的战争啊……究竟谁在真正为它负责?
创伤岁月
那晚轰炸停息以后,保育院的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默默修复他们被破坏了的家园。夏日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烤着被炸毁的山峦和村庄,一双双布满青筋的手,艰难地搬动石块,垒筑一座座高墙。在叮叮咚咚的铁锤敲击声中,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深深的伤痕,渐渐平复。大自然怀抱里的青山秀水,渐渐吐露生机。大火灭了。简易街道重新修起来。遍地瓦砾石块和那一具具尸体慢慢清扫干净。据史书记载,这座城市那些日子,大街小巷停放着棺材。燥热凄凉的夜晚,一盏盏忽明忽暗的桐油灯,在街头巷尾闪忽着凄楚的亮光,祭奠亡灵,映照它们不归的远路。再后来,棺材没了,门板没了,桐油灯没了,弯腰驼背的战争幸存者,用竹筐独轮车卡车,把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