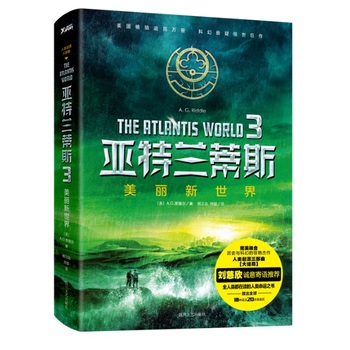世界三部曲1:世界在爱情中成长-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等待最高军事当局召见的百无聊赖的日子,怎样在老鼠飞窜的肮脏旅馆,第一次获得了关于女人的经验。他叙述得很平静,不自责,也不炫耀。他说,多年之后,他结了婚,有了两个聪明活泼的女儿,才知道他在那间老鼠打着洞的肮脏旅馆里做了什么。差一点悔恨得掉下泪来。当他看到二十出头已显苍老的阔脸中国女人和他睡觉之后,穿上裤子,拿着他给她聊做嫖资的一支高级派克金笔,摇晃着薄薄的腰肢,下到街对面当铺去换了零钞,急忙从小摊上换了一把油条抓在手中,站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狂吞不止的时候,他说,写着写着就流泪了。
“唉!那种时候和那样饥饿的人在一起做爱,会获得多少快乐?”梓茕想,“人的生命不同于动物生命,就在于他会反省自己并富有良知。哪怕已经失足,失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失足的麻木。甚至把失足作为一种辉煌来炫耀。而良知,总是反省自己的心灵驱动器和精神发动机。”
战争,会使人的生命变得如蝉翼般单薄而又空灵,似乎轻轻一挑,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不依然是一个外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的故事?是那位男人鼻子不高,眼睛不蓝,还是中国女人没被他描写得朦胧绰约,花枝招展?都不是。不无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那个出卖肉体以抵御饥饿的女人进行任何描绘。这样很好,像一朵云,随风而逝。那位男人,我们不仅知道他的名字,还很响亮。只要翻出美国历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就能找到他。梓茕也不想写出他的真实名字。在生命长河中,名字不过是一种符号。和包容万千气象神秘莫测生命之海比较起来,它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但是,那个有名的美国男人和无名的中国女人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就那么值得炫耀那么美?人,赤裸裸的生命,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包装着的赤裸裸的生命,像两朵陌生的云,两道交叉的路,两弯山涧的水,两株蓬勃的树,靠近接近碰撞相交相溶的时候,是怎样迸发出绚丽的色彩与浪花?给对方带来永不磨灭的记忆刻骨铭心的伤害,乃至因一次出卖性的肌肤接触,便宣判对方精神的死亡,这一切,是可以轻描淡写的么?
男女之间的生命行为,不正需要从对方身上,获得友善与自尊?人类,哪有什么能够做得出又说不清楚的事情!
站起来的民族和站起来的人,并不只看我们的两只脚,是不是踩在大地上行走。
写到这里,梓茕握着笔,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草坪黄昏
那天,保育院教师秦二娥被干练姑娘虞苜公主从头戴英雄结的彝族黑脸男子阿嘎手中抢夺回来,一场虚惊。当晚,她们再次在神秘
别墅的二楼,浴室里浸泡。像鸟儿关在精致的笼里养着,一个星期后,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在一个丹桂飘香的夜晚,献给了公主的父亲。之后,可能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那位权贵人家,给了二娥多少钱,什么车,多少房。而她,岫儿……素子……或秦二娥,可能会为自己失去贞操痛苦不已,或茶饭不思、自寻短见,等等。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二娥依稀记得,那只洁白的裸天鹅,在温柔的锦缎云彩中蠕蠕而动,火车在茫然深邃的隧道中沉闷穿行,风暴折断雏燕的翅膀,风雨中找不到栖息的花枝。秋夜绵绵。除了隐隐的有时又是钻心的疼痛外,她没有其他感觉。不知睡了多久,阳光透过窗帘射进屋子,窗外林子里传来湿漉漉的鸟鸣。懵懵懂懂起床,身边的公主已不知去向。
“真能睡,知道吗?已经是第三天早上了。”
虞苜公主陪二娥吃了西式早餐。公主有说有笑。给她介绍黄油面包,鸡蛋牛奶。二娥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轻轻喝了牛奶,觉得身子很沉,又好像在飘。粉脸泛着淡红,眼里汪着湿润的光泽。吃完早餐,公主把她送上早已停靠在别墅门前的美式吉普车,细细的手指点着她的额角,轻而有力地说,“记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说着,挑了眉头,柳眉微微竖起,露出隐藏在眉宇间的凶狠。说完,召来使女,送给二娥一口精致的小铁箱。公主告诉她,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打开。她不知点头,还是摇头,木然接过小铁箱,钻进了吉普。车里,坐着慵懒的美国大兵杰姆。见了二娥,杰姆脸上的倦容,立即消失。
“哈罗!Hello!”
杰姆向站在车窗外的干练姑娘虞苜公主挥挥手。公主笑着,目送吉普远去。吉普穿过花坛,绕过翠竹,驶出山峦起伏的森林,奔驰在流水潺潺缀满野花的河岸。二娥望了一眼络腮胡美国大兵,迅速低下头。他们脸上,都挂着深深疲惫和微微潮红。他俩也许都知道,同时做了神秘山头上,金碧辉煌的小楼里父女俩的玩物。迷幻离奇的是,这俩玩物又同坐一辆车,在驶向远方……雾蒙蒙的城市。他们是浓重的战争烟云里,飘然而出的生命与爱情的世纪绝唱。
……
“交个朋友吧。”
回到保育院撑着大芭蕉叶的院子,杰姆用生硬的汉语对低头不语的二娥说,两眼热切地望着她。
二娥没有抬头。也没有正眼看大兵。身体从柔软的车座里倦倦抽出,提了小铁箱,下了车。她觉得头重脚轻,像踏上了彩云。
一进屋子,二娥便栽倒在地,一头撞在摔落在地的小铁箱上,额角血流不止,面色苍白,昏迷不醒。院长嬷嬷慌忙叫住美国大兵,用车把二娥送到附近的野战医院。美国大兵救中国姑娘……战时保育院教师,又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新闻一出,便深深笼罩着神秘色彩。随后,二娥被医院安顿在与世隔绝地下室治疗。说姑娘自杀者有之,说姑娘遭谋杀者有之。但二娥姑娘毕竟没有死,院长嬷嬷异常热情的目光,美国大兵深深痛惜的目光,化装成医生护士的便衣特务冷漠的目光,使她掉进冰窖……
一个星期后,二娥出院了。一检查,她根本就没有病。那算什么病呢?少女变成了女人,而且是那种方式变成的女人,算什么病呢?肉体和精神摧残,究竟有多深,也许她自己都不完全明白。美国大兵把她接回保育院,还是那辆吉普车。
“我们都是他们的玩物。”杰姆侧过头,高高的鼻子几乎触到了二娥的脸。
“他们玩腻了的时候,我们将什么也不是。”
杰姆的眼睛,明亮而幽蓝。
“但并不等于我们必须死。”
这个高高大大的美国男人,也许,不仅要挽救她的生命,还想拯救她的心灵和爱情。
“你还应该生活,好好活着,唱歌跳舞,甚至读书,哦,来中国的时候,我正在读书,高中……二年级……我喜欢物理,喜欢化学……你知道什么是物理化学吗?”
二娥木然。杰姆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支粗重的金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从此以后,二娥完全变了一个人,整日沉默不语。不再唱歌,不再跳舞,真正成了一位沉默的保育院的保姆。机械地在厨房扫地担水,做杂务,给孩子喂饭,穿衣,洗屎倒尿……干练姑娘虞苜公主再没来找她看她,院长嬷嬷异样的看着她,美国大兵始终都在注意她,但她却觉得这一切都不存在,她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大兵想了一个办法,他要把二娥拉回现实的世界里来。
许多天后的一个黄昏,二娥端了一筐洗好的衣物从保育院下面的河沟里回来,美国大兵拦住了她,把她拉上美式吉普,飞快向郊外驶去。他们的车,停在一片高大的松柏树林里。夜色迷蒙。杰姆在驾驶室里紧紧拥抱着她。
“你需要爱。”杰姆说,“你过去的不是爱,爱,只有我才能给你。”
杰姆捧起二娥的头,想吻她的嘴。
二娥木然。一动不动。
“我很久就没有和那女人在一起了。”杰姆说,“她是烂货,婊子。我要远远的逃离她。他们一家子都喜欢玩弄人作乐。……爱你,我要娶你,我,明天,不,马上,我想和你一起逃回我的家乡去,我们一块儿,上我家教堂旁边的学校里继续念书,一块念书。”
二娥木然。杰姆像啃
苹果一样,吻她的脸,吻她的嘴……二娥闭上眼睛。她不敢看杰姆那闪着幽蓝的眼睛,像牛一样冒着粗气的椭圆形的鼻孔和翼动着的高高的鼻梁。
他想挽救她。
挽救她最好的方法就是强暴她。
……杰姆疯了似的把二娥抱下车。傍晚的树林,鸟儿鸣叫,斜阳余辉,五彩斑斓。他紧搂着她松软的身子,在草坪上旋转着,嗷嗷叫着,左奔右突,像有使不完的劲。晚霞映照着他们的身影,简直就是一幅浪漫而绝美的爱情生命画图。旋转了一会儿,他轻轻把二娥放在碧绿的草地上。端详她的头,她的脸,她的腰身,然后,伸出毛茸茸的大手,慢慢解她胸前的纽扣……木然的姑娘秦二娥突然坐起来,从腰间掏出一支小巧的勃朗宁手枪……
美国大兵一怔,毛茸茸的手从二娥热热的胸脯上慢慢退出来。随即,淡淡笑了:
“你也有这玩意儿,谁给你的?”
杰姆像摘一朵熟透了的棉花一样,轻轻摘下了二娥手里的枪。
监视
二娥似乎淡忘了那天晚上的那一幕。她也不愿意去回忆它,像被人用来擦过一次的火柴盒,或者用来盛过一次水的茶缸。火柴依旧,茶缸依旧。这就是她的生活。战争逃亡,孤儿院,亲人的失去,周围少得可怜的熟人生命的消失……逃亡武汉。拥挤不堪的马路。市郊。炸弹呼啸,血肉横飞。二娥从泥浆和血浆里被人拖出来,小小的耳鼓灌满了恐怖的呐喊,飞机撕裂人心的怪叫。
她成了一头受伤的小鹿,经历生死磨难的雏燕。她没有想过体验过心灵深处蔓延滋长的情感和欲望,所以那晚
别墅小楼所发生的一切,对她并不算什么。她依然那么美丽。这种美丽,是战争氛围笼罩下残酷的生命赐予。她在保育院里漠然地做她要做的一切。她没有想过,还要不要去找那位时而脸像桃花灿烂,时而竖眉像利剑一样凶狠的虞苜公主。
公主称她:“朋友。”
她不笑。
公主叫她:“妹妹。”
她淡然。
公主叫她:“不许开那口铁箱子。”
二娥果然没有打开。她把铁箱子随手丢放在简易的床头柜上。就连好几次,几个陌生的便衣在保育院门外徘徊,院子里走动,离教室不远的青翠的黄桷树下抡起手枪,观察她,监视她,她也不知道。
她不是她了。
走私
实业部钱次长的六公子,“面首”一样伺候公主和她的母亲。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床上如水一样温文尔雅的英俊小男人,离开她们,上了边境战场,立即变成了一头敛财的猛虎。尤其是他在前线搞军火走私的时候,更是如此。
……
干爹的副官笑面佛萧狐呼和舞女芍药的认识,简直充满戏剧性,好像上苍故意安排。红透全球的舞女芍药,从香港逃难回来的路上遭了劫匪,几十箱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为了讨好芍药,萧狐呼主动请求为她追回财宝。财宝追回一部分,他也把别人的老婆芍药搞到了手。其实,他们进行的只是一笔更加肮脏的肉体交易。萧狐呼把舞女的丈夫,送到另一座更遥远的城市里去,当上了稽查大队长。战争时期,那个职位是肥缺,既能敛财,又能搞女人。萧狐呼把身边的贴身使女,当然也是军人,送了一个给舞女的丈夫。权利金钱伴随肉欲,在他们生活圈内,重组交换,使人根本不觉得人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