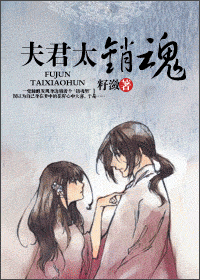匆匆,太匆匆-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颗小脑袋从脖子上摇得快掉下来了。她说:“不 行!不行!我生平最怕照相!何况照了给你拿回家去,我才不干呢!我又不是你的什么 人………”
他用手一把蒙住她的嘴。
“最怕听你来这一套!”他说。“跟我照相很恐怖吗?我又不是猩猩!”“我宁可跟猩 猩照相,不跟你照!”
“哦?”他傻傻的瞪大眼“因为猩猩不会拿着我的照片去给它的父母看!”
“好,我答应你,我也不拿给我父母看,只要你跟我去照张相!”“不要,我好丑!” “胡说,你是世界上最美的!”
“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事情僵持不下,最后,他提议,以 掷铜板来决定。她勉强同意了。拿了个壹圆的辅币,她猜是梅花面,他猜是“壹圆”面。铜 板丢上去,落下来。哈,居然是“壹圆”的那面,他乐坏了,拖着她就往照相馆走。她无可 奈何,也就半推半就的照了那么张“合照”。照片洗出来,他一脸傻傻的笑,她也一脸傻傻 的笑。他还得意呢!居然夸口的说:“你看过什么叫金童玉女吗?这就是金童玉女!”
真不害羞啊,她抢着想去撕那张照片,他当宝贝似的抱着照片跑。拿他没办法啊,她认 了。只是,好久以后,她还会想起这件事来,狐疑的问他一句:“那个铜板是不是变魔术的道具铜板?会不会两面都刻着‘壹圆’?”他大笑。“可能 吧!”他说。“真的?真的?”她追着问:“我看你这人有点不老实,我八成上了你的 当!”唉!鸵鸵,我会让你上当吗?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去合照更多的照片,那时,你将披 上白纱,当我的新娘。他瞅着她,心里的话,嘴里并没有说出来。只为了,认识了这么久, 已相遇,既相知,复相爱,又相怜……而那“婚姻”两字,仍然是两人间的绊脚石。他可以 了解她好多好多方面,独独不了解她对“婚姻”的抗拒感。正像她说的,如果他逼得太紧, 她会逃开。正像徐业平说的,未来是虚无缥缈,漫漫长长的路。哦,鸵鸵,他心里低呼,难 道我还不够爱你,不够资格伴你走过以后的漫漫长路?难道你还不能信赖你自己,信赖你自 己的选择!还是……你认为在你以后的生涯中,会遇到比我更强更好的人?不不!这最后一 个问题要从心底画掉,彻彻底底画掉!他画掉了,只是,心底的底版上,仍然留下一条画过 的刻痕,虽然淡档的,却也带来隐隐的伤痛。
那年暑假,他回家去只住了二十天,就匆匆北返了。实在太想她了,太想太想了。生平 第一次,尝到相思滋味,原来如此苦涩、无奈,躲不掉,也抛不开。他录过一张不知那儿看 到的小笺给她:“鸵鸵:我不想想你,但心思一动,我就想起了你。我不想梦见你,但眼睛 一闭,我就梦见了你。我不想谈论你,但嘴一张,我就又说起了你。——青”
和他的信比起来,她的来信却潇洒得太多太多了。那时,她正参加暑期在万里的夏令 营,来信潇洒得近乎活泼,潇洒得俏皮,也潇洒得连一丁点儿“脂粉味”都没有:“青:当你接到这封信时,该是一早起来时,那时你正穿着一双拖鞋,(瞧,左右脚都穿错了!人家才刚起来嘛!)
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走向前厅,打算好好看个够‘中国时报’上的武侠小说。心中正在想着想着,没想到邮差先生唰的一声,一招漂亮的‘飞云贯日’迎头劈了下来,正待伸手接下这一招,已是不及。一时只见一白色的银镖迎头砸了下来,三字经正待出口,摸摸那练过铁头功的脑袋安然无恙,也就作罢。低头一看,不是什么,原来正是万里镖局的掌门人袁长风派遣的绿衣使者,送来的镖书……好了,姑娘的幻想曲就此打住,要不然,我也可以写一本‘残月·蜻蜓·刀’之类的小说了。
此祝安好鸵鸵七、廿六于万里海滨“
多么可爱的一封信!多么活泼的一封信!多么生动的一封信。但是,信中就少了那么一 点点东西,一点点可以让他感觉出她的思念的东西。没有。就缺那样。他把信左看一次,右 看一次,就少那么点东西。万里海滨!那儿有许多大专学生,正在做夏季活动。想必,他的 鸵鸵是最活跃的,想必,他的鸵鸵是最受欢拥的!他注视着桌上已放大的那张合照,鸵鸵巧 笑嫣然,明眸皓齿,神采飞扬而婉约动人。他有什么把握说鸵鸵不会改变?他有什么把握说 鸵鸵不会被成群的追求者动摇?屏东的家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母亲苍老的脸,父亲关怀的注 视,弟妹们的笑语呢喃……全抵不住台北的一个名字。鸵鸵,我好想你,纵使我本就在想 你。鸵鸵,我好爱你,纵使我已如此的爱你。回到台北,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鸵鸵。
不在家,出去了。看看手表,晚上八点钟。万里的夏令营也已结束。出去了?去哪儿? 第二个电话打给方克梅。
“哦?你回来了?”方克梅的语气好惊讶。“这样吧,我正要去徐业平家,你也来吧, 见面再谈!”
有什么不对了?他的心忽然就沉进了海底。好深好深的海底,老半天都浮不起来。然 后,没有耽误一分钟,他直奔徐业平家,他们家住在台北的中兴大学后面,是公教人员的眷 属宿舍里。一走进徐家,就听到徐业伟在发疯般的敲着他的手鼓。这人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 活力。徐家父母都出去了,怪不得方克梅会来徐家,不止方克梅来了,小丁香也在。徐业平 搂着方克梅,正在大唱着:
“我的心上人,请你不要走,听那鼓声好节奏……”
“咚哌哌!砰排排排排!”徐业伟的鼓声立刻伴奏。
韩青的心脏也在那儿“咚哌哌,砰排排”的乱敲着,敲得可没有徐业伟的鼓声好,敲得 一点节奏感都没有。他进去拉住了徐业平,还没说话,徐业平就笑嘻嘻的递给他一瓶冰啤 酒,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喝啊!”
“喝啊!”徐业伟也喊,敲着鼓。咚哌哌哌哌!
“袁嘉珮呢?”他握着瓶子,劈头就问。瞪视着徐业平。
“你没有把她交给我保管呀!”徐业平仍然笑着。“即使交给我保管,我也管不着!”
“徐业平!”他正色喊。
“小方,你跟他说去!”徐业平推着方克梅。“跟这个认死扣的傻瓜说去!”“到底怎 么回事?”他大声问,徐业伟的鼓声把他的头都快敲昏了。“韩青,你别急。”方克梅走了 过来,温柔的望着他。“只是老故事而已。”“什么老故事?”他的额上冒着汗,太热了。 他觉得背脊上的衬衫都湿透了。“一个男孩子。”方克梅细声说:“他们在万里认得的,不 过才认识十几天而已。袁嘉珮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娃娃。因为那男孩很爱笑,很爱闹,一 张娃娃脸。袁嘉珮欣赏他的洒脱,说他乱幽默的。你知道袁嘉珮,只要谁有那么一丁点跟她 类似的地方,她就会一下子迷糊起来,把对方欣赏得半死!她就是这样的!”他握着瓶啤 酒,顿时双腿都软了,踉跄着冲出那间燠热无比的小屋,他跌坐在屋前的台阶上。一个人坐 在那儿,动也不动。半晌,他觉得有只温柔的小手搭在他肩上,他回头看,是丁香。她送上 来一支点燃了的烟,一直把烟塞进他嘴里,她低头看着他说:“徐业伟要我告诉你,你一定 会赢!”
他瞪着丁香,一时间,不太懂得她的意思。
“看过夺标没有?”丁香笑着,甜甜的,柔柔的,细腻而女性的、早熟的女孩。“徐业 伟说,人家起跑已经比你慢了一步了,除非你放弃,要不然,跑下去呀!还没到终点线呢!”
他凝视丁香,再回头望向屋内,徐业伟咧着张大嘴对他笑,疯狂的拍着他的手鼓;砰 砰,砰排排!
匆匆,太匆匆 10
“鸵鸵,让我告诉你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韩青说,静静的坐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 “看海”原是鸵鸵在情绪不稳定时的习惯,不知何时,这习惯也传染给韩青了。两个人如果 太接近,不止习惯会变得相同,有时连相貌都会变得有几分相似的。鸵鸵坐在他身边,被动 的把下巴放在膝上。她不说话,也不动,只是凝视着那遥远的、无边无际的海。夏天的海好 蓝好蓝,天也好蓝好蓝,那一望无际的蓝,似乎伸到了无穷尽的宇宙的边缘。平时,她爱闹 爱笑爱哭,在海边,她总是最“情绪化”的时候。而今天,她很安静,从他的匆匆北返,从 他约她出来“看海”,她知道,什么事都瞒不住他,而她,也并不想隐瞒任何事。方克梅说 过一句话,你可以交无数的男朋友,但是你只能嫁一个。她不想告诉韩青,她才只有二十 岁,她还不想安定下来,她也不敢相信自己会安定下来。
“鸵鸵,”他继续说,眼光根本不看她,只是看着海,他的声音低沉而清晰的吐出来。 “我很少跟你谈我的家庭,我的过去,只因为你不太想听,你总说,你要的是现在的我,不 是过去的我。但是,鸵鸵,每一个现在的我都是由过去堆积起来的,不但我是,你也是的。”
她用手指绕着一绺头发,绕了又松开,松开又绕起来,她只是反复的做这动作。“让我 讲我小时的故事给你听吧。我小时候家里好穷好穷,现在我们家虽然开了个小商店,那时候 我们连商店都没有。我父亲去给人家采槟榔,你不知道采槟榔是多么苦,多么没前途的工 作。我父亲并不是个天生采槟榔的人,他也有野心,也有抱负。但是,他的命运一直不好, 做什么都不成功。他的人是很好的,对子女,对家庭,他也肯负责任,但,当他情绪不好的 时候,他会拚命喝酒,然后在烂醉中狂歌当哭。”那年,我生病了,大概只有四、五岁吧, 我病得非常重,几乎快死了。全家疯狂的筹了钱给我看医生,给我治病,我爸爸负债累累, 只为了想救我这条小命。那么多年以前,医生开出来的药,居然要九块钱一粒,我一天要吃 十几粒,你可以想像每天要花多少钱了。那些药像珍珠一样名贵的捧到我面前来,而我实在 太小了,我吃药吃怕了,于是,有一天,我把药全吐出来,吐到阴沟里去了。
“你不知道,那时我父亲快要气疯了,他喝掉了两瓶米酒,把自己灌醉了,然后他把我 从床上拎起来,摔在地下,用那穿了厚木屐的脚踢我,他不断的踢我,哭骂着说,如果把全 家拖垮了大家死,不如踢死我算了。当时,他那么疯狂,我瘦瘦小小的母亲根本阻止不了 他,全家吓得都哭了,而我,也几乎快被他踢死了。”就在这时候,住在我们家对面的一个 老婆婆赶来了,她拚了命把我从父亲的拳打脚踢下救了出来,把我抱到她家里去了。说也奇 怪,大概因为我出了一身汗,大概因为哭喊使我有了发泄,我的病居然就这样好了。从此, 这个老婆婆就常对我说,我的命是她救下来的。
“那个老婆婆,她一生没念过书,只是个乡下普普通通的老人。后来,她那儿却成为我 生命中的避风港。每当我病了,每当我受到挫折,每当我意志消沉的时候,父母不能了解 我,老婆婆却能够。有一次,我考坏了,被当掉一年,这对我是很重的打击,那年我已经十 五、六岁了,我很伤心,很痛苦,我到老婆婆那儿去。”老婆婆已经好老好老了,我不怕在 她面前掉眼泪。她却笑着对我说:阿青,你看看麻雀是怎么飞的?我真的跑出去看麻雀,我 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