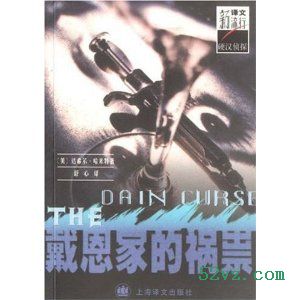德伯家的苔丝-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我承认,”伊茨小声说,“今天他抱着我走过水塘的时候,我心里想他一定要吻我的;我静静地靠在他的胸膛上,等了又等,一动也不动。但是他没有吻我。我再也不愿意在泰波塞斯住下去了!我要回家去。”
姑娘们的爱情既然没有了希望,卧室里的气氛也就变得烦躁不安起来。冷酷的自然法则把她们的感情激发出来——这种感情既不是她们想要的,也不是她们情愿的,就是在这种感情的压力下,她们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白天发生的事已经燃起了火苗,在她们的胸膛里燃烧着,折磨着她们,使她们痛苦得几乎无法忍受了。她们作为个体存在的差别被这种感情消除了,她们每一个人都不过是被称作女人的这种有机体的一部分。因为谁也没有希望,所以她们都是那样坦诚,没有一点儿忌妒。她们每一个人都是明白事理的姑娘,谁也没有想到为了超过别人,就用虚荣的幻想去自欺欺人,或是去否认她们的爱情,或去卖弄风情。从她们的身分地位看,她们完全明白她们的痴情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意义的;是她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在作怪;从文明的观点看,她们的爱情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但是从自然的观点看,什么理由也不缺少);事实是,爱情是确实存在的,而且给她们带来的极度喜悦到了销魂蚀魄的程度;所有这一切也使她们产生出一种听天由命和自尊自重的思想,而她们要是真的去争夺他作丈夫,卑鄙地想心思,那么这种态度就会被破坏掉了。
她们在小床上翻来覆去的,老是睡不着,楼下的奶油榨机里也传来单调的滴答声。
“你没睡着吧,苔丝?”过了半小时,有一个女孩子低声问。
那是伊茨·体特的声音。
苔丝回答说没有睡着,刚一说完,莱蒂和玛丽安也掀开了被单叹着气说——
“我们也没有睡着呢!”
“据说他家里给他找了一位小姐——我实在想知道她长的是个什么样子!”
“我也很想知道,”伊茨说。
“给他找了一个小姐?”苔丝吃了一惊,急忙问。
“啊,不错——听人悄悄说的;是一个门户和他相当的小姐,他家里给他找的;是一个神学博士的女儿,离他父亲住的爱敏寺教区不远;他们说他不太喜欢她。不过他肯定是要娶她的。”
关于这件事,她们知道的就是这样一点点;但是在夜色深沉的晚上,这件事已经足以使她们建立起痛苦和悲哀的遐想。他们想象出所有的细节,想象他怎样被劝说得同意了,想象怎样准备婚礼,想象新娘的快乐,想象新娘的服装和婚纱,想象新娘和他住在一起的幸福之家,而他同她们之间的旧情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她们就这样谈着,痛苦着,直到她们哭着睡着了,才算把忧愁驱散掉。
在这段新闻透露出来以后,苔丝也就断了痴心妄想的念头,不再以为克莱尔对她的殷勤含有什么严肃郑重的意义了。那只是因为她的美丽而爱她的,就像上在过去的夏季一样,也就是说,他是为了暂时的爱情欢娱而爱她的,此外没有别的。在这种悲伤的想法里,她还戴有一顶荆棘之冠,那就是他对她的暂时爱恋胜于其他的人,而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在天性方面比她们更热情、更聪明、更美貌,但是从社会礼法的观点看,她却不比被他忽视的不如她美貌的那些人更值得他爱。
……………………
第二十四章
……………………
在佛卢姆谷里,土壤肥沃得冒油,气候温暖得发酵,在这种季节里,从万物滋生发育的咝咝声中,几乎连草木汁液的奔流都听得见,因此,那种最富有幻想的爱情就不可能不生出缠绵的情意来。生活在那儿的胸怀激情的两个人,也都受到了周围环境的感染。
七月已经从他们的身边过去了,随后而来的便是暑月①的气候,似乎自然这一方面也在作出努力,以便能够适合在泰波塞斯奶牛场谈情说爱的心境。这个地方的空气,在春天和初夏都非常清新,而现在却变得呆滞和使人困倦了。沉重的气息压在他们的身上,到了正午,似乎连景物也昏昏入睡了。像埃塞俄比亚的烈日一样灼热的太阳,晒黄了牧场斜坡顶上的青草,不过在流水潺潺的地方依然还是嫩绿的草地。克莱尔不仅外面受到热气的灼烤,而且内心里也为了温柔沉静的苔丝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激情的压迫。
①暑月(Thermindnrean),1789年法国大革命改变历法,其中从7月19日至8月17日的一个月被称为暑月。Thermindorean来自希腊文,热的意思,暑月也有被译为雾月和热月的。
雨已经下过了,高地也干了。奶牛场老板坐着带弹簧的双轮马车从市场回家,马车跑得飞快,车轮的后面带起一股白色的尘土,好像是点燃了的一条细长的火药引线一样。奶牛被牛虻咬得发了疯,有五道横木的栅栏门都被它们跳了过去;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奶牛场的克里克老板卷起来的衬衣袖子,从来就没有放下来过。只开窗户而不把门打开,风是透不进来的;在奶牛场的园子里,乌鸦和画盾在覆盆子树丛下跳来跳去,看它们的样子,与其说它们是长翅膀的飞鸟,还不如说它们是长四条腿的走兽。厨房里的蚊蝇懒洋洋的,一点儿也不伯人,在没有人的地方爬来爬去,比如地板上、柜子上以及挤奶女工的手背上。他们在一块儿谈话的内容总是与中暑有关;而做黄油,尤其是保存黄油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了。
为了凉爽和方便,挤牛奶的工人们不把奶牛赶回家去,完全在草地上挤奶。白天,随着地球的转动,太阳也绕着树干移动,因此哪怕是最小的一棵树木,奶牛也要跟随着它的阴影转动;挤奶工人过来挤奶时,由于蚊蝇的叮咬,奶牛几乎都无法安静地站着。
这些天以来,有一天下午,有四五条还没有挤奶的奶牛碰巧离开了牛群,站在一个树篱的拐角后面,这几条牛中有矮胖子和老美人,同其他的女工比起来,它们最喜欢由苔丝来挤奶。苔丝挤完了一头奶牛的奶,从凳子上站起来,这时候已经把她注意了一会儿的安琪尔·克莱尔问她,愿不愿意去挤前面提到的两头奶牛。苔丝默不作声地同意了,把凳子拿在手里,提起牛奶桶,向那两头奶牛站的地方走过去。不久,从树篱那边传来了老美人的奶被挤进桶里的咝咝声,安琪尔·克莱尔这时候也想到拐角那儿去,以便把跑到那边的一头难挤的奶牛的奶挤完,因为他现在已能像奶牛场老板一样挤难挤的奶牛了。
所有挤奶的男工,还有一些女工,他们在挤奶的时候都把额头抵在牛的身上,眼睛盯着牛奶桶。但是也有几个人,主要是年轻的女工,都侧着头靠在牛的肚子上。苔丝·德北菲尔德就是这种挤奶的习惯,她把太阳穴靠在奶牛的肚子上,眼睛凝视着草场的远方,悄悄地聚精会神地想着心思。她就是用这样的姿势为老美人挤奶的,太阳刚好照在挤奶的这一边,太阳的光线一直射到她穿粉红裙子的身上,射到她戴的有帽檐的白色帽子上,照亮了她的侧面身影,使她看上去就像是从奶牛的黄褐色背景上雕刻出来的一尊玉石浮雕像。
她不知道克莱尔随后也来到了她的附近,也不知道他正坐在奶牛下面观察她。很明显,她的头和她的面目安详沉静:她似乎在那儿发怔出神,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却看不见。在这幅图画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老美人的尾巴和苔丝粉红色的双手在活动着,那双手的活动是那样地轻柔,所以就变成了一种韵律的搏动,它们也仿佛正在按照反射的刺激活动,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一样。
在他看来,她的脸非常可爱。但是,那张脸上又没有超凡入圣的神情,全部都是真正的青春活力,真正的温暖,真正的血肉之躯。而这一切又全都集中到了她的嘴上。她的一双眼睛和他过去看见的一样,一直是那样深沉,似乎能够说话,她的面颊,也许还是像他从前见过的那样美丽;她的眉毛还是像从前见过的那样弯弯如弓,她的下巴还是像从前见过的那样棱角分明,她的脖颈也还是像从前见过的那样端正;然而她的那张嘴从前却没有见到过,不知道天底下有没有能同它相比的。她的中部微微向上掀起的红色上唇,就连最没有激情的青年男子见了,也要神魂颠倒,痴迷如醉,为之疯狂。他从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的嘴唇和牙齿如此美妙,让他在心中不断地想起玫瑰含雪①这个古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比喻。在他用一个情人的眼光看来,她的嘴和牙齿简直是完美无缺了。但又个是完美无缺——它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正是在似乎完美无缺中显露出来的一点儿不完美,这才生出甜蜜来,正因为有了这一点不完美,也才符合人之常情。
①玫瑰含雪(roses filled with snow),出自托玛斯·坎皮恩的诗《樱桃熟了》:“看上去它们就像含雪的玫瑰蓓蕾。”
克莱尔已经把她的两片嘴唇的曲线研究过许多次了,因此他在心里很容易就能够把它们再现出来;此刻它们就出现在他的面前,红红的嘴唇充满了生气,它们送过来一阵清风,吹过他的身体,这阵清风吹进了他的神经,几乎使他颤栗起来;实在的情形是,由于某种神秘的生理过程,这阵清风让他打了一个毫无诗意的喷嚏。
接着苔丝意识到他正在看她;不过她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坐着的姿势一点儿也没有动,但是她那种梦幻一样的沉思却消失了,只要仔细一看,很容易就能发现她脸上的玫瑰红色正在加深,后来又慢慢消褪了,上面只剩下一点淡淡的红色。
克莱尔心中出现的那种好像从天而降的激动情绪,还没有消失。决心、沉默、谨慎、恐惧,好像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往后直退。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把牛奶桶扔在那儿,也不管会不会被奶牛踢翻,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他一心渴望的人跟前,跪在她的旁边,把她拥抱在自己怀里。
苔丝冷不防地被吓了一跳,但是她想也没想,就不由自主地让他拥抱着自己。她看清了来到她面前的不是别人,确实是她所爱的人,就张开嘴发出一种近似狂喜的呼喊,带着暂时的欢愉倒在他的怀里。
他正要去吻那张迷人的小嘴,但是由于他温柔的良知而克制住了自己。
“原谅我,亲爱的苔丝!”他小声说。“我应该先问问你的。我——我真不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不是有意冒犯你的。我是真心爱你的,最亲爱的苔丝,我完全是一片真心啊!”
这时候老美人回过头来看着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它看见在它的肚子下面蜷伏着两个人,从它记事以来,那儿应该只有一个人的,于是发了脾气,抬了抬后腿。
“她生气了——她不懂我们在干什么——她会把牛奶桶踢翻的!”苔丝嘴里嚷着,一边轻轻地从克莱尔怀里挣脱出来,她的眼睛注意的是牛的动作,她的心里想的却是克莱尔和她自己。
她从凳子上站起来,两人站在一起,克莱尔的胳膊仍然搂着她。苔丝的眼睛注视着远方,眼泪开始流了出来。
“你为什么哭了,亲爱的?”他问。
“啊——我不知道呀!”她嘟哝着说。
等到她把自己的地位看清楚了,弄明白了,她就开始变得焦虑不安了,想从克莱尔的搂抱中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