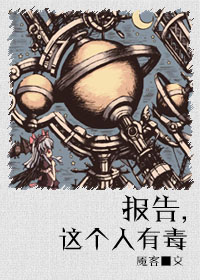个人的体验-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是如此啊,鸟。”
“这么说来,也曾有过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好好地活到现在这样最坏的瞬间吧。”鸟被很遥远的呼唤所吸引,仿佛现在这时刻就要入睡似的,用含含糊糊的声音确认道。是这样吧。在那危险时刻,另一个我,就那样变成死尸留在后边了吗?在与现在置身之地不同的各种宇宙里,我曾是个孱弱的小学生,又曾是个头脑简单但身体比现在还健壮的高中生,我应该拥有无数个死去的自己吧?现今宇宙里的我,无疑不够理想,但是,究竟哪一位死者,是最为理想的我的自身呢?“如果我最终无法逃往另一个宇宙,现在这个宇宙里的我的死,成了我的全部宇宙之死,也就是我的最后之死,究竟有呢,还是没有?”
“如果没有最后之死,你就必须在一个宇宙里无限期生存下去啊,那么就算有吧。”火见子说。“那可能是九十岁以后,衰老而死吧。所有的人,在他老死于最后一个宇宙之前,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宇宙之死,然后转到另一个宇宙里生存下去的啊。如果我们把所的人的结局都看作是老死在最后的宇宙里,那不是可以说是很公平的吗?鸟。”
鸟突然感觉到了一个问题,他打断火见子说:“你现在还在为丈夫的自杀而感到愧疚不安,因此,为了不把死看成是绝对无可挽回的东西,你设计了这样一个心理骗术。难道不是这样么?”
“不管怎么说,残留在这个宇宙的我,一直都没法忘记自杀的他,一直承受着痛苦啊。”火见子说。她的眼睛已经开始疲倦,浅黑色的眼圈突然泛起红潮,让人觉得愈发难看。“至少,我没有回避我在这个宇宙里的责任”。火见子又说。”“我并不想责怪你,但事情就是这样呀,火见子。”鸟再一次微笑着说。他尽量减轻自己言辞的刻毒,但同时又表现得很固执。他继续说:“你设想在彼岸宇宙里他仍然活着,从而使在此岸宇宙已死的他这一无法挽回的绝对事实相对化。但是,不管怎样使用心理层面上的修辞手段,也没法动摇一个人的死这一绝对性内容,使之相对化吧?”
“也可能是这样的吧。鸟,能再给我倒杯威士忌吗?”火见子突然对自己的多元宇宙论失去了兴趣,兴味索然地说。
鸟给火见子,也给自己重新斟满威士忌,他希望火见子能烂醉如泥,完全忘掉自己对她的批评,明天酒醒,仍然继续做她的多元宇宙之梦。鸟很像一位乘坐时间飞船寻访万年之前的世界的旅行者,深恐自己的影响会给现实世界招来异变。这是他获得自己的孩子头部异常消息以来,心里不断升腾的情绪。鸟像从连续倒运的扑克牌游戏里走出来一样,渐渐地回到了这个世界里。鸟和火见子都沉默着,不知不觉,双方互相致以宽容的微笑,然后,又像甲虫喝树液一样,非常严肃地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初夏午后遥远的街道上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鸟都置若罔闻。他伸腰打了个哈欠,懵然落下一滴像唾液一样的眼泪,他又啜了一口新倒进杯里的酒。他感到自己在从这边的世界顺利地往下落……
“哎,鸟。”
鸟用手指夹住威士忌酒杯,已经跌入香甜的睡梦中,火见子的喊,让他肩头一哆嗦,威士忌洒到了膝盖上,他很不高兴地睁开了眼睛。他感到自己已经进入酒醉的第二个层次。“啊?”
“你大伯给你的那件鹿皮外套,现在哪去了?”火见子也醉了,又圆又红的脸像个大西红柿,她特别用力地转动舌头,尽量让自己的发音准确。
“是啊,哪儿去了呢,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穿的呢。”“一直穿到二年级的冬天呀,鸟。”
冬天这个词,在鸟那被酒精麻醉的记忆的湖水里,强烈地激起了波纹。
“是呵,我俩睡觉那次,我把那件外套就那样直接铺在地上,是刚刚下过雨的储材场的地上。第二天早上一看,粘满了泥和碎木屑,什么辙也没有,那时候,洗衣房还不肯收鹿皮外套呢。只好就那么扔到壁橱里,什么时候把它扔掉的呢?”鸟说,说起那年隆冬深夜,他像回忆起一件非常遥远的往事。那天夜里忘记是由什么契机引发的,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鸟和火见子都喝得酩酊大醉。鸟送火见子回寄宿的木材店,在那座二层店铺后面储材场的暗影里,鸟抱住了火见子。开初,两人不过是因为感觉冷而相互拥抱着爱抚,不一会,鸟的手像是很偶然地碰到了火见子的性器。于是,鸟兴奋起来,他把火见子按在贴板壁立着的方木上,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性器往里插。火见子也积极配合,但竟不自觉地悄然笑了起来。他们兴奋激昂,但终于未超出游戏的领域。不过,当明白了这样站着是不可能插进去的时候,鸟感到自己被当成了未成熟的孩子,他愈发执拗地不肯退却。他把鹿皮外套铺在地面上,然后把仍然笑嘻嘻的火见子横放到上面。火见子个儿高,头和膝盖以下,都直接挨着地,垫不着鹿皮外套。不一会儿,火见子停止了笑声,鸟以为她快达到了高潮。又过了一会儿,他问火见子,想证实自己的想法,但火见子回答说自己只是感觉冷。于是,鸟中止了性交。
“那时候,我是个野蛮的家伙。”鸟像一个百岁老人回顾往事似的说。
“我也同样野蛮呀。”
“为什么我们没有重来一次呢?那以后,我们就没来过第二次。”
“贮材场那件事儿,让人感觉完全是一次偶发事件,第二天回顾一下,无法想象会重来第二次的。”
“是啊,那确实像是一次不正常的事件,好像是强奸事件。”鸟惶恐羞愧地说。
“那就是强奸事件呀!”火见子订正说。
“可是,你真的一点儿快感也没有吗?离高潮还很远吗?”鸟不无遗憾地问。
“那是不可能的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性交。”
鸟吃惊地盯着火见子。鸟知道火见子不是那种撒谎或信口开玩笑的人。鸟心里一片茫然,随后,他被恐怖感和责怪他的滑稽感强制着,发出短促的笑声。这笑声也感染了火见子。
“人生确实很奇怪,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情啊。”鸟的脸全涨红了,但却不只是因为酒醉。
“不要说这些伤心的话了,鸟。那次性交,如果对我来说意味着第一次,那也只和我自己有关,和你是没关系的。”火见子说。
鸟用水杯代替酒杯,倒上威士忌,一饮而尽。他感到必须准确地回忆一下当时在贮材场发生的事件。确实,那时,他的生殖器遭到了一个硬硬缩紧如尖唇似的东西的反复抵抗和阻挡。他以为那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火见子冻得浑身拘挛的缘故。但第二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衬衫边上有血污。我那时为什么没想想那是什么呢?鸟这样想着,一股躁动的欲望涌了上来,他咬住牙,紧紧握住装酒的水杯,像在忍受着一种痛苦。混合着剧烈痛疼与不安的肿瘤似的东西,在他体内的中心部位生长出来,那是欲望,名副其实的欲望,那是与缠绕在心肌梗塞病患者肋下的疼痛和不安极为相似的欲望;并且,那欲望又与所谓家庭式的欲望全然不同。家庭式的欲望,和辉映在鸟意识天空里的非洲旅行之梦截然相反,不过是疲惫而安稳的日常生活中凸起的一个小疙瘩,是每周和妻子性交几次即可消解的平实的欲望;是伴随着猥亵的叫声、沾满悲哀而疲劳的泥水的欲望。而鸟现在涌起的,却是数千次性交都无法消解的欲望;这欲望,丝毫不像环行电车用过的车票;欲望中最激烈的欲望,严格说不容重复,因此,当它实现的瞬间,让人惶恐地感到,这是极其危险的欲望;在沁满汗珠的裸体背后,死不正在悄然走近吗?或许,这可以认为是鸟完全了解了自己几年前在冬夜贮材场上强奸了一个处女之后,而被注满的欲望。
鸟被威士忌烧得燥热,他用力凝住眼珠,偷看了像鼬鼠一样灵活敏捷的火见子一眼。他的脑袋发胀像鼓起的气球。香烟的烟雾沙丁鱼群似的在房间里游来游去,找不到出口,而火见子就飘浮在雾里,她现在已经醉得昏昏沉沉,脸上浮现着单纯得可疑的微笑,她注视着鸟。但事实上她的眼睛里什么也没看到。一直沉湎于梦想的火见子感到自己浑身发软,变圆,特别是灼热的脸庞,尤其如此。
如果能和火见子重演一次那个冬夜里的强奸剧,那会怎样呢?鸟怀着一种惋惜的心情想。但那已经没有可能。从今往后,即使能有机会与火见子性交,那么,这性交则将和鸟今天早晨换衣服时偶然瞥见的自己瘦弱如雀的生殖器,和他妻子出产之时急剧扩张而后又缓慢收缩的生殖器连系在一起;将和濒死的婴儿连系在一起;还将和被称作人道主义的人的猥杂的悲惨连系在一起。这种人道主义偏离现实世界的所有期待,相互默契共同对此佯作不知,不必说这不是欲望的升华,而是欲望的分解。鸟呷了一口威士忌,微微暖热起来的内脏被自己的一个念头吓得战栗不已。和火见子干,如果那年冬夜的紧张劲儿再上来,最终还是干不成,那该怎么办?那就只能把她勒死吧?屠杀,奸尸!在他心灵深处的欲望之窠里,振翅飞腾起这样的声音。但是鸟清楚,自己现在不可能这样冒险。我知道了火见子在那个夜晚还是处女,现在只有悔恨。鸟很看不起自己内心的混乱念头并努力排拒思绪混乱的自己。然而,那黑红色欲望与不安,却像海胆似的棘刺蓬蓬,不能彻底消溶。不能去屠杀奸尸,那么,设法挑起一个同样紧张并具爆炸性的戏剧吧。然而,对异常而危险的事件,鸟束手无策,茫然无知。他像一个因屡屡失误而被替换下来,返回赛场边侧长凳坐着喝水的篮球运动员,精疲力竭而又焦燥不安,颇带着一些自我嘲弄的心情,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威士忌已经不烈也不香,甚至苦味儿都没有了。“鸟,你喝威士忌,一直是喝得这么快,这么多吗?简直像喝红茶一样,就是红茶,烫的时候也不能这么喝呀。”“是呀,一直是这样的,喝的时候。”鸟颇有些害羞地回答。
“和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喝?”
“为什么不能这么喝?”
“像你这么喝,你没法让女人满足吧。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始终都达不到高潮的。像一个长距离游泳运动员,疲惫劳顿,心脏律动失常,在女人的脑袋旁架起酒精的彩虹!”“你现在想和我睡吗?”
“你醉得一塌糊涂我才不想和你一块睡呢,因为那对我们俩儿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鸟把手指伸到裤兜深处的角落,去摸自己那个热乎柔软的东西;那是一只无聊地睡在那里的一只小老鼠。和鸟心里燃起的欲望正相反,它无精打彩地萎缩着。
“看,不行吧,鸟。”火见子敏锐地打量着鸟的动作,不无夸耀地说。
“就算我达不到高潮,但我可以像孙悟空那样挺拔活跃起来,让你达到高潮呀。”
“没那么简单呀,我的高潮!你好像没有好好记住那年深冬我们在贮材场上的事情,那虽然也没什么,但那是我一个生活阶段开始的仪式。又冷又脏,滑稽而惨痛的仪式呐。打那以后,我苦战苦斗,跑起了长途赛呀。鸟。”
“莫不是我让你得了性感缺乏症?”
“要说一般的高潮,那倒是常能达到啊。那次,我的指甲里还残留着贮材场地面上的泥土的时候,得到一位同年级同学的帮助,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