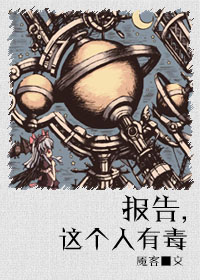个人的体验-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当儿,鸟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从身后由远而近,撒完尿回头看时,自己已经被那些绣龙运动装青年紧紧包围。他们背对剧场那边照来过的微弱的光,黑影幢幢,无法窥见他们是怎样的表情。但在这一瞬间,鸟也想起来,刚才在那店铺里他们所呈现的毫无表情的神态,其中就潜藏着对自己彻底而冷酷的拒绝。一个极其孱弱的存在映入他们的眼帘,唤醒了他们猛兽的本能。遇见软弱可欺的家伙就一定要欺侮。他们浑身躁动着暴力少年的可怕欲望,追赶这只拳击力500、应该袭击的可怜的羊。鸟极为恐怖,惊惶地寻找逃走的路。朝明亮的繁华街跑,必须正面冲破包围圈最稠密的部分,以他刚才测定的体力(四十岁人的握力与拉力!),毫无可能,大概立刻就会被推挡回来。鸟的右边,是被板障遮住的死胡同;左边,铁道路堤和工地高高的铁网围栏中间有一条细细的昏暗小路,和远方的柏油马路相通。如果能冲过一百米左右,不被捉住,那可能就有希望了。
鸟决心已定。他猛然转身,做出向右边死胡同奔的样子,然后一个回转,向左边突进。但敌人都是进行此类袭击的老手,和鸟二十岁时在地方城市夜晚世界里的行径一样,他们已经看穿对手的战略,当鸟身向右转的时候,他们便向左移动,严密封住。鸟转换身形向左突进的那一瞬间,恰恰与那位挺胸运劲儿、用刚才打沙袋的姿势击来的黑脸青年正面相遇。他已经没有转身的余地。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凶狠有力的一击,身子后仰,跳到路坝的草丛里。鸟呻吟着吐出血和唾液。跟刚才打得沙袋计数器全身麻木时一样,青年们发出响亮的笑声,随即再度沉默,包围圈缩成比刚才更小的半圆形,他们俯视着倒在地上的鸟,待机而动。
鸟想,压在自己身体和路坝中间的非洲地图,肯定弄得折皱不堪了。随后,现在自己的孩子将要出生这一念头,第一次切切实实地跃上鸟的意识的最前线。无名的怒火和粗暴的绝望感笼罩着鸟。这之前,鸟惊愕、困惑之余,一心想的是如何逃跑,但现在,鸟不再想逃。如果现在不投入战斗,那么,我去非洲旅行的机会就永远地失去了;不,不只如此,我的孩子可能也将因此而度过苦难的一生。鸟仿佛获得了某种谕示,他对此坚信不疑。雨滴滴在他干裂的嘴唇上。他抬起头,呻吟着慢慢挺起身。青年人围住的半圆形从容退后,引诱他向前。也有一个非常倔强的家伙,充满自信地踏前一步。鸟两臂无力地垂着,颚部前突,做出一副夜市上被随意踢在一边的木偶似的呆样子,立了起来。那个年轻人从容地瞄着目标,像棒球投手的动作似的,一只脚高高提起,上身后仰,手臂后伸,然后开始进袭。鸟低头,探腰,对着年轻人的腹部牛似的冲撞过去。年轻人大叫一声,噢地吐出胃液,随即突然沉默无语,颓然倒下。他已经窒息。鸟立即昂起头,与其他那些年轻人对峙。斗争的喜悦在鸟的身上复苏。这已经是多年不曾有的事情了。鸟和青年们相互对视着不动,双方都清楚碰上了强健的对手。时间流逝。
突然,一个年轻人向同伴们叫:
“住手吧,住手!这家伙不是我们的敌手呀,他是个老叔叔哟!”
青年们的紧张立时全部解除,他们无视仍然保持着原来架势的鸟,颇为沮丧地拥着拉着向剧场方向撤去。鸟孤独地淋在雨中,奇妙而啼笑皆非的滑稽感油然而生;过了一会,鸟竟无声地笑了起来。他的上衣沾染了血污,如果在雨中走走,可能会和雨迹水痕混在一起。鸟感到这是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被击中的颚部不消说了,眼睛四周,手臂,背部,都感到疼痛,但自妻子开始产前阵痛以来,鸟现在的心情最好。他拖着跛腿,沿着路坝和工地之间的小路,向柏油马路走去。一辆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气机车正喷着烟灰,在路坝上行进。机车从鸟的头顶通过时,它简直是一头挂在黑暗夜空上的巨大黑犀。走到柏油路,鸟一边等着出租车,一边把一颗被打断的牙齿从舌与齿茎中间抠了出来,吐到地上。
二
西部非洲地图沾满泥土,鼻息和胃液的污迹,用图钉钉在墙上。墙壁下,鸟像受惊的潮虫一样蜷屈着身子睡着。这里是鸟夫妇的卧室。鸟睡着的床和妻子空荡荡的床中间,放着一张大鸟笼似的白色婴儿床,婴儿床上罩着的塑料包装尚未拆去。鸟仿佛对凌晨的寒气怀着不满,哼哼呻吟着做了一个痛苦的梦。
鸟立于尼日尔之东、乍得海西岸的高原上。他究竟是在那里等待什么机会呢?他突然被弗科赫尔盯上了。这个凶暴的野兽腾越沙丘飞驰而来。这绝非坏事。鸟来非洲,本来就是为了通过冒险、遇难、与新的种族相会,窥视到远在现今安稳、平庸的日常生活彼岸的东西。但鸟没有能与弗科赫尔搏斗的武器。我既无准备,也未受过训练,就这样来到了非洲。鸟极为恐慌地想。而猛兽已经逼近。鸟想起自己少年时代在外地城市裤角插着弹簧刀放浪的往事。不过,那条裤子他早就扔掉了。说来也滑稽可笑,他甚至想不起弗科赫尔用日语该怎么说。他听到那些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在安全地带喊:危险!快逃!弗科赫尔来了!暴怒的弗科赫尔已经逼到对面仅距十米左右的低浅的灌木丛,鸟似乎很难逃脱。这时,他发现,北边有一处被水色斜线围起来的地方,那斜线肯定是铁丝网。往这里边儿跑,跑进来就没事了!那些把他丢下不管的家伙在那里边儿喊着。鸟开始向那儿奔。然而,实在太晚了!弗科赫尔已经逼近他的身后。我毫无准备,也没经过训练,就这样来到非洲的。避开弗科赫尔的攻击看来已经绝无可能,鸟完全绝望了;但恐惧驱使他狂奔不止。水色斜线里,无数“安全的人们”眺望着奔逃的鸟。弗科赫尔锐利的牙齿凶狠地咬进了鸟的脚踝……
电话铃响了起来,鸟突然惊醒。天已黎明,而窗外雨声依旧。鸟纵身跃起,光着脚踏着冰冷潮湿的地板,像兔子一样蹦到电话机旁。鸟拿起话筒,一个男子的声音,没有客套寒喧,确认了他的名字后便说:“请即刻到医院来!婴儿出现异常,有事需要商量!”
鸟突然孤立无援。他感到自己想要退回尼日尔高原,品尝刚才梦境的余味,尽管那梦就像栽在恐怖的荆棘里浑身棘皮的海胆一样。随后,鸟努力抵抗着自己总是沉湎于往事的行为,用意志坚定的语气,像谈论别人的事情一样问:“孩子的妈妈没事吧?”他感到,这样的声音,可能曾千百次和这种背台词式的情境相遇。
“孩子妈妈还好。事情紧急,务请快来!”
鸟像缩回巢穴的螃蟹一样匆忙跑回卧室,眼睛硬硬地阖着,他想钻进温暖的被窝;仿佛用这样的办法拒绝现实,现实的一切就会像梦中的尼日尔高原一样突然消失。随后,鸟摇晃了一下脑袋,清醒了过来,弯腰捡起扔在床旁的衬衫和裤子。弯腰的时候,身上一阵疼痛,使鸟想起昨夜的战斗。他想炫耀一下自己仍然经得住殴斗的体力,但不必说,现在不可能唤起那样的情绪了。鸟一边扣着衫衬扣子,一边抬头望那张西部非洲地图。从地图上看,他在梦里驻足的高原是迪伊法。那里画着奔跑的疣猪。弗科赫尔就是疣猪。疣猪的上方水色斜线部分意味着那里是禁猎区。刚才鸟在梦中即使逃到了那里,也不可能获救。鸟又一次晃了晃脑袋,边扣着上衣边走出卧室,然后蹑手蹑脚地下了楼。如果住在一层的房东老太婆醒了,应该怎样回答她那被善意和好奇的砥石擦磨得非常锋利的发问呢?鸟会告诉她:现在还一无所知,医院方面只通知说婴儿出现异常。但事态可能相当可怕吧?鸟想。鸟在门口摸摸索索找到鞋子,尽可能不出声响地开开门锁,然后便走进黎明的微光里。
鸟的自行车倒在矮树篱笆下的碎石上,被小雨淋得精湿。他椆起自行车,用上衣袖擦了擦固执地停在朽烂了的车座皮上的水滴。但还没有擦净,鸟便一屁股坐上去,像一匹发怒的烈马,蹄下砂土翻腾,从树篱间穿过,奔向柏油马路。屁股的皮肤被濡得冰凉难受。雨仍然在下。风劈面吹来,他满脸雨水淋漓。鸟为了不让车轮掉进路面的坑洼里,他大睁着眼睛,使劲蹬着车子疾奔,雨珠直直地打到眼球上。不一会儿,鸟驶到更为宽阔的柏油路上,拐到左侧。风挟着雨从他的右前方吹来,这样多少可以躲开一点儿。鸟上身右倾,顶着风,平衡着自行车。柏油路面上薄薄地积着的一层水,快速转动的车轮激起细碎的波浪,水珠腾落如雾,鸟斜着身子,低头看着水雾起落,两脚上下猛蹬。这当儿,他感到头晕。鸟仰起头,视线所及,柏油路上空空荡荡,连个人影都没有。列在路两旁的银杏树叶子又浓又厚,茂密的叶片上吸满了水滴,显得笨重而臃肿。黑黑的树干,其实是支撑着一块块深绿色的海。如果这些海一齐冲决,鸟和自行车大概都要淹到味道清香的洪水里。鸟感觉到了这些树木对自己的威胁。高高的树梢上摇曳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鸟透过树梢的夹隙眺望东边的天空,那里灰黑一片,但深底里似乎渗出淡淡的桃红。天空一副卑微而羞涩的神态,乱云却像猛犬一样粗野地奔腾。几只长尾蓝鸟像野猫似的从鸟的眼前大摇大摆地穿过,惊得他慌乱无措;鸟发现,蓝鸟淡青色的尾巴上,聚集着银色虱子似的水滴。鸟觉得自己太容易受惊了,而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感觉又过于敏锐了。他茫然不知所以地想:这是不吉之兆。他沉醉不醒的那段时间里就曾经是这样的。
鸟探身伸腰,头深深伏下,把全部体重都压到自行车脚蹬上,加速前进。梦中那种无路可逃的情绪油然复生。但鸟是在疾速前行。他的肩膀碰断了银杏树细细的树枝,断碴儿像弹条一样弹过来,刮伤了他的耳朵。然而,鸟没有放慢速度。雨滴簌簌,从阵阵作痛的耳边掠过。驶进医院的停车棚,鸟把制动手闸捏得直响,如同自己发出的叫声。他浑身淋得像一只落水狗。鸟抖动身子,甩去身上的水滴,同时陷入一种错觉:他感到自己跑了相当遥远的路。
在诊疗室前,鸟喘了喘气,走进光线暗淡的室内,对着几张在这里等着他的眉目不清的面孔,声音嘶哑地说:“我是孩子的父亲。”鸟内心则颇觉奇怪:为什么不开灯呢?
随后,鸟看到,岳母用衣袖掩着嘴巴坐在那里,像要止住呕吐一样。鸟走到她的身边,在近旁的椅子上坐下。透湿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脊背和屁股的皮肤上。和刚才闯进车棚时的粗野相完全不同,现在,鸟浑身瑟瑟战抖,像一只伶仃孤苦的小鸡雏。
鸟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室内的光线,他看到,三个审问官似的医生绷着脸一言不发,目光审慎地盯着自己。如果说,法庭审问官的头顶都悬挂着象征法律权威的国旗,那么,对于诊疗室里的审问官们来说,身后的彩色人体解剖图就是象征他们的法律权威的旗帜。
“我是孩子的父亲。”鸟焦燥地重复说,声音里明显流露出受到了威吓的不安。
“哎,哎。”坐在中间的那个男子(他是医院院长,鸟曾经看见他在呻吟的妻子身旁洗手)似乎从鸟的话音里嗅出某种进攻的味道,他带有几分防御的准备,这样应答。
鸟直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