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风流-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又想起冉阿让老兄。当某一天终于成为社会贤达,自己想要干的第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扶贫济困。
望着这么多吃的,他想,这种日子,二哥和彩珠做梦也不敢想吧?心中就有了一丝宽慰。他还有什么可失意的。
他又想着春花了。她是那么善良、美丽,以至众多的城市男儿都不配向她求婚……可他却不能要她。
她只能象秦桔一样,最后卖掉一个肾。
她知道秦桔卖了肾。在她看来,秦桔那么轻易就解救了一家人。他怎么去阻止她的疯狂想法呢?他就连自己的前途都看不见……失意中,他把面前的酒瓶推开。
他还是把酒瓶拿了过来。狷躁的灵魂,需要它的滋润。一瓶白酒喝光了。又打开啤酒。咽下喉咙的酒,从嘴角流出来。大脑刺激出特别愉快的感觉,虽然内心也有了莫名的痛楚。
在有些昏花的目光里,他的胳膊上冒出许多红点。“我被染上梅毒了吗?”他大惊失色,人一下从凳子上跳起来,一边甩着胳膊,身子向后逃去。他撞在了墙上。
他回过头来,用惊恐的目光盯着自己的胳膊。在一瞬之间,所有的红点都消失了。他眨着眼睛,抚摸着这只胳膊,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渐渐,胳膊成了尸体的颜色。他睁大眼睛。胳膊上确实带上了死气,这死气正在向全身扩散……就连心脏也有了窒息的感觉。
“我要死啦……”他这么想,头脑里浮现出太平间里死人们的样子,两腿一软,脊背沿着墙壁滑下去。
他蹲在那里,两只眼睛带着灰色的死光。他用奇怪的样子,抓起地上的啤酒瓶盖,把它按在胳膊上,用力一拉。胳膊上出现几溜儿白印,白印里里渗出几道鲜血。他用麻木的头脑思索着,脸上终于有了微笑。
还不等脸上的笑纹彻底绽开,胳膊上的鲜血就又变成了黑煤色。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恐怖的煤山,他则变成了一堆小坟包一样的煤粉。幻觉里,无数黑煤鬼从煤山上冲下来,双脚踩跺他的身体,小坟包眼看就要在这个世界消失了。
“我不……”他挣扎着,从他们的脚底下爬起来。
他走进幻觉,人赫然站起,冲出屋子。他在夜色中奔逃,甩着胳膊。两只胳膊一步不落地紧随着他。他的脚步更快,把胳膊甩得更猛。“放过我吧,”他哀求道,“让我回乡……”两只胳膊如恶魔似地,紧追着他不放,仿佛非要将他踩扁、踏烂,很可能还要再次剥下他的裤子呢。
绝望中,他差点又尿出来。
#
直到看见巷子的路灯,他才清醒。他呆呆地站了一刻,朝回走。可又实在不想马上回到那间令人窒息的小煤房。
他朝艺术茶廊去了。他要向姑娘们打听一番,金志国到底是啥人。进了茶廊,小方等几个人迎上来。她这就不认识他了,把他当成了大老板,一心要泡他。可他不理她,跟另一个女子进了包间。有人把茶端上来。他跟姑娘聊起了金志国。
“他跟一个大老板搞房地产去啦。”她说。
她说到房地产,脸上带着很大的敬意,说到艺术顾问,并没有这样。她对金志国的过去不了解,只知道他对书法有研究,这个茶廊是他帮着布置起来的。
姑娘的大腿紧挨着保瑞的腿,把热乎乎的体温传过来。然而,这个男人显得如此麻木。
茶廊里又进来几个客人,都是喝了酒的。很快,姑娘们各领着一个客人进了包间。一个姑娘让人把茶廊的大门反锁上。
“对不起,我坐得太久了。”保瑞站起来。
“你付了钱再走。”她瞪着眼睛。
保瑞问,要多少钱。她这就去结账。保瑞站在大厅里等。她回来了,说,是三百九十八块。她交给他一张单据。
“我身上只有二十块钱。”保瑞哼了一声,也不接单。
“这不是抢人嘛,没见过你这么蛮横的人……”她嚷道。
周围站了好几个人。两个男人的脸上带着一股匪气,另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有点象老板。保瑞对这个象老板的人说,我是来打听金志国的,不是来喝茶的,我还给你们当过野马,背过一个叫贾明礼的,我还有金志国的名片。保瑞掏出金志国的名片。
“搞什么名堂嘛?”刚才陪了保瑞的姑娘说。
“我能走了吗?”保瑞问象老板的男人。见对方点头,他便往外走。一男子从包厢里出来,说,乱糟糟的,哪象个茶廊。
保瑞走出十几米远,听见茶廊的金属卷闸门哗啦一声拉了下来。此时就是张正和季小虎过来,也叫不开门了。
第33章 湟水,饱含不屈的意志和力量
这一年,大高原东北部的这个角落,雨水超过往年平均值的一倍。湟水浩浩荡荡。火车站广场西侧两里外的河岸,一些地方早年修了水泥堤岸,一些地方只是用铁丝网围住石块,以保护岸土。在更远的地方,河岸呈现着自然状态,每到夜晚,人类的声息沉寂下来,河水的喧哗声就大起来,不时还会传来岸土崩塌落入水中的响声。这个季节,河水早已不是黄色,而是黑色,水稠得泥浆一般。站在河岸上,浓浓的泥腥味会猛烈地闯进鼻孔。
沿着河岸的土路往东走不到两华里,有一片美丽的杨树林。在这片林子附近,散布着零零散散的麦田,和老式的村舍。村舍在夜色中总是那么寂静,跟城市的喧闹形成对照。刚才,一个处在变音期的少年,在林子附近唱花儿。少年的歌声,引得在河边洗东西的村妇们一阵骚动。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传向很远。这当儿,少年的歌声再次传过来:
#
大豆杆杆吹唢呐,
赛过了青铜的喇叭;
你把我甭当个憨娃娃,
我在个墙头上跑马……
#
少年的身影只有十三四岁,歌声却把她们逗得兴奋起来。然而她们的野性,早就被城市的文明软化下去,以至对出的歌儿显得羞羞搭搭,并不时被羞怯的笑声掩埋……
唯独只有湟水的涛声,永远这般强劲有力,其间饱含了不屈的意志和力量。古老的湟水居民正是通过耳朵和眼睛,持续承受着它的熏陶和滋养,才得以把古老的性格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以便某一天能重现自己的原貌。湟水的涛声在这些无心的耳朵和眼睛里,竟然含上了哀诉的成分。
湟水以沉默的方式,排挤着压迫它的胸脯的水泥堤岸,铁丝网,以及一切企图禁锢它灵魂的人类造物。在这种对野性的呼唤中,时光的养分不断注入河水的拍浪,所以河床里涌动着的就远不止是由冰川融水、山泉、雪霰、冰雹、雨水……汇合而成的流水,也是时间和岁月的感情和意志。
这后者的意义,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生灵要来得更加重要。一切的一切,都是时间这个造物主的宠儿或牺牲品。在时间的舞台上,人类的总体力量因为自身心智的超拔,暂时迅速壮大和膨胀,其增长速率远远超过了土地兄弟,江河兄弟,各种动物、植物兄弟……这个局面,还将持续几百年或几千年。一种不平衡感,甚至还有毁灭的预感,也就必然要刻在大地的脸上和人类的心中,从而使人类永远达不到愉快的极致。人类可以战胜一切兄弟,但最终战胜不了时间与岁月。
#
春花和保瑞坐在河岸的土台上,亲热地交谈。喜鹊在树上低声鸣唱。水流声象是有了情感,或许正是在跟喜鹊们对唱吧。草地的湿气飘过来,跟流水的泥腥味搅在一起。不远处,村妇又唱起花儿,歌声很快被她们的笑声打断。
春花的胸腔,又有些不舒服。
“我现在是不是太瘦啊?”
“嗯,但这样就有了城市雅妇的风韵。”
“才不是哩。”她笑着捏了一下他的胳膊,“也许,我应该每天吃一两猪头肉,一个月吃上三斤。郑家卤肉馆的香味,都把广场淹没了。”她咂了咂口水,把口水咽下去。
“那天我买了一斤,可你却跑掉了。”
“就不会再买一次吗?还是心不诚呀。”
“是啊,明天就买上两斤,让你一次吃个够。”
“还是分几次买吧,先买上半斤就行呀。”她瞅着他,“你觉得,自己是大富翁啦。我不想让你买了。我这几天再也不会见你了。你就自己吃吧。再说,我早就不吃荤啦。真的。”
“我并没有得罪你啊。”
月亮如金色的盘子,镶在天空,映在水里的影子,变成了一片片颤动的碎光。保瑞一时感到自己又回到了侯家堡。月光撒在春花的脸上,使她显得更加俏美。他忍不住又瞅了她一眼。她多么象彩珠,也多么象春芳。他的心脏被什么捏住,感到难受。
#
春花的神智变得有些恍惚。她也在思念家乡,思念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的父亲。她突然想哭。她弄不清,这股情绪是怎么回事。反正,她最近的情绪一直很不正常。
春花的老家距这里两百华里。那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一百万年来,由西伯利亚吹来的黄土覆盖在地表上,如今已堆积了一两百米厚。河水流经那一带,把一半精血失散在干渴的土地上。地学上称这种土为第四纪马兰黄土。春花家乡的人不这么叫,只称作老黄土。老黄土上沟壑纵横,气候干燥,物产匮薄。春花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爬滚了几百年,到了春花,因为造化,她进了城。每个月,她都要给家里寄一笔钱。年迈多病的父母亲,五个未成年的弟妹,都指望着这笔钱。至于她在城里干了些什么,家里人从不过问。最初,她只是来这一带要饭。操家乡口音的要饭人,在这一带曾经很多。她的家乡把出来要饭叫闹吃的。“走,闹吃的去。”就是指要饭去。如今要饭的少了,大概是谋生的手段一下子变多了。家乡的叫花子们,一直喜欢唱一首带着浓烈的山野情调的歌谣:
#
你是哪里人?
我是钢谷人;
钢谷怎么样呀?
钢谷渴死人……
#
男女叫花子,脸上肮脏无比,神态疲惫不堪,但只要一唱起这支家乡的歌谣,眼里就会流露出为外人所不能理解的微笑。
第34章 自杀不被上帝允许,但自虐可以
春花从小就听惯了这支歌谣。久而久之,歌子的韵味如血液渗进了骨肉。贫穷就是这样,变成了心灵的一部分。只是她们依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就好似伸展开来的树根永远能找到水源一样。多少年来,农家就是那一两间破土屋,屋里有个土垒的大炕,全家人就拥挤在这炕上睡觉,做梦,调理筋骨。直到十五岁,春花还跟弟弟妹妹们挤睡在这个炕上。父亲母亲曾经也都挤在这个炕上。每当母亲再生下一个孩子,大炕就变得更挤一点。然而,这炕仍然是大家每天劳累之后最想往的去处。在这里,休息代替了劳作,美梦代替了烦愁。
直到有一天,她走进城里,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比梦境还要美妙的天堂。这个讨饭姑娘在城里长高了,变胖了,脸蛋也白嫩了,就连失神的眼睛也有了神采。后来的许多日子,她时常会想,要是自己一直在要饭,该有多好;要是自己也能象侯保瑞一样,给一户绝对清白的生意人家洗涮碗盘,张罗顾客,该有多好……一天,她在梳辫子时,无意间发现了好些白头发。她愣怔了好一阵。整整一天,再也不能打起精神来。
只是对她来讲,一切思索都显得毫无意义,任何思索也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拥有父母亲赠给的这副身躯,便什么也没有了。父母亲还赠给了她一张需要吃饭的嘴。需要吃、穿和睡觉,也许就是她的几件最大的不幸。不仅如此,她还得操心远在乡间一家人的吃、穿和睡觉。就在今天,她还幻想过,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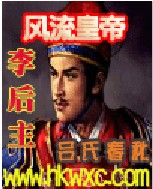
![[综]数风流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1/133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