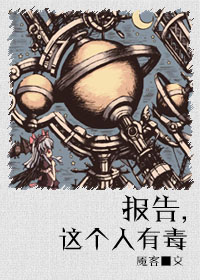幸存者-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吃了个午饭,然后就坐着鑫海山庄派来接我的车子,上了山。
后来才知道,易延端在什邡给我联系的三家宾馆,在地震中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地震重灾区什邡红白镇的那家,全镇的房子基本都塌了,但它没受大的影响。
命中注定我要经历这场灾劫,躲都躲不掉,尽管有那么多预兆,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我应该服从命运的安排?
呼吸
黑夜里传来的轰响让我不再相信这是简单的山体滑坡,这是可怕的地震。连续山摇地动的余震随时都有可能吞噬残存的生命。在鑫海山庄以外的地方,还有多少生命在那瞬间被无情吞噬?山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多少人被埋葬?那说过要救我的老板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余震中遇难?还有易延端,是不是也遭到了不测?
我突然替他们担忧,替他们难过。
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
如果我能够安全出去,我一定会去救人的。
可我现在只有哀叹,自身难保,出去救人的话有点像是谎言。
此时,我身体上的伤口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压在底下的那半边身体已经麻木,失去了知觉。
伤口是不是还在流血?
是不是已经开始发炎,开始腐烂?
我想象着我的伤口慢慢地冒出黑色的黏稠的血浆,伤口的四周在糜烂,翻开的皮肉化了脓,有很多像肉芽般的蛆在蠢蠢欲动……我仿佛闻到了腐臭的味道,那是从我糜烂的伤口散发出来的腐臭味儿。
我的呼吸沉重。
我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
只有呼吸的声音可以证明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开始腐烂。我的皮肉会慢慢地腐烂,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最后连呼吸的声音也会消失,就像唱机碰到停电,歌声戛然而止。
我想象着躺在家里那张舒适的大床上的情景,李小坏躺在我的旁边,面朝着我,她的小手放在我的胸膛上,一条小腿也搁在我的肚子上。她在我身边沉睡,我听着她轻微的呼吸声,闻着她身上的奶香,心里充满了慈爱。
我伸出尚能动弹的右手,往旁边摸了摸。
我希望能够摸到李小坏温热柔嫩的小手或者小脸,可我摸到的是冰冷的碎物和从破碎的木板上刺出的铁钉。
我心里一阵悲凉。
我的呼吸停止后,刚刚过完周岁生日不久的李小坏就永远没有爸爸了。
她爸爸永远不会抱着她,轻轻地哄她睡觉了,也永远不能保护她了。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个最亲近的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人……
可怜的李小坏呀!
我想流泪,可流不出来。
我眼睛里只有黑色的血在循环流动。我还能呼吸多久?
活着的尊严和死的尊严
我难以形容在黑暗的废墟下所忍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果说在那瞬间被砸死了,那也就一了百了了,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死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一切悲伤痛苦留给活着的人承担。这是十分自私的想法。是的,我想到过自杀,可我找不到自杀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连自杀的能力也不具备。
但是我很快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自杀是没有尊严的!
那是在背叛生命。
在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我两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其中一次是在梅离开的时候。她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她,我听到她乘坐的那班飞机从我们部队办公楼顶飞过的时候,我霍地站了起来,伸出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抓住。那天,我一天都是痴呆的,房间里还残存着她的气息,还有她用过的东西。我们在七月的北京相识,爱情像七月的骄阳那么如火如荼。那时她才二十岁,我也只有二十五岁。或者有些盲目,或者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残酷,并不是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可毕竟我们是相爱的。我们的爱情随着她的离开也死亡了,那段时间我总是神思恍惚,像是被魔鬼吸去了灵魂。我在一个晚上,企图用刀片割断我手上的动脉血管。就在我要动手的时候,战友陈强敲响了我的房间门,我手上的刀片掉落在地上。陈强手里提着一瓶白酒和一包卤鹅肉,笑着对我说:“呆在那里干什么?喝酒吧!消消愁。”那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谈了很多。当他得知我有轻生的念头后,他朝我吼道:“你他妈的还是男人吗?我一直以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是个孬种!男人要死也站着死,自杀算什么东西!”他走后,我把那刀片扔进了垃圾桶。没错,自杀是没有尊严的,那是对生命的背叛。
在这个黑夜,我自然也想起了她,想起她无奈的表情。
也想起了浩林。
他们同样是我心中的痛!
我想在我呼吸停止之前向他们告别,却无处告别。
……
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没有贵贱之分。
父亲大名叫李文友,小名叫火贵生。他一生在故乡闽西乡村靠种田和做豆腐为生。沉默寡语的父亲很少和人聊天什么的,在我记忆之中,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劳动着。他年轻的时候身体特别健壮,我记得酷暑的时候,他在田野里劳作时,总是光着厚实的被阳光晒得脱皮的后背,汗水从他的背脊上淌下,湿透了裤子。父亲做什么事情都不求人,能干的就干,干不了的也不强求,在父亲的词典里,没有乞求这两个字。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无论再难再苦,也默默地挺着脊梁把它干完!这一点我继承了他的秉性,我不会乞求我得不到的东西。
父亲有他做人的原则。该是他的东西他就要,不是他的东西,他想都不会去想。那时候,他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当时生产队的保管员李路长和他关系不错,李路长后来因为贪污被抓起来了,有个别人怀疑我父亲也有问题,上面下来的工作组就调查他,看他有没有和李路长同流合污。结果父亲清清白白,怎么查也查不出问题。生产队的社员都站在父亲一边,说他是个老实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和李路长一起贪污。父亲靠着读了两年私塾的底子,把生产队里的账目理得井井有条。多少年后的今天,他还保留着那些年当生产队会计时的账本,他对我说过;什么时候来查他,他都不怕!那年大洪灾,他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了那一塑料袋的账本,就是为了两个字:“清白”!
父亲一生辛劳,为我们四个儿子和两个养女耗尽了心血。
在他的肩膀上,扛着的永远是责任。
父亲也从来没有怕过什么!
他从来不会去欺负人家,却不容别人践踏他的尊严。
他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们几兄弟都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很多美德。
我们都觉得应该像父亲那样活着,一生坦坦荡荡,经得起考验。可我在生命的路途中却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沉沦。每当我做了些亏心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是对父亲的侮辱。父亲的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的行为。
父亲很少动手打我们兄弟,可他有一次差一点一巴掌把我的耳朵打聋。那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和一个邻居的孩子打架,结果我打输了,我一怒之下抱着一块石头冲到邻居家里,把他家的锅给砸了。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我准备偷偷地溜进屋里,却被等在厅堂里的父亲叫住了。父亲阴沉着脸,浑身在发抖,我站在那里,知道不妙。他老鹰抓小鸡般一把把我提溜过去,咬着牙说:“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我低着头,大气不敢出一口。父亲愤怒地吼道:“你说呀,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急了的父亲扬起蒲扇般的巴掌,朝我的左脸扇了过来。我听到一股凛冽的风声,随后我的左耳嗡的一声,脑袋就晕了……父亲说:“你出去和人打架,打输了你就要认输,打赢了也不要得意,但是你怎么能够去砸人的锅呢!你知道吗,那是流氓无赖的行为!你丢尽了我的脸!”
我知道父亲用心良苦,他是要我做一个输得起的、赢得光明磊落的、有尊严的人。
活着的尊严和死的尊严同样地重要。
父亲如果知道我埋在废墟里是因为忍受不了痛苦折磨自杀的,他一定会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做!”
父亲如果知道了我的死是因为血流干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而死,他会用沉默的忧伤表达对我的感情。
想起父亲,我内心十分沉痛。
四十多年了,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没能让他苍老的心灵得到慰藉,却在浪迹的途中死于非命,这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在他面前,我不是个负责任的人,无论是对他和母亲,还是对我的妻儿,我都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我能够这样死去吗?
回故乡之路
明年的这个夜晚也许就是我的忌日。随着余震次数的增加,我身上积压的碎物越来越厚,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这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我的坚持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每次路过我家附近的龙华殡仪馆时,我就浑身毛骨悚然,有些时候我特别脆弱。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殡葬工人,亲眼看过他把一具尸体送进焚尸炉。说实话,我接受不了火葬,总觉得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人死了,就应该让他穿戴整齐,安放进棺材里,然后入土为安。
这似乎和观念的新旧无关,这是对死者的尊重。
我经常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的尸体运回故乡,埋在我奶奶的坟边。”
她笑了,“老土,现在谁还土葬呀!”
我很严肃地说:“你记住我刚才的话没有?”
她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收起了笑容,点了点头。
现在看来,我的尸体要回故乡埋葬是不可能的了,这里离我故乡那么遥远,而且我的尸体能不能完整地被挖出废墟还是个问题。看来,我注定是个漂泊异乡的孤魂野鬼。
多年来,我在现实的生活中,常常被物欲压迫得抬不起头来,常常为了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伤害着自己的灵魂,现实的罪恶让我徘徊在崩溃的边缘,脑海里充斥着污浊的东西,我的一身臭皮囊已经无法回到纯真的年代。
我想我的灵魂和肉体早已经背叛的故乡。
我离当初逃离故乡的那个充满理想的少年越来越远,也离那个曾经感动过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那些闽西乡村的风景在我眼前是如此的灰暗,却又如此地令我感伤。那是我逃离的地方,此时却是我最想归去的地方。故乡那苍茫群山里,是否还有斑鸠飞过?田野是否还稻花飘香?汀江里的流水是否还那么清澈,或者洪水滔天?……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的故乡。是我死了都想运回去埋葬的故乡。那些野地里自由开放的苦草花,或者还记得我的模样,以前,每年清明时,我会采摘一束束的苦草花,放在已故亲人的坟前。那是乡村里最平凡的花朵,平凡得它连一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在野地里自由生长,而且生生不息。苦草花就是我故乡乡亲的形象。
此时,我想起那些淳朴的乡亲,会突然心动,感伤。
我发现我是那么多愁善感的人,而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武夫。
黄毛婆婆该有九十岁了吧,不知道她现在身体怎么样,以前打电话回家,会向母亲问她的状况,想想,也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人老了,就像一盏临近熄灭的油灯。在那饥馑年代,黄毛婆婆会偷偷地把一把地瓜干塞到我书包里,轻轻地对我说:“孩子,带上它,饿了吃吧,看你都饿成皮包骨了!”
还有那个一生都孤独一人的杨秀婆婆,七十多岁了还自己下田劳作,她在我眼中永远穿着打满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