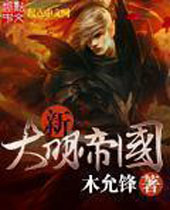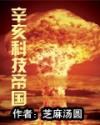大汉帝国雄风录-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了一会,卓文君从李云怀中跳起来,打好清水,梳洗了脸颊,将那盘兔腿放到李云面前道:“李君,这个是我做的,你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李云用筷子挑起一丝肉丝放入嘴中,只觉得香甜可口,赞道:“文君,真好吃!你以后天天给我做好不好?”
卓文君羞涩的点点头。道:“李君,走,到客厅去吃,在这里吃多不象话?”
李云跟着卓文君走向客厅,一边走一边道:“文君,有件事我想有必要和你说!”
卓文君道:“有什么事情等吃完再说好吗?”
李云摇摇头道:“不,我再不说出来,会憋死的,我对不起你!”
卓文君不解的看着李云,不明白他说什么,李云叹了口气将天子赐婚的事情说了,卓文君听了却并无什么反应,依旧是那样的看着他,过了一会才笑道:“李君,此事你不说,文君也知道,男儿志在四方,君终究是要大展抱负的,文君只要你不辜负我的心意就是了!”接着卓文君又道:“李君,那南月公主君可见过?”
李云点点头,卓文君问道:“那她怎么样?”
李云老实道:“很漂亮,很文静!”
卓文君又问道:“她今年芳年几许?”
李云道:“十六了!”
卓文君拍着手道:“好啊!文君早就想找一个妹妹了,可惜一直没找到,这下好了,文君有伴了!”
李云没想到他一直担心的卓文君竟然是如此的大度,心中一直感动,伸过手将她软软的身子搂进怀中,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
解决了儿女私情之后,李云信心爆满,第二日就在县衙外贴出告示,广招有各种技术的人才,待遇写的丰厚至极,足以令大多数人心动。
比如一名技术精湛,擅长机关制作的工人每年可拿到不低于四百石的薪水,另外还有年终奖金,季度奖,优秀奖等写的诱惑至极的条件,当真是令许多人红了眼。
李云当然知道要想养成人们学习技术的热潮,必须是金钱开路,只要学技术的都能拿到优厚的待遇和社会地位,那么大汉就永远不会在愁没有发明创造,而华夏民族也就可以永远领导着世界科技的发展方向。
但是为了避免有人说他李云在临邛任上,不重农本,舍本求末,因此他同时还招聘那些有种田技术的人才,一来是为了摸索出在大汉现有条件下可以实现的新农业技术,二则是因为他从西域带回的棉花种子和葡萄需要有人种植,推广。毕竟中原人并不知道该如何种植这些从未有过种植历史的农作物。
李云的告示一贴出来,整个临邛沸腾了,各家作坊中的老师傅见了那优厚的待遇,难免心动,不少人纷纷抛弃了原来的东家,跑到县衙报名。
一时间临邛的各家作坊中,有经验的工人纷纷向东家递交辞呈,各大作坊慌了神,忙将工人的工钱向上调,以此来留住这些工人,也是从这时候起许多有眼光的商人开始注意到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假如垄断人才将给自己带来的暴利,比如卓张两家便开始下力气培养新的技术工人,而由此引发的影响,甚至连李云也想不到最后竟然影响了整个大汉商业发展的走向。
技术人才,原料,开始成为商人们重点关注的项目。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李云就一共招到了二百多名技术精湛的各行各业人员,这些人不仅有临邛本地人,更有从邻近县听到消息跑来的技术人才。不过在这其中农业和冶炼型人才占了绝大多数,另外还有三十来名木匠,十多名陶瓷匠以及七名李云最想招到的造纸人才。更有数名炼丹方士被入选,李云希望靠他们的手可以先一步将火药弄出来,虽然李云知道黑火药的威力不大,但是至少黑火药可以用来当恐吓品,试想一下,假如两军对阵,一方在关键时刻忽然引爆大量发出巨响的火药,纵使不能杀敌,至少也可在心理上狠狠的打击对方,甚至可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更何况大汉的主要敌人是纯骑兵作战的草原民族,而火药爆炸发出的巨响,无疑是可有效惊吓对方马匹,扰乱敌人攻击秩序的不二良器!
李云花了大半天时间将这些招徕来的技术人员各自分好工。
农民主要负责实验性的种植李云带回来的棉花,葡萄,并且摸索出类似代田法的耕作技术,李云和他们详细的解释了一下现代的农业技术,譬如多打牲畜的肥料到地里做底肥等,又分给他们几十顷属于不可耕的废地,嘱咐他们务必先施肥。
所谓不可耕之地,这种土地一般属于农民的废弃地,这些土地由于靠近大道,或者肥力不足,所以产量极为低下,没有农民愿意在那些土地上耕作,所以大汉律也有明文规定,不可耕之地,经核实后,可不收取任何赋税。
但是这些常人眼中的废地,在李云眼中却是完全可以改造成良田的好地,因为大汉现在还未有人知道应该将牲畜的粪便做底肥,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废地,和每三年一次的休耕,这在李云看来实在是大大的划不俩,且不说废地,单是土地大面积的休耕,就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任谁看了都会心疼。
所以他迫切的希望改变这个局面,但是强迫农民用底肥,显然是极不可取的做法,这样做只会引来传统势力的抗拒,强迫永远也不如引导,李云希望这些招徕来的人成为榜样,将这个技术传播到大汉的各地,这样一来,每年粮食的产量就至少可提高三成到一半,足可应付未来百余年人口爆涨所带来的粮食危机。
而冶炼工人自然是被全部分配到兵器监,李云更投下十万余钱的巨资,扩大兵器监的规模并增加了好几口冶炼炉,李云不是冶金业毕业的,所以他也只能做到这么多,尽量为冶金科技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其他的也只能靠这些技术精湛的工人来努力了。
那十多名陶瓷匠则是承担起了烧制出水泥和新式瓷器的重任,水泥很好办,大汉现在的瓷器在李云看来太过原始了,李云希望至少可烧出成熟的青瓷来,这样单单是靠卖青瓷,临邛人就可大赚一笔。
至于那些方士和有造纸技术的人才,则是李云亲自带队,李云想自己亲手制造出历史上第一张白纸,第一份黑火药,这个荣耀他当然不会放过。
卷四 风云
第十一节 双雄会
长安的七月,雨有些小,阴沉沉的天空上始终郁积着一片厚厚的乌云,公孙弘抬起他那有些苍老的脸,望了望天空,不禁有些感叹命运对他的不公。
公孙弘乃字川国薛地人,年少的时候家境贫寒,连生活都难以维持,那时候他靠着放牧些家猪过日子。
后来他走运的得到家乡一名朋友的举荐,得以到薛县当任狱吏一职,可是奈何他自小学识微薄,不懂法令,不久就因为犯罪而被免职。
旁人若是遭了这般变故,不说自暴自弃,怎么着也会再无心思向官,可他公孙弘不是这样的人,知耻而后勇,是所谓真大夫也!秉承着这样的信念,当时年轻的公孙弘毅然在麓台村苦攻学识,四十岁那年更拜入当世大儒胡母子门下学习《春秋公羊传》。
几年后得到老师的赞许而出师,公孙弘至今依然记得当时他的豪情壮志,他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学来为儒家争取地位。
可是十多年下来,他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低头,方才他冒雨去魏其侯窦婴府上自荐,因他早听说当朝三公之首,大将军窦婴素喜儒家,可是他信心满怀的去,却连门都进不了,魏其侯的下人听说他是一名儒者之后,立即就将大门关了,冷冷的回了他一句“你还是去读读黄老之学再来吧!”
为何为官之路会如此的坎坷哩?公孙弘摇摇头,摸摸了怀中的盘缠,只剩下不到三百钱了,倘若在这些钱花完前他依然不能找到一名肯赏识他的贵人,那么毫无疑问他不得不再次踏上回家的道路。
可公孙弘不甘心,他已是第四次来长安,每一次他的运气都很不好,特别是前年,那年他刚来长安恰好就碰上了太后对儒家大发雷霆,长安城中所有的儒家学者具被扫地出门,他自然只得收拾包袱打道回府。
可是这次他已决定不再回去,因他今年已经六十岁了,人道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他已不能再等下去,否则到他死亡的那天,他也无可能完成光大儒学的志愿。
公孙弘走到一家酒肆中,叫上一壶浊酒,两份小菜,一边吃,一边听着这酒肆中客人的谈话,他希望可以从中听到些什么有用的信息。
跪坐在公孙弘对面饮酒的是几位衣着华丽的贵公子,看年纪不过十五六,他们今天显然兴致很浓,几人一边对饮,一边说着话。
公孙弘只听得一人道:“杨兄,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可再见,我等兄弟今日就敬兄一杯,愿兄学业有成,早日飞黄腾达,那时可勿要忘记了今日我等的兄弟之情,朋友之谊!”
另一人道:“是极,杨兄真是好福气,生在那临邛可得到李云李大人的亲自教导,我等羡煞不已啊!”
而很显然是今日的主角的那名少年却道:“张兄,范兄,二位兄长如此抬举小弟,小弟实在惭愧!”
那几人起哄道:“杨兄,现在长安谁人不知,李云大人圣眷正浓,又有太子照拂,杨兄拜入李云大人门下,自然也就是上了升官的捷径,杨兄却还在谦虚,要不杨兄你我换换如何?”
那杨姓少年晒道:“别的东西,小弟或许会答应,但是这个机会嘛,可遇而不可求,纵使千金亦不可换之!”
那杨姓少年是临邛城南杨家的独子,今次来长安本是见他那嫁与长安勋贵的姐姐,因此也结识了这些长安城中的公子哥,却不想还未玩出兴致,他父亲就急书于他,令他快快回家,说是临邛县令李云已答应收他为弟子。
本来一个小小的县令,是怎么也入不了他那姐夫的眼睛,可是李云却又不同,现在长安的勋贵谁人不知这李云正是棘手可热,不仅仅得到天子的赞许,太子的欢心,就连魏其侯也认之为义侄,当真是红的发紫,因此见信后立刻就将正在长安嬉戏的小舅子拉回来,着他立刻准备好回临邛。
可他到底是少年心性,一时忍不住偷偷跑出来,在伙伴面前炫耀,而知道了此事原委的少年,自然是立刻就起哄要他请客,于是就有了酒肆中的一幕。
公孙弘听了这些少年的话语,心头剧动,他们说的临邛县令李云到底是何许人也,公孙弘并不清楚,毕竟他只是一个游离在政治决策圈之外的人,对于圈内的事情并不清楚。
可他很奇怪,因为一个县令收弟子,这并未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这些少年却比拜了一个有名的学者为师还高兴。
公孙弘当下心头就冒火,想他公孙弘苦读儒学经典数十年,论学问当今之世也就唯有广川董仲舒可在《春秋公羊传》的造诣上远胜于他,其余人哪会放在他眼中。可如今他却依然没有半个追随者,而广川董仲舒的弟子却早过百人之众,如今在这酒肆中更是听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令也可引来这些少年的崇拜,人人似乎都想拜他门下。
公孙弘并非是心胸狭隘的人,可是任谁到了六十花甲,苦读半辈子学识,却无一人赏识他的才华,心理都难免扭曲。
公孙弘压下心中怒火,他本就是极为善变之人,多年来的磨砺将他性格磨的极为圆滑。他露出一个慈和的笑容,问那名杨姓少年道:“这位小哥,老汉我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