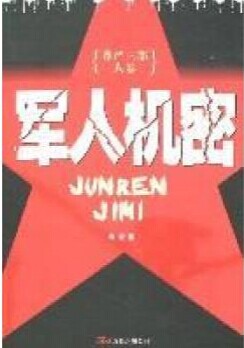军人大院-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之她什么可能都想了,想到最后剩下的就是对皇甫更加强烈的思念,这种思念像长了牙的猛兽一样,使劲地在咬着她的心、她的神经。
突然,树林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皇甫就出现了。还不等皇甫站稳,朱丽莎就猛地扑了上去,一把搂住皇甫的脖子,呜呜哭了起来,边哭边使劲地挤向皇甫,皇甫顺势倒在了地上,朱丽莎也随着他倒了下去,但手依然紧紧地搂在皇甫的脖子上,皇甫一翻身,就把朱丽莎压到了自己的身下,接着一阵狂风暴雨的吻点落在了朱丽莎的脸上、眼睛上、嘴巴上,最后就在朱丽莎的嘴上停住了,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在粗粗的鼻息声里,唇与唇紧紧地吸引着。
许久,朱丽莎移开了自己的嘴,睁开了眼睛看着皇甫,皇甫看到了她长长的睫毛上挑起的晶莹的泪珠,又一口叼住她的嘴吮吸着。皇甫本来已经膨胀的身体,现在就好像要爆炸一样,他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额头渗出了密密的汗珠。他飞快地扯下了朱丽莎的下装,……
朱丽莎感到自己飞了起来,身体好像已经失去了重量,她好像坐在云端,轻柔地飘啊飘,她只想向上,向上……
许久,皇甫翻过了身,脸冲着天,说:“我爱你。”
朱丽莎浑身一激灵,脑袋里呼地刮过一阵风,竟忽然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
43
自从上次朱丽莎那样说了王萍平以后,王萍平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好起来,尽管她们没有吵起来,但是,王萍平知道在别人的心里关于她的事都已经清清楚楚了。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清楚,那本来就是一个让她心疼的伤疤,她以为那是一个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的秘密,一个连她自己都不愿多想的秘密,那个秘密实在是太……
因此,她恨,她恨所有的知道她的秘密的人,她想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她为什么要比别的人承受得多?她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她不要承受。
这一天,王萍平在做完治疗以后又钻到了会议室里偷偷地看起了英语书,她坚定地相信,总有一天她会等到机会的。
忽然,会议室的门开了,她看到护士长那一张阴沉沉的脸,护士长冷冷地说:“你去看看你做的治疗吧。”说完就转身走了。
王萍平跟了出来,心里想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她跟着护士长到了一个病房,护士长走到了23床的前面,没有说话,而是用嘴向那个病人努了努,完了就自己走了出去。
王萍平看了一眼眼前的病人,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她看到病人的右眼肿得像一个桃,她想起来了,这是她刚刚进行过球后注射的病人,她的心一阵惊恐。她来到了护士办公室,看着护士长,护士长说:“王萍平,再怎么你也是一个老护士了,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
“我……”
“是不是没有三查七对?”
“不,不会的。”
“我看是剂量问题。你最近怎么了?老是心不在焉。这还是小事,要是出了大事,我看你怎么办?”护土长说,她的声音不大,但是扎得王萍平的心很难受。
王萍平沮丧极了,她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朱丽莎那刻薄的话引起的,在会议室里她哭得伤心极了。
对于任歌,杨新民有足够的耐心,他相信女孩是要追的,只有穷追不会,才能得到自己最想得到的女人。
这一天,杨干事又来到了任歌她们宿舍,他敲了敲门,听见里面传出“进来”的声音,他听出是任歌的声音,心想着还好,没有白来,就推开了门。声音很轻,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声音,他蹑手蹑脚,因为他看到任歌正在画画,她把纸钉在了墙上,地上放着一个堆满油画颜料的凳子,任歌手里端着一个调色板,正画得专心。杨干事悄悄地走到她的身后,看到任歌正在临摹一幅外国人像,是一个金发女孩的像,他就抱起手做出看她画的样子。
任歌在画上又添了几笔,这才回过头来,一看是杨干事,就“哦”了一声。
“你坐吧。”任歌指了指自己的床。
杨干事点着头向她的床边挪去,他看到床单很干净。就犹豫了一下。
“没关系,你坐吧。”任歌手里还端着调色板,并用调色板比划着。
“你喝水吧。”任歌说着就放下手里的调色板,要去倒水。
“不用了,我不喝。”杨干事忙起身。
自从有了大平地的交谈,任歌就对自己说,不能那样对杨新民,她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她觉得自己尽可以不爱他,可以不接受他的爱,但是,千万不可伤害他。他再怎么说,也还算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他能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他还是走了一段非常不容易的路。
任歌坐到了朱丽莎的床上,正好对着杨干事,她看了一眼杨干事,想找个话题,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就把胳膊放到桌子上,看着桌子上的一排花花绿绿的书脊。看到一本书,她又忍不住地把它取出来翻了翻。
“画得真好。”杨干事说。
任歌就摇了摇头,“瞎画。”
“哦,可不是瞎画,从我来到一五八,还从来没有见过画画画得这么好的。”杨干事忙说。
任歌就笑笑,不太信这些话。总想杨新民肯定不会跟她说什么真话,不过,他也不懂画,就不再多想。
然后就是沉默,任歌满脑子在急急搜寻着该说什么,可就是想不出来。杨新民似乎也在想,想出一个话题又觉得庸俗,怕任歌不感兴趣,就不敢开口。抬眼看一看任歌,看到她正拿着一本书在翻,就更不敢说话,怕打扰了任歌。
时间在流逝。还是无话。
任歌站了起来,说:“我还是画画吧,你坐,好吗?”
杨干事就一个劲地点头,“好、好。”反正心里舍不得走。
任歌又抄起画笔和调色板,站在墙面前,马上就进入到了作品中。就这样,杨干事在一旁看着,任歌画着,有时,任歌都忘了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人。宜到朱丽莎回来,又坐了一会儿,杨新民才起身告辞。
杨新民一走,任歌像放下了一个很重的大包袱似的,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朱丽莎奇怪地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朱丽莎说:“谈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任歌瞪了朱丽莎一眼,“简直就找不到话说。”
“嗳,可怜啊。”朱丽莎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
“谁可怜啊?”
“两个都可怜。”
任歌一想,也对。真是两个都可怜,可是怎么办呢?就想也许自己这样,是会害了别人,可是难道和他大吵一顿,或者把他臭骂一顿吗?任歌越想越觉得理不清,就摇了摇头,又对着墙画了起来。只有涂抹着这腻腻的油彩,闻着一股浓浓的油彩香味,她才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她真的使劲用鼻子吸了吸,看上去很惬意。
44
这一天,当任歌站在一片田野上时,她的神经仿佛忽然被烧起来一样,她有一种想大喊大叫的欲望。她看到的田野是一片深红色的土地,在冬天的阳光下,没有任何生长着的作物,红土地无牵无挂地裸露着。
任歌立刻昂扬在那一片土地上,手里提着一个油画箱,那是一个不太正规的油画箱,是她请医院的老木工做的,凭着她的想象做的。还是穿着那一身军装,是冬装,站在田野里的她,本身就是一幅油画,她就像长在田野里的一棵树。齐耳的短发,总是像水泡着的一双透着淡淡的忧伤的眼睛,饱满的嘴唇,灵巧的鼻子,浑身透着一种不俗的气质。
在田野的尽头,她停了下来,放下手里的画箱,打开盖子,箱盖上已经事先用图钉订好了一张100克的白纸。从箱子里取出调色板,然后在上面挤上各色颜料,把随身带的挎包放在地上,挎包里面有带着的饼干和一壶水,也取了出来。她把挎包垫在屁股下面,画起画来。
这是一个星期天,一个冬日有着暖暖阳光的星期天,任歌选择了这一天到野外来写生。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户外来写生了,在春天、夏天、秋天的时候,她都到野外写过生,她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惬意,她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感激着一五八,是一五八使她拥有了自由的天空,她觉得她终于可以像一只飞出鸟笼的小鸟一样飞翔了。
她在白色的纸上画下了第一笔,用赭石色,用小号的排笔,在画面的上1/3处,斜着半孤形地画了一条线,一幅图画已经长在了她的心里。
温柔的阳光很怜爱地照着她,她整个人沐浴在阳光下面。她蹲了起来,放弃了那个用来作垫子的挎包。她一会儿眯起眼睛看远处,一会儿又收回目光看眼前的画面。恍惚中,她感到自己在摇动,摇动,眼前有一些舞蹈的少女,她们举着白色的纱巾,裸露着棕色的胴体,站在一座金红色的冰搭成的舞台上,她们舞啊、舞啊,忽然,她们手里的白纱巾变成了火红色的,而舞台成了一个用真正的冰搭成的透亮晶莹的舞台,少女的眼神含着浓浓的忧郁,还有坚挺的棕色的如小馒头一样的胸,一脸的圣洁,一阵悠远的音乐像一股坚硬的光芒越过她们的头顶……
画面在变化,在任歌的想象里呈现……
她沉浸在她脑子里的那个世界里,忘记了周围,忘记了天空,忘记了一切。
最后她像从梦中走回来了一样,舒展开身子,蛇一样摆动着身体。
任歌这时才发现已经在她的身边站立了许久的戴天亮,不过,那时她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在他们交谈了许久以后,她居然忘了问这个男人叫什么,仿佛一切都已经是前世定好的,她感受到了心跳和慌张。
“你好。”戴天亮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交谈的。
“你好。”任歌觉得他看到了自己什么,有些难为精。
“尽管是轻飘的小情调,但是毕竟是你的世界。”戴天亮轻描淡写地说着。这就是他对任歌画的评价。
任歌举起目光,认真地打量着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不速之客。首先给她的感觉是眼前这个解放军气宇轩昂,剑眉下的一双眼睛竟莫名地流淌出水一样的柔光,坚挺的鼻子,一张极其精致的嘴,就是画画意义上的精致,或者说是棱角分明,嘴角很深,这种嘴无论长在男人或女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扭转乾坤的作用,它会让你一下子极其像一个正派人。—。
“最起码我还有一个属于我的世界。你呢?”任歌在看过眼前的这个男人以后说。
“是啊,你比我活得要幸福。”戴天亮说着就也蹲了下来,接着就干脆坐在了地上。
任歌转着身子看了看四周,什么也没有,在田野的尽头连着连绵的山,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呢?就说:“你从天上来的吧?”
戴天亮笑笑,“抱歉,我这样的人上不了天,最多也只是天地之间吧。我看你倒是像刚从天上回来。”
“要不是你捣乱,我还要在天上呆一呆。”
“哦?”戴天亮说,“天上呆长了不见得是好事,你还要谢我才是。”
“难道你不知道有梦才有美好。”
“不过,梦毕竟是梦,再好的梦也是虚无的。”
“想必你是高炮兵吧?”
“何以见得?”
“专门毁别人的梦。”
戴天亮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看你应该改行。”
“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
“在这里的女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