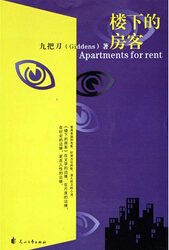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想去哪儿?”她问,“要不我回去把女儿也叫上,这会儿她应该放学了。”
他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想让女儿看到我现在的模样,就咱们两个人去,去北海。”
那天,他的精神特别好,可能是镇痛药加麻醉剂又一次产生了奇效,也可能是生命垂危的患者都曾出现过的那种回光返照。他的声音又像流水那样清澈,额头上的皱纹也不见了,晦暗的脸色显得红润了许多,似乎全身的疼痛已经消失,竟然谁也不用帮忙就自己坐立了起来,活力四射的眼神奇妙地又出现在昨日还处于垂危状态中的他的脸上。
“我们偷偷地出去,别声张,”他悄声道,“这会儿正是医生、护士们交接班的时候。”
她推着他慢慢地走过住院处长长的走廊,当时,医护值班室里站满了人,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转过头来向走廊里看上一眼。来到医院门口,他们又顺利地叫到了一辆出租车。而通常这些司机们是不愿意拉残疾人的,他们嫌麻烦。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黄昏里,他们又一起来到当初他们相识的地方。面对着清澈的湖水,眺望着对岸绿树环抱的白塔,他显得非常激动,他执拗地要她帮助自己坐到当初他们相识时他坐过的那张长椅上。
“这样多好啊!”他拉着她的手,说,“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就像不久前才发生的……那天,我一把拽住了你,把你从困境中拉了回来。”
她望着他痛心地想,今天我却无法将你从病魔手中夺过来。
“在我的人生中能够与你相识、相爱、组成家庭并有一个那么可爱懂事的女儿,真是莫大的幸运,真的,我总是这样想。其实,咱们之间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是我在不停地付出、给予,我觉得,你同样也是在给予、付出。”他惬意地舒展了一下身子,望着水面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道,“有时我甚至这样想,我们之间的爱情就像我的病……”
“你说什么?”她惊诧地问,“你是说我们的爱情像你的病,像癌症!”
“是的,尽管这话显得有些可怕和难听,但我此刻实在想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他说,“就像不断繁殖的癌细胞和淋巴液不断地侵蚀着一个人的肌体,癌越发展,病人就越清楚,任何药物都无法制服它,任何手术都不能将它根除。因为此时癌症已经夺取了这个人的每个器官,每一处组织,他再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同癌混成了一体,混成了一种只能用死亡来分解的粘液了。就像我现在提到‘我的病’时是平静、宽容、甚至还带有几分亲切的口气一样,我对你的爱就达到了这种程度。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了绝不忍心让你哪怕是有一点不开心的地步。为了这种爱,尽管我自己受到过创伤,但决不会让你受到创伤,尽管我自己受到过背叛,但决不会让你受到背叛,就因为我爱你。我甚至爱你的缺点,爱你的过失,爱你的犹豫,爱你的迷茫,爱你的谎言,爱你的一切。抛弃你就是抛弃我自己,抛弃你的幻想,就是抛弃我的幻想,抛弃你的希望,就是抛弃我的希望。这就是我对你的爱情,你说他像不像一种病,一种得了就无法治愈的病?”
他不停地说着,她的热泪不停地流着。她要他不要再说,并用亲吻阻止着他。他们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动情地亲吻着,像热恋中的情人们一样。
沉默的钟楼 70(2)
当他们离开公园时,夜空阴沉沉的,看不到一颗星星。本来很多天都是骄阳似火,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但那天却阴沉下来。那天夜里,先是狂风大作,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暴雨,闪电不停地划破夜空,雨水充满了街道,直到黎明时分一切才恢复平静。早晨的天空依然是阴沉沉的,好像灌了铅一样,街面上流着雨水,被刮断的树枝和砸落的树叶令街道显得杂乱不堪,路上的人们低着头匆匆赶路,脸色和天空一样阴沉,到处都预示着不祥。
就在这天夜里,李全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索燕和他的女儿。她感到当时就像自己一直依靠着的一座大山突然间倒塌了似的,将她深深地埋了进去,压抑、黑暗、看不到一丝光明。
她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是在太平间。当时,太平间外面站着几个她不认识的人,他们站在那里沉默着。她被推入到一个大房间里,一支小小的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发出微弱的光。那里的工作人员见她进来,将一辆蒙着白被单的担架车推到她面前。白被单下面是李全明的尸体,从头部、放在胸前的双手以及双腿的形状很容易辨认出来。工作人员揭去了被单,她看到了他。她好像看到他又像往常那样伏在桌前,专心致志地为别人检修电视机时的模样。他穿着她为他买的那套黑色的衣服,里面穿着雪白的衬衫,头发像起伏的波浪。昨天,他们还一起坐在北海岸边相亲相爱,而今天他却一个人孤独地走了。他僵直地躺在那里,冰冷严峻,无动于衷,对任何爱情的语言和动作都毫无反应。她先是胆怯地呼唤他,而后又犹豫地触摸他,最后,她哭着伏在了他的身上,想将他重新温暖过来。但他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反应。“别哭了。”她听到那些不相识的人在劝她,并将她簇拥出了太平间。
外面夜幕已经降临,她一个人走在街上,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从里到外有一股彻骨的冰凉。她机械地迈动着双腿,不停地向前走着,不知道自己将走向那里。
她想着李全明,想着他为自己所做出的一切,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或许在别人看来,他们之间的结合是一桩时代造就的畸婚,但她却觉得是一种幸运。当初,是他在她像挂在副食店里的鲜肉一样任人挑选的时候,挺身而出收留了她,用他特有的方式,帮助她重新树立起了生活的信心。是他在她浮躁闹腾的时候,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剧烈的病痛,独自一人抚养着他们的女儿,支撑着她的家。几乎所有人都有可以选择生或死的权利,但李全明却不幸地属于别无选择的那一类,因为他的生命权被死神过早地掌握了。他无法选择人生的长度,无法增加生命的数量,但他短暂的一生所达到的高度和质量却使索燕受益无比。他那种高尚的品格,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教给了她许多许多。
她想,每一个知青的情恋经历,或许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这样的故事又都无法抹去地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它令人回忆,引人思索,给人启迪。虽然那个时代已经久远了,但它仍然使人相信,在那个时代萌生的恋情,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轻飘、世俗和晃动的,因为它有着真诚和凝重的根基。她和李全明之间的恋情就是证明。
沉默的钟楼 71(1)
黄圆的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在不长的时间里,她先后将翠翠和她的儿子刘山,还有已经七十多岁的叉子的母亲接到了家里来。
你和黄圆商量此事时,她说,“这事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也跟黄方提过很多次,但他就是不放在心上,哪有把自己的儿子扔在山里不管的道理,再说人家翠翠对他那么好!只是……”她停住话口望着你,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只是我不知道你对我将叉子母亲接来一事怎么看?你不会在心里……”
“别扭、吃醋,说你不忘旧情?”你反问。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才不会呢,不忘旧情就对了,这正是你令人欣赏的地方。”你说,“其实这件事,第一我无权也没有资格吃醋和别扭,第二我对叉子的母亲也很想念,如果她真的能来北京,我们一块赡养她。”
那些日子黄圆忙的不可开交,在将翠翠母子接来北京后,先是忙着联系落实刘山就读的学校,同时还四处打探着叉子母亲的下落。最后,她在环卫局人事处叉子父亲的档案中,找到了叉子家乡的地址。她按照地址写信过去,收到回信后马上找到你。
“大妈还活着。”黄圆对你说,“只是年纪又大,眼睛又不好,孤身一人日子过的很艰难。”
“我和你一道去接大妈。”你说。
那天,你开着车子和黄圆一道去河北沧州附近的一个村庄去接叉子的母亲。路上,兴致勃勃的她看出了你闷闷不乐的神情。
“你怎么了?”她问“不是因为这事让你……”
“跟这事没关系,”你轻描淡写地说,“是公司里的事情,遇到了一点儿麻烦。”
“不是一点儿麻烦吧?我看你这一段时间的情绪都不太好,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吗?”
“这事你可帮不上忙……真的是一点儿麻烦,没事儿,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嘴上这样说着,心中却已经在盘算着如果就此公司真的破产的话,今后该怎么办?事情的进展如你所料,如果全部按照无锡方面的要求进行赔付,刚刚红火起来的建筑公司破产是无法避免的。
几经问路,你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小村庄,并在村民们的引领下来到叉子家门口。
你们看到了叉子的母亲,她就站在门口向远处张望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她拄着拐棍,穿着一身没准还是丈夫留下的、洗白了的兰布工装,扶着长满蒿草的土墙,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秋风吹动着她那满头白发,像是要将她吹倒似的。
“大妈!”黄圆叫着紧忙走上去搀住了她,“我是黄圆,来接您的。”
“黄圆……”大妈念叨着,伸出干瘦的手,上下抚摸着她,“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是我,大妈,”黄圆眼里噙着泪水,“迪克也来接您了,您还记得他吗?”
“记得记得,当然记得,”老人说,“迪克,还有黄方,你们都是好孩子……”
你握住了老人的手,动情地说,“大妈,跟我们走吧。”
就在那一刹,你看着老人布满沧桑的面容,眼前陡地浮现出叉子死前站在桥头上那从容不迫的神情,他好像还笑了一下,没错,你肯定他笑了一下,面对刘震亚一伙带给他的死亡威胁,他的确轻蔑地笑了一下。与他相比,今天刘震亚给你设计的阴谋、带给你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不就是钱吗?你想,几年前你不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一个四处打工、没着没落的返城知青吗?
你环视着叉子家破败的院落,院子里长满荒草,仅有的两间北房向一侧倾斜着,像是稍有震动就会垮塌下来似的,门窗裂着大缝,发黄的窗纸被风吹得忽扇着。
“自打你们来了信,老太太天天就站在门口等着你们,一站就是一天,谁劝都不回去。”闻讯赶来的老人家在村里的一位亲戚对你说,“老太太一个人这么多年不容易啊!”
“以后就好了,”你说,“我们今天就接老人家走,你们放心吧。”
你们搀着老人进到屋里。你看到,屋里除了灶台边的那口水缸和炕上的那个小炕桌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件摆设,屋里到处都是尘土,炕还是凉的,只有老人被褥旁边的那两个骨灰盒被擦得锃亮。
“你们俩在这儿歇会儿就回去吧,”老人坐在炕沿上,拍着黄圆的手,说,“天太晚了又人生地不熟的。”
“行,咱们歇会儿就走。”黄圆说,“大妈,您看您还有什么要带的东西?”你看到,黄圆说这话时眼光扫向了炕头上那两个刺眼的骨灰盒。
“我不跟你们去了,”老人缓慢、清晰地说道,“我哪儿也不想去,你们能想起来看我一回,我这心里就……”
“别,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