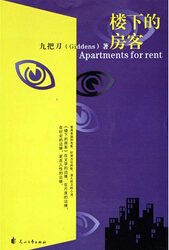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定主意这个字到底签还是不签。黎明时分,你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自己抗到底,就是不签这个字,刘大林他们能把自己怎样呢?把自己根本就没有干过的一桩罪行承担下来,这是不是也有点儿太窝囊了?既然这事是冲着自己来的,那他们就没必要非将老吴抓起来,刘大林讲的这些其实是抓住了你的心理要害,是在利用你对老吴父女的同情心理在威胁你。想到这些,你的心里开始踏实下来。拖下去,你想,就这样拖下去,看看他们究竟还有什么招数?
当然,眼前的路似乎还有一条,那就是逃跑,但那肯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起码需要黄方的全力配合。而现在你俩根本无法见面,但你坚信黄方在外面一定不会没有行动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与你见面。你又恢复了信心,打定主意拖延下去。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你坚持拖延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看到刘大林又采取什么新的动作。你感到,你和刘大林之间正较量着耐力,沉不住气又没有新办法的一方将是这场较量的失败者。
沉默的钟楼 34(1)
由于刘二林加入了审讯你的专案组,所以在他的极力建议下,也将黄方从运输机组撤换下来,安排他到田间拖拉机组干活,主要是上夜班翻地、耕地。比起搞运输,这种单调枯燥,每日像夜猫子似的白天睡觉、夜里干活的节奏,没两天就令黄方感到难以忍受了。为了逃避这活,他推脱自己患上了夜盲症,在翻、耕地时故意甩下大片的田边地角,起垅时也走得歪歪斜斜,两边差得八丈远。机务排长见此情景,只好将他替换下来,改为让他夜里在几处田间作业的拖拉机手送饭。黄方很高兴地接受下来这份活计,此活不但轻松,更重要地是他可以在夜间公开活动,随时找机会与你接触。
这天夜里,他像往常那样在大约十一点左右来到食堂,取出为拖拉机手们预备好的夜班饭,再用一条破旧的棉被将装着饭菜的十几个饭盒裹成一个包袱,用一根镐把挑在肩上。就在他走出食堂时,突然发现食堂后边的小屋里亮着灯,里面还有谈话声。他警觉地四下看了一眼,然后蹑手蹑脚地凑到小屋窗外侧耳听着。
平时,这间小屋是专门用来招待来连检查工作的上级首长们吃饭的地方。自打刘大林将他的办公室改作审讯室后,这里便成了刘大林的办公室,他和他的那帮打手们常在这里吃饭和商议事情。
小屋的窗帘挡得很严实,但黄方能够凭借说话声听出屋里都有谁。
“总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黄方听出是天津知青小魏在说,“他总这么死抗着,咱们太被动,听通讯员今天回来说,团里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那倒不怕,”刘二林说,“反正咱们有证据,不怕他不认账。”
“有什么证据?”刘大林说,“这案子要是总拖着结不了,对咱们很不利,你们没听这两天姓王的一个劲儿地催咱们先放人吗?”
刘大林指的姓王的,显然是在指王连长。
“那怎么办?”刘二林焦急地问。
“本来我是打算将这个案子搞清楚了,再向团里汇报,但现在看来可能不行了。”刘大林说,“有人走漏了消息,估计还是那个姓王的……看来,我们只有采取另一套方案了……如果他还是抗着不认的话,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停止审讯,按时送饭,并给他松绑,窗子和门也别再锁了……”
“那他还不逃跑了?”小魏说。
“就怕他不跑!他跑了属于畏罪潜逃,人跑得了事推不掉,事还在他身上背着呢,但咱们就主动了。”刘大林说,“小魏,你平时枪法那么好,等他逃跑时你完全可以……只要是他不在屋里就行……”
“指导员,”小魏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上趟厕所。”
黄方听至此,紧忙闪身躲进了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待小魏走过去之后,越过壕沟,跑进了青纱帐里。
他飞快地将几处拖拉机手的夜班饭送完,坐在地头上不停地抽着烟。绞尽脑汁地想着怎样才能帮你摆脱险境。黎明时分他决定,帮助你逃走是使你摆脱险境的最好办法。
你是在中午得知黄方的这一计划的。当时,从窗外飞进来的一颗石子正打在你身上,你瞥见那颗石子被纸包着,你赶紧打开那张纸一看,然后立即将纸团吞进了嘴里。
黄方在纸条上简要告诉了你目前所处的险境,告诉了你逃跑的时间和与你见面的地点。
午夜,当两台东方红——54型拖拉机轰鸣着从连部附近的三号地开回来前往油库加油时,你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两台拖拉机一前一后经过连部时,已经站在窗台上的你一个箭步窜了出去,落地后就势一滚,待你站起身时,已经躲在了场院的仓房后面。仓房旁边便是粮屯,一共有八个,最后一个粮屯就紧挨着地边了,地里长着齐人高的玉米。白天,你已设想过无数遍逃跑时的路线,你认定,只要你能顺利地进入这片玉米地,就基本上安全了。
就在你跑出了玉米地,来到国防公路边上的时候,连部方向传过来两声清脆的枪响。你跳进公路边的排水沟里,在灌木丛的掩护下,很快来到了见面地点——离连五里远朝鲜屯村边的公路桥洞下。
及至近前,你惊讶地看到,不但黄方等在这里,吴歌也来了。一见面还没说话,吴歌便扑进了你怀里。
“别这样,”黄方拉开吴歌,对你说,“待会儿你就在这儿等着,别的车不要拦,只拦从山里下来拉木头的车。我都观察好了,这几天夜里都有,给司机点儿烟,提包里有。”他说着递给你一只手提包。“能想到的我都给你备好了,都在提包里。我这里只有四十块钱,刚够回北京的,到时候你去找黄圆要吧……”
“我这儿还有,”吴歌掏出一沓钱递给你。“家里的钱我全拿来了,一共是一百多块,还有咸鸡蛋、馒头、水,你都带在路上吃吧。”吴歌说着又一次扑进你的怀里,紧紧地搂着你,浑身颤抖着,不停地哽咽着,“他们怎么把你打成了这样……你哪会儿回来……”
吴歌的泪水濡湿了你的脖颈,你望着泪眼模糊的她,任凭她颤抖的小手抚摸着你被打得肿胀的面颊,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只有亲人才能给予的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关爱。
“你藏好,我们先走了。”黄方拉开你怀里的吴歌,紧握了一下你的手。“我担心他们很快会追来。”
沉默的钟楼 34(2)
恰在这时,一辆从北往南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开了过来,两道雪白的光柱晃得你们眯起了眼,看不到后面的车厢。
“是拉木头的车,我听都能听出来。”黄方说着一跃而起,窜上了桥头,举起双手向迎面而来的卡车示意着。卡车“吱”地拉着长声刹住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伸出头来骂道,“你他妈找死呐?”
你紧忙跑过去,从提包里掏出一条香烟递到司机手里,说道,“哥们儿急着赶火车,带一道吧。”
司机迟疑了一下,看到黄方仍旧站在车前没有离开的意思,才点了点头,对你说,“上车吧。”
你坐在车厢里,卡车重新启动了。就在卡车快要驶离桥面的时候,吴歌追了上来,她边跑边喊,“我等你回来……我等你回来……”
那一刻,你的心悸动了。你知道,这是发自一位纯情少女内心深处的呼唤,是你根本无法拒绝的请求。
沉默的钟楼 35
如果说,没有过住院治疗经历的人生,算不上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并以此类推的话,那么没有流浪经历、甚至是逃亡经历的人生,就更算不上是一种完整的人生了。因为人在这种经历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寒冷、饥饿、疾病、被追捕、审讯、苦役等等平时很少遇到的人生考验,无论是来自生理的或是心理的种种磨难,都在无时不刻地考验着人的智力、体力、承受能力和生存技能。当然,如果说没有过此种经历算是人生的一种遗憾的话,换一个角度看,拥有此种经历同样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一个多小时以后你来到了团部,火车站与团部仅一路之隔。你跳下卡车,看了下表,凌晨两点。你走进小站唯一的那间候车室,售票窗口关着,屋里的长椅上躺着两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在那里昏睡,他们枕着一个肮脏的包袱,像是与你一样即将踏上流浪之路的人。
你盯着墙上那张残缺不全的列车时刻表,心中盘算着逃亡路线。先回北京是肯定的,你想,再从北京倒车去看望一下你的父母。当然,这些地方都不能耽搁太长时间,尤其是在父母那里,你不想给他们招惹事和令他们看出破绽。让你犹豫再三的是,你如何回去,是买票还是蹭车,蹭货车还是客车?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需要二十九块四毛钱,这对你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用这些钱来买票你还真有些舍不得。要是蹭车的话,客车舒适但危险,容易被人查出来,货车要安全得多,但是受罪。最后,你决定客、货车同时蹭,长途蹭客车,短途蹭货车,完全视情况而定。首先,是要尽快地离开这里。
黎明时分,你扒上了一辆货车,不是往南而是往北。你知道,往北是鹤岗,那里是国家铁路北线的终点,往来车辆多,选择余地大,你很多次拉煤去过那里,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到了鹤岗,你找到一家饭馆吃了多日来的第一顿饱饭,又买了两瓶白酒带在身上。当夜,你又扒上了南去的货车,是运煤的敞篷列车。临别时,黄方塞给你的那件破棉大衣起了作用,别看是在夏季,但当火车开起来时,尤其是在夜里还是冷风刺骨。在靠近车帮的地方,你在煤堆里挖了个坑,穿上那件破棉大衣蜷缩进煤坑里,一来可以挡风,二来可以隐蔽身体。列车走走停停,加煤、加水、让车、换车头,每一次火车停下来,都会令你紧张一番,因为例行的检修工作总是在这会儿进行。为了不致被人发现,你必需提前下车躲起来,而且离车还不能太远,这些车没准点儿,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好几次弄得你手忙脚乱。终于,火车在开到哈尔滨后彻底不走了,你等了五个多小时,也没见开走的车头再开回来,而且整列火车中前面的那几节零担车厢已经开始卸货了。你决定,改乘客车。
你在火车站候车大厅的厕所里,用凉水擦了个澡,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买了到达河北家乡的车票,你准备先去探望在乡下的父母,然后再开始你的流浪生活。
沉默的钟楼 36(1)
看着眼前那一条条长长的麦垅,黄圆直想哭。这些麦垅的长度是一千米,而黄圆每割一刀麦子的长度是三十多公分,她算计着,每干完一垅麦子,她需要弯腰费力地重复三百多次这样的动作。
此时已近晌午,她还没有割完一条麦垅的一半,而今天分配下来要她干完的有六垅。她支着自己快要直不起来的腰,收回僵硬得像是要断了的胳膊轻轻地活动着,无奈地望着早晨一块从地头出发,而现在离她越来越远的人群。
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黄圆的浑身上下早就湿透了,她不停地用毛巾擦着脸上和脖颈间的汗水,期盼着天气赶快阴下来或是刮一点儿风。说心里话,她真想学同屋知青晓云的样子,狠下心来割伤自己的手,就能有辙不出工了,蹭过这个麦收。她边想边伸出自己的双手端详着,到底割那只好呢?她拿不定主意也下不去手,刚才晓云那只被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