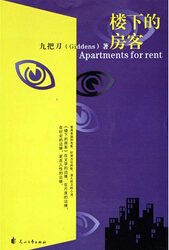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凛冽的寒风席卷着一望无际的雪野,你手中信纸的一角被风刮得咔啦啦直响,像是要被撕碎似的。你向四周望了望,划着火柴,将信烧掉了。
你站起身,揉了揉被寒风刮得麻木、生疼的面颊,使劲跺着脚,用力搓着被冻得僵硬的手指,走出了土坑。工地上,干活儿的人们正在渐渐散去,显然炮眼已经打好,又要放炮了,只有一幅“冒严寒斗风雪无所畏惧,修水利造良田百年大计”的横标,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
连续两年,每到冬季你们便要在这千古荒原的胸膛上,豁开两道巨大的口子,交由夏天的雨水,用泥土再将其填满。
你看了下手表,那是黄圆寄给你的生日礼物。差五分十点,该你们上场了。你突然灵机一动,自己添些钱,给黄方的女人买块表倒是正合适。
你是放炮组的组长。连你算上,小组里共有六个人,三名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知青,三名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本身就是黑五类,什么人干什么活儿,连里分得很清楚。一会儿,你们一人负责点十炮,谁也甭多谁也甭少,有了哑炮自个儿排,炸死活该。连里虽然没有这么明说,但你是这么理解的。
你站到土堆上,冲着躲在不远处沟渠里的那几名属下招了招手,他们很快凑过来。
“还是老规矩,一人十炮,最好是一次点着,不然的话,出了哑炮自己排。”你说完,点着了一支烟,紧嘬了几口。不管多没钱,只要是干这种点炮的玩儿命活儿,你总要抽好烟。那种烟丝太短,像锯末似的劣质烟,点不了几炮就灭了,到时候干着急,曾经有过这种教训。你将手中的烟递给站在身旁的老吴,这位北京的作曲家、教授,至今还不会抽烟,别人都说他除了会作曲之外,搞女人也挺在行。但你并不这样看他,相反,你倒是觉得他多少有些木讷,很单纯,是个好人。所以,你总在可能的范围内照顾他,有时还帮他完成一些劳动定额。你从不直呼他的姓名,总是对他很尊敬。看得出来,他多少对此有些受宠若惊。
重要的是,你对老吴的好感还来自另外一层关系,那便是他的刚上初中的女儿吴歌,一位漂亮聪颖、娇柔可人的女孩。老吴不知从哪里听说你会打乒乓球,便几次开口求你教他的女儿,说这孩子迷上了乒乓球,就是没有一个好教练。你答应了,并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教她,而吴歌仗着她天生的悟性和勤奋,每每总给你惊喜,短短几个月时间,她的那份架势和攻杀已经相当有样儿了。你感叹她的悟性和聪颖,私下里几次劝老吴教他女儿声乐。老吴起初说什么也不同意,说是绝不让自己的女儿在文艺圈里混了,但后来你还是说服了他,让他在家里偷偷地教他女儿练唱。隐隐地,吴歌在球技上的每一点进步,甚至令你产生了一丝成就感。
“还是那个顺序,”你边说边又点着一支烟,“老吴头一个,接着往下排,我最后。”头一个路途最近,排在最后的路途最远,在这里,点燃导火索后返回安全地带的路途远近,等于危险系数。
“现在开始。”随着你的一声令下,六个人像六只刚刚挤出圈门的马鹿一样窜了出去,直奔属于自己的那十个目标。他们顶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跳跃在布满塔墩、高低不平的荒原上,他们时而弯腰,沉稳冷静地用手中的烟头引燃导火索,时而狂奔疾跑,谁都希望自己头一个返回到安全地带。
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导火索的长度是经过严格测算的,十炮中最后一炮导火索的长度,只允许你们在丝毫无误地点燃后跑出大约三十多米的距离。虔诚而又狂热的人们还不知道,眼前这一投入了十万大军,数百辆施工机械的所谓水利工程,才是一桩最大的浪费,大自然的力量将会无情地给予证明。用不了三年两载,你们今天在地球上留下的所有痕迹,都将被大自然化为乌有。三九严寒,使冻土层掩盖住了这荒原下面那无边无垠、深不可测的苦海。在夏季,偶然间闯进这里的拖拉机开着开着,便会突然间沉下去,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你赶到了近前去看,会发现这里只是一层浸在水洼中的草甸子,与旁边的草甸子并无异样。这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但人们宁愿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而且还封锁诸如此类动摇军心的消息。等高线十七度以下的荒原不宜开垦成农田,应该保留草场原貌的专家论断,被视作是扯淡!这年头,专家的一切论断都是扯淡!他们的险恶用意是,阻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拥有更多的肥沃良田。
沉默的钟楼 28(2)
你点燃了最后一炮后,直起腰,边往回跑边朝老吴喊道,“您那儿用帮忙吗?”
“不用。”老吴疾跑着,显得有些兴奋,动作也格外麻利。每次,你总要替老吴点上两炮,而此刻他已经跑到最后一个炮位跟前了。
早晨,老吴对你说,连里已经找他了,让他给连里的宣传队当指导,连里的宣传队要是没人给指导一下,连锣鼓镲都敲不出个准点儿来。大概是即将重操旧业的喜悦,再加上来自组织的器重,令他显得有些激动,受宠若惊的神情溢于言表。
跃过沟渠旁的土坡时,你看到远处营区内的大道上,不知什么时候用松枝扎起了一个简易牌楼,几面彩旗在上面迎风招展。春节到了,一年中仅有的两天假期快要来了。
又有两个人跑回到沟渠里。
“您快点儿。”你又一次冲老吴招呼着。
“来了,来了。”老吴答应着,一手扶着眼镜,一手插在兜里,气喘吁吁地向这边跑过来,脚步像踩着节拍。他一定是在心里默诵着语录歌的旋律,也许,从明天或是下午,他就可以开始放开歌喉,施展特长了。
他的烟呢?
就在老吴快要跑到沟渠边上时,他的身上突然响起一阵“啪、啪、啪、啪”的连续爆炸声,老吴惨叫着,倒在了血泊中,身上的棉袄被炸得四处飞散,腹部一片血肉模糊,一团团的棉絮在他身旁飞舞着。
远处,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接连轰响起来,惊天动地,土块横飞,你在心里计算着,应该是六十炮。
“老吴……”你大喊着,不顾一切地冲上沟渠,将他拖了下来。
一切都明白了,老吴在点燃了最后一炮之后,忘乎所以地将冻僵的、拿着烟头的手,揣进了装有多只雷管的衣兜里。
炮声停止了,工地上静极了,一阵阵欢庆节日与胜利的喜庆锣鼓声随风飘来。
专业真害人!
“刚才响了多少炮?”你蹲在地上,怀里抱着昏迷不醒的老吴,怔怔地问道,“谁数了?”
“刚才这一乱腾,谁也没数呀。”胡瞎子说。
“都先回去吧,我马上送老吴去医院。”你说,“下午都来检查一下,谁的哑炮谁负责排除。”
深夜。团部医院。
你守候在手术室门外,老吴的手术已经进行三个多小时,一位从里面出来的大夫告诉你,伤员的腹部和右手上,有几百块雷管碎片,虽说都在浅层,但也别指望一、两次手术就能摘干净。
长长的医院走廊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灯,你刚要躺在长椅上睡一会儿,忽然看到连里的人抬着副担架走过来,胡瞎子躺在上面。
“他怎么啦?”你焦急地问。
“也给炸了,下午排哑炮时炸的。”
“炸哪儿了,”你又问,“有危险吗?”
“炸鸡巴了。下午排哑炮时,他非要往没炸的炮眼里撒泡尿,说是这样安全。没想到,他刚把那玩意掏出来,炮就响了……准是导火索又受潮了,你放心吧,他没危险,这小子命大着呢,刚才他还叫唤疼呢……”
又来了一个,挨炸也成双成对。
“胡瞎子,醒醒,快醒醒,我是迪克,”你伏下身,摇晃着胡瞎子,“你老小子怎么总是玩儿邪的……”
胡瞎子“哼哼”着,睁开眼,说,“哎哟,真他妈疼死我了!要不是我有经验,反应又快,紧着趴下,这回小命准得玩儿完!”
“上午放炮时没你呀,”你说,“我走时嘱咐好了,谁的哑炮谁自个儿排。”
“是我主动要求去的,那活儿不是轻省吗。”
“快进去吧。”你催促着,颓坐在椅子上。
胡瞎子是本地老职工,虽说已近五十还没有结婚,但他的鸡巴却屡遭蹂躏。早先他在农场里放牛时偶然发现,那些随着前来此地参加农场援建的苏联农业专家的夫人、小姐们,常爱到河里去游泳、洗澡。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总一个人躲到河边的树丛后面去偷窥人家换衣服。没想到有一天,那些闲得没事的女人们发现了他,于是分工合作,给他来了个迂回包抄,正逮了个结实。不容分说,她们就将胡瞎子连拉带扯地拖到沙滩上,扒光了他的衣服,就地取材,用沙滩上滚烫、粗硬的沙子,把他的鸡巴揉搓得血痕累累。
胡瞎子被紧急处治了一番之后,又被抬到观察室去了。医院里只有一个手术室,他还得先忍会儿。你看着疼得嘴牙咧嘴的胡瞎子,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
此时,你又想起了一个人留在家里的吴歌。中午,你们临上车时,她那眼泪汪汪、无依无靠的神情,真叫你怜惜。
“别哭,我会照顾你的。”你轻声对她说着,重复了好几遍。
沉默的钟楼 29(1)
你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一九七一年的除夕。那天出奇地冷,狂风刮了一整天,连里破例早些收了工。黄昏时分,当你疲惫地拉着铁锹从水利工地走回连里时,恰好碰到从团里回来的拖拉机。连里的通讯员也在上面,他喊了你一声,扔下一封信来。你紧忙捡起来看,信封落款是一处你从未见过的外地农村地址,但笔迹分明是你熟悉的父亲的笔迹。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你的心头。信确实是父亲写的,信中告诉你,他和你母亲都被轰到农村老家去了,因为刚回农村,连一间可以栖身的住房都没有,一切都需要安顿,所以迟到今天才给你写信。 父亲的信写得很平淡,没有任何情绪在里面,除报平安之外,似乎来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知你一个新的通信地址。
你站在路边看着信,先是手部,而后是胳膊,最后是整个身体都无法抑制地抽搐起来,双腿一阵阵地发软。你拉着铁锹,支撑着快要瘫软下去的身体,脸色蜡黄,只觉得一股股的寒气袭进了你的身体里。那天你没有吃饭,直接回到宿舍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三天三夜。
这三天三夜,你始终在昏迷中,分不清白天黑夜,身体忽冷忽热,不停地发着高烧。三天三夜你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只记得在一次醒来时爬到炕下,喝过一次桶里的井水。昏迷中,你似曾听见连里的卫生员来过一次,但他只说了句,他在发高烧,等他醒了给他吃两片解热镇痛药就好了。以后再没有来过。
第三天午后你醒了过来,浑身上下显得轻松了许多,头脑也不再昏沉。宿舍里静悄悄的,你瞥了眼门上挂着的日历,才知道自己已经躺了多长时间。当你撩开被子试图下地走一走时,一下子惊呆了!你看到,你自己原本健壮的双腿,竟然瘦得只有锹把那么细,只有一层松驰的皮肤包着骨头……
你被确诊为急性肝炎,住进了团部医院,在那场北大荒大面积流行肝炎的瘟疫中,你成为被病魔俘获的一员。
有人说,病房是一个小世界;也有人说,没有住过医院的人生算不上是完整的人生。通过那次近三个月的住院治疗,你对这些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