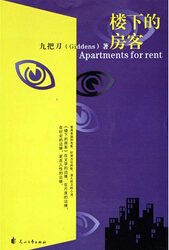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这里过河、过铁道、再爬过那段城墙,就是你们的学校。此刻,你看到学校茶炉的烟囱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冒着烟。你趴在铁轨上听了一会儿,确认在五分钟之内此处不会有火车通过,感到有点沮丧。这是什么兆头?通常此时总会有一列火车通过的。
至今,你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北护城河的模样。那高高的河堤,青青的草地,那树冠向河心倾斜着的垂柳,那汩汩流淌的河水。为了方便过河,你们曾在河水最浅的地方摆放了一行石块,你称之为“浮桥”。站在河堤顶端,叫喊着,以百米跑的速度向着河床冲下去,在汩汩水声的伴奏下,准确而又轻巧地跳跃在“浮桥”上,再冲上对岸堤顶,这是你的绝活,有着当众表演从未失败的记录。
但是,那天你却失败了。正当你跳跃在河中心的时候,忽然感到一阵晕眩,阳光下的河水似乎在晃荡,你无法控制地一个趔趄掉进河里,眼看着脱手而出的书包,随着湍急的河水向远处飘去。
你站在河里,目光怔怔地呆立着,心想,不是要出什么事吧?果然,在那个早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真的印证了你的预感。
“我去把它捞回来。”黄方一边讨好地说着,一边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河里。
“算了,反正也考完试了。”你说这话时,脑海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从此再不背书包了多好!你讨厌书包,也讨厌学校。你没有料到,你的这个愿望,正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明媚阳光的早晨,借助于这世代流淌的河水实现的。
河堤的上面是一片开阔地。站在破败的城墙上,你看到了父亲上班的那所学校和自己学校的操场。此刻,操场上已经有不少同学了。再往南边,便是钟楼、鼓楼、北海的白塔和景山的知春亭,其余的是一片没有尽头、高低错落的灰色层顶。在靠近城墙的附近,是一片黑乎乎的棚屋。你猜想,那一定就是劳动人民的住所了。
你似乎明白,劳动人民就是报纸和广播里常说的工人阶级,就是同班同学的那些爸爸妈妈们。你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整日里也在工作和劳动,却不能算是劳动人民。尽管没人对你明说过,但从爸爸妈妈整天哀声叹气、唯唯嚅嚅的神情,和“耗子”对你冷嘲热讽的态度,你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黄方爬上城墙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身上全湿了,手里捧着你刚才掉进河里的书包,一群人紧追在他的身后。你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正待转身要走的时候,身后传来一片叫喊。
“那俩傻X站住!就说你们呐,站住!”
随着叫骂声,你看到那些人已经追了上来,在你们身旁围成了一个半圆,拦住了你们的去路。
“你丫的刚才骂谁呢?”那伙人中一个身穿蓝色工服,中等个子,面色黝黑的人对黄方说,“甭他妈装傻,就说你呐。”
“刚才在河里捞书包时,这帮人跟我找茬,我就……”黄方小声向你解释着,声音有点儿颤抖,一副求助的神情。每当他露出这种神情的时候,一般都祸到临头。
当时你真的怕了。与其说是你们两个,不如说只是你一个人(因为你了解黄方,打起架来,只要不被打趴下,他跑得比谁都快),要面对年龄和个子都比自己大的中学生,结果肯定是要被打得头破血流。
你镇定了一下,将浑身颤抖的黄方推到自己身后,完全是靠一种莫名而至的鲁莽和少不更事的逞能支撑着,神态自若地对为首的那个人说道,“我们正要上学去,我们可不想打架。”
“去你妈的!你丫往前凑什么?”为首的那人上下打量着你,一副不屑的神情,“也他妈找花呐。”
你们俩的身体近在咫尺,你们四目对视。对方那双在浓浓的剑眉下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那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将“花”字用作形容词,你估计,“花”字用在这里的含义肯定是,头破血流。
“我跟你说了,我们不想逃学。”你站着没动。你清楚,此刻只要你们转身一跑,身前身后就会乱石如雨,这河边、这城墙,从此也就休想再来了。“真想打架的话,今天下午四点我们放学后,咱们还在这儿。”你边说边指着他身后的人,“你们现在是不是人也多了点儿。”
“哼,小丫的口还挺正,”那人痛快地说,“那咱俩就单练。”说完之后,他退身一步拉开了架势。
你在说“行”的时候,感到裆间猛地收缩了一下,先前身体的恐惧瞬间消失了。随后,全身都好像绷紧了,变得轻盈而有力。你向四周望了望,四周空旷无人,迎面是一轮金光灿灿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你机敏地左躲右闪,挡过那人的一阵急拳之后,和他扭打在一起。你用力支撑着对方猛压过来的身体,躲避着来自他脚下的绊子,脑海里却在不断地闪现着你在什刹海体校学习乒乓球时,隔壁训练馆里摔跤教练们时常做的示范动作。你慢慢地移动着脚步与他周旋,趁他稍显懈怠的当儿,突然间上身向后一闪,抬脚猛地向那人的脚下铲去,与此同时,两臂用力扭向一边,对手被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
沉默的钟楼 2(2)
那人的样子很难看,看来是被摔得够呛,地上的砖头硌痛了他。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艰难地站起来,手里变戏法儿似的,不知何时攥住一把锃亮的刀子。
一看见刀子你慌了,你还从没有跟手里有刀子的人打过架。顾不上多想,你猛地扑了上去,一手掐住对方的脖子,一手紧紧攥住他那拿着刀子的手腕。
刀子在空中停滞了一会儿之后,那人便在手腕能及的范围内,缓慢地顺着你的胳膊向下划。你看到,你已经穿了三年仍然心爱的灯心绒夹克袖子被划破,胳膊也被划出了一道深浅不一,断断续续的口子,向外殷着血。
“嘿!”你大叫一声,使劲搡开对手,就势一个下勾拳,准确地打在那人的下巴上。你可以肯定,对方在你猝不及防的一击下,咬了自己的舌头。你看到他的嘴角渗出了血。趁他稍一迟疑,你紧跟着迎面对他又是一记重拳,拳头被硌得麻酥酥的,那人的鼻血畅快地流了出来。被他随手一抹之后,满脸是血。
对手被“花”了,你感到一阵兴奋,身体随之变得更加轻盈,双脚富有弹性地跳跃着。你感到自己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惧怕刀子了。
当对方挥舞着刀子,疯狂地又一次向你进攻时,你灵活而冷静地一次次躲闪开,然后瞅准空档,迅即飞起一脚,准确地踢在那人的手腕上。
对方手中的刀子被震落在地上。你瞥见黄方猫一样窜了过去,捡起地上的刀子转身扔进了河里。刹那间,你又是狠狠地一脚,正踢在对手的裆间。
那人难受地弯下腰,捂着肚子倒退了好几步,最后蹲了下去。他的脸色由黝黑变成了蜡黄,额头上渗着汗珠儿。你可以肯定对手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你有过这方面的体验。那是在你刚进入四年级时,因为占抢乒乓球桌子,一个高年级学生令你尝到的。
见此情景,对手身后的那群人哗啦一下围了过来,手里拿着棍棒和砖头,一个个气势汹汹,大有将你们俩顷刻打烂的架势。
“算了,”对手捂着肚子艰难地站起身来,挥了下手,说道:“让这俩好学生回去上学吧,今儿先饶了他们,这笔账给他们记着,咱哥们儿说话得算数。”
“傻X,你丫知道你在跟谁打架呢吗?”对手的追随者们心有不甘地瞪着你们,嘴里边骂着,边扔下手中的棍棒和砖头,纷纷向对手聚拢过去,搀扶着他。“他就是叉子!你丫打听打听去,谁他妈敢跟叉子过招,你们俩小丫的等着,这事没完!”
那天早上,以叉子为首的那伙人,最终还是放你们俩安全地走了,叉子并没有恃仗人多而违反你们打架之前单练的承诺,你和黄方侥幸地逃过了一难。但在事后,在你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有关叉子的种种传闻之后,你真的有些后怕,真的庆幸自己能站着从叉子的手里逃出来。你绝没有想到,在这以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叉子在北京城里的名气,就像那些在文革中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那样日升日隆。他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作为所谓“联动”、老红卫兵和公安局的对手,被他们称为所有“地痞、流氓和社会渣子”的总代表,叉子在北京中小学生中的影响,一点不比今天的港台明星和所谓的“韩流”逊色。
你也绝没有想到,“不打不成交”的古谚竟在你俩之间得到了应验。你们不但在日后成为了好朋友,他用年轻生命诠释的某些东西,甚至影响了你的一生。
沉默的钟楼 3(1)
在谈到你的家庭的时候,不能不说一下你家所在的那个地方。你家所在的那条胡同,东边是北锣鼓巷,西边是宝钞胡同,这两条长街的尽头便是北城墙了。在这两条长街当中,横着许多条胡同,整个北城就是由这些长长短短、或宽或窄的胡同和高大的城墙组成的。当时你认识社会的视野,就局限在你的学校和你所熟悉的这些胡同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你知道了许多原先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你从别人嘴里听说了与你们住了多少年的邻居,他们都曾从事过什么样的职业,他们都是什么出身,一个有着二十多个院落的胡同,在那个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隐私的时代,几乎被你这样一个孩子了解了个遍。什么一号的房东是个大地主,二号的房东是个资本家,三号的房东是个旧社会在天津商界混的洋买办,四号的房东是一个旧军阀手下的旅长,五号的房东是个伪警察,六号是个大宅子,据说原先是个蒙古王爷府,现在住着一个共产党的大官……这就使你对当时的一个流行说法产生了怀疑。既然报纸上总说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劳动人民,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只占不足百分之五,那在你身边怎么住着这么多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如果按照你家所住的这条胡同的住户比例来算,这说法颠过来还差不多。后来你到了农村才明白,这说法主要是针对农村而言的,在大城市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在北京,由于它几百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所决定,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历朝历代的各界精英在失势和败落之后沉淀在这里,不少家庭都有着一段可以夸耀的家世。
你家住的那个院子是个标准的四合院,里院住着房东,他是一位大学教授,你家租住在外院的四间南房里。黄方的家与你家紧挨着,你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玩。他家的房子是自己的,不但房子多,院子还特别大。黄方有一个姐姐,叫黄圆,上初二,是你家那一带最漂亮的女孩儿,那时就长到了一米七三,用今天的眼光看,她长着一副标准的模特身材。她那凝脂般雪白细腻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高挺细直的鼻梁,弯弯的眉毛,红润丰满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让人简直无法找出她的缺点。
黄方的父亲叫黄宗远,五十多岁,面色红润,身体强壮。他和妻子都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进进出出的,显得挺忙活。在你看来,黄宗远的忙活主要集中在厨房里,他似乎一刻不停地在做饭,除了给家人做之外,还要给他养着的七、八十只鸡做。那些鸡源源不断地供给他家鸡蛋,帮助他家度过饥荒和保持营养。每天他遛早的时候,都要在所经过的几个菜店里,捡回一大口袋人家扔弃的各种各样的菜叶,然后再到垃圾站拾回一些剩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