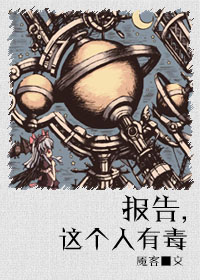嫌疑人-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来了,他上楼梯之前,她坐在露台上看见这个男人。几天来,她一直守候在露 上,她一直固执地、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守着露台,她观望着每一个出入的男人或女人。
直到那个男人穿着一件风衣,那是一件暗灰色的风衣上楼,音乐出门时,总是习惯于穿那种颜色的风衣。他来了,因为他抵抗不了内心的那种忧虑和焦灼,因为失去了欧丽丽对这个男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迷惘,所以,她相信他一定会来的。他上楼梯的声音并不急促,那是他有意掩饰住的困兽似的焦躁,他敲门时,一点也不恼怒,这正是他的优雅,许多女人都因为迷恋上了他的这种优雅,而被其奴役了一生。
她就是被其奴役者之一。
她打开了门,这是她为之等候的风暴,她穿着一件长裙,他曾经赞美过这条长裙,他赞美她的时候,她和他发生了短促的情欲关系。那是惟一的一次情欲关系,之后,再也没有发生。然而,这惟一的一次使她将为此纠缠他一生吗?
《嫌疑人》第三十八章(2)
音乐家依然是为欧丽丽而来,他申明说欧丽丽只可能在她布置的阴谋中消失,他似乎已经穿透过了她那具病态的、颓废的、充满黝暗精神之旅的身体,他恼怒地说:“你就是那只狐狸,我想不通,当初我为什么为你作曲,我为什么对那只在林中穿巡的狐狸充满了激情?”“因为我是惟一的,只有我可以跳出狐狸舞,只有我可以让观从看到那只狐狸的孤独和忧伤。”她走上前去,脱掉了那件风衣,她递给了他一杯红酒,这是她早已准备好的,如果她想让他死,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然而,她从来没想到过毒药,她生活中从未产生过那种致命的险境,因为她之所以递给他杯子,是想让这个男人为她而留下来。这一次,她没有在杯子里放安定片,她想慢慢地观看这个男人倍受折磨的脸颊。
他缺少理智地同她干杯。他肯定要醉,这正是她乐于看到的一种场景。他像孩子一样地躺下去了,然后又像孩子一样的醒来对她说:“我要找到欧丽丽,我一定会找到欧丽丽的。”她坚决地说:“你不会寻找到欧丽丽的,她已经怀孕了,她就要跟这个男人结婚了。”他清醒了审视着她说:“所有这一切你都知道如此清楚,这是为什么?”他离开了,她本以来他会再来求她,为了欧丽丽他一定会继续来求她的。然而,从此以后,她坐在露台上再也没有看见一个穿暗黑色风衣的男人走进来。
她似乎知道他已经不会来了,欧丽丽已经消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按照规则,欧丽丽的名字被歌舞剧院除名了。她得到了一种满足,在歌舞剧院今后再也看不到她的敌人了。她想回到舞台上去,回到她生命的核心中去,她想再一次拥有一场属于她自己的舞蹈高潮。她知道欧丽丽缺席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为此,她想替代欧丽丽,她想完成欧丽丽来不及开始的那种舞蹈,那是一只蝴蝶舞,她来到了练功大厅,令她生命为此窒息的一种现实场景突如其来,一个年轻的女孩,比欧丽丽更年轻的女孩已经站在了欧丽丽的舞台上。
而且,旁边所有的舞台都已经被年轻的舞者们占据了。她们仿佛从蜜一样的蜜房中涌出来,浑身带着甜美而动人的舞姿在练功房中伸展着四肢,音乐家正在那间欧丽丽的从前练功房间里,专心致声地弹着钢琴,那个女孩正翩翩起舞。
她所虚拟过的场景都已经被现实所覆盖。欧丽丽消失了,并不意味着她已经获胜。就在那个最为失意的时刻,一个她的舞迷者走了进来。这个舞迷是一个中年男人,几个月以后,她结婚了,然而,从那以后,她却走出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怀孕,像欧丽丽一样去怀孕。她突然真正地隐退下去,她新婚不久的丈夫让她眩晕,她再也不想回到舞台上去,也许是因为欧丽丽消失了。
《嫌疑人》第三十九章(1)
“我想曾经迫不及待怀孕,我近乎疯狂地想怀上孩子,然而,很长时间过了,我依然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我来到医院,妇产科医生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身体,询问了一遍身体的历史,然后不容置疑地告诉我说,因为第一次流产得不到极好的疗养和休息,我的身体从那时就蒙受了创伤,致使我怀孕非常困难……而且对我来说有可能会丧失怀孕的希望。”
杜小娟听完医生的话以后,整个身体似乎已经再一次失去了支撑点,她下了妇产科的楼梯,视线变得越来越黑暗。医生说得很对,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无法怀孕,每一次她结束性生活时,都渴望着怀孕,她从这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的期待着,然而,她却是一个失败者,她再也不可能怀孕,因为上帝要惩罚她。就在这个时候,欧丽丽像一阵呼啸的风一样卷回来了,那已经两年以后,那时候,欧丽丽显然已经失去了歌舞剧院的舞台。
杜小娟描述并回忆着那个晚上她跟欧丽丽的秘密约会。她一因到这座城市的当天就给杜小娟打来电话。这个时候的杜小娟已经跟丈夫彻底地分居,因为她昔日的舞迷,追求她的男人在听到她与音乐家的那种谣传之后质问她,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她说:“不错,我们曾经是情人关系,如果过去的事情你都想追究的话,我们可以分开。”丈夫是一个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部,他忍受不了她的那段历史,因为音乐家的形象已经占据了这座城市,每个人提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名人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提到音乐家的名字,不仅仅如此,那个名字已经风靡在许多大城市的广告牌和音乐媒体上。
丈夫忍受不了这一切,同意和她分居。她也不再做怀孕的梦想,从听到欧丽丽打来电话时,她的身心中洋溢着那种萎靡不振仿佛被溶解了,欧丽丽要见她,而她当然也想见欧丽丽。欧丽丽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她已经离婚了,把孩子给了前夫,她厌倦了提供给她物质生活的男人,因为感觉到她的灵魂每天都在潜逃着、漫游着想重新回来,她割断了婚姻的绳索,回到了这座城市,然而,她从下飞机时就感觉到四周空荡荡的,根本就没有欧丽丽的位置。对此,杜小娟毫不迟疑地告诉她说:“不错,你离开后的第三个月,你就已经被歌剧院除名了。”欧丽丽承认这是她的宿命,她逃脱不了这种宿命,因为在她被一个人中一种生活笼罩时,她有一种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忘记规则,忘记所有的游戏规则,这必然要让她失去生命中很多东西。
欧丽丽的身体依然没有发胖,她说生完孩子以后她就开始练身,她害怕自己为此胖起来,她害怕时间会惩罚她自己,所以,从那一刻她就作好了准备,想回到她从前生活的地方,想重新拥有她自己的舞台。
杜小娟刻薄地说:“你想重新占据舞台,那简直是梦想。因为那些比你年轻和有姿色的女人已经替代了你。你为什么总要舞台呢?你为什么总想抓住不松手呢?因为你忘不了音乐家,他现在的名声比过去更大了,在这座城市,他是偶像,是情圣,而你是什么呢?”
欧丽丽从箱子中取出了一大堆她和音乐家在一起时拍摄的照片,充满自信地说:“我拥有这些证据,如果有他帮助,我就会回到舞台上去,因为我还年轻……”那是一些自动拍摄的照片,是她和音乐家拥抱时的许多幅照片,欧丽丽说:“他对我说过我曾经是他的灵魂,我一跳舞,他的灵魂就会紧追不舍。”
杜小娟笑了,她已经是一个饱尝人世艰辛的女人。所以,她的笑像是在嘲弄欧丽丽,她用那种女人和女人之间暧昧的笑嘲弄着欧丽丽的这种无知的幻想,随即她又把这种幻想托起来,对欧丽丽说道:“是啊,这些照片就是证据,为什么不去找他帮忙呢?我要是你,就一定会去纠缠他,有了这些照片,你就一定可以纠缠到底。”
欧丽丽在她鼓励之下,寻找到了力量,这时候,两个昔日的敌人突然变得亲密起来,因为她们拥有了同一契机:在两个人已经失去舞台之后同攀附一种枝杆,那是一个男人的肩膀,她们要在这个世界呼吸这个男人的味道,并让这个男人帮助她们寻找到已经失去的舞台。
两个人犹如遭遇到一种自然灾害之后重又回到了明媚的春天,她们沉浸在春天的幼芽之中时,并不知道音乐家正在筹办他的个人音乐会。
在短期内,她们怎么也无法寻找到音乐家到底在哪里。她们寻遍了音乐家有可能出入的地方:比如,音乐家过去的住宅和现在的住宅,两个人分别把守着出入的小径,她们都想呼吸到音乐家的气味,因而她们似乎已经变成了狩猎人;比如,音乐家有可能出入的茶巴和餐馆,那是夜晚音乐家容易闯入的空间,而通常他出入这些地方的时候会跟朋友们在一起。
两个女人都无法看到音乐家的影子,就在这刻杜小娟突然想起一个女人,一个比她们都年轻的女人,她就是殷秀花。杜小娟告诉她说,自从她消失以后,女人就替代了她——出演那场蝴蝶舞,欧丽丽听后脸色像霜降一样地颤栗着说:“人生真可怕,人生为什么总有替身存在呢?”欧丽丽想见到殷秀花的愿望变强烈了。于是,她撤出了被她困守的每条有可能见到音乐家的路径,她们开始通往另一个路口,那是殷秀花出入的地方,那是一个新的“嫌疑人”。对于洪范晓琼来说,殷秀花确实是一个“嫌疑人”,母亲的讲述突然被阵阵火车的轰鸣声再一次折断了,母亲的嘴唇突然变得很干燥,仿佛可以用火焰点燃,母亲说:“我累了,因为夜色来临了,我想睡一觉,你父亲的故事让我感觉到疲惫。”
《嫌疑人》第三十九章(2)
母亲躺下去了,她被回忆中的难以忍受的干燥折磨着。折磨母亲的自然是她的同类以及母亲的异类。范晓琼从包厢中退出来,她想透透气,她想回到现实,她想由此回到火车厢中的人群之中去,她想放下许多被触角似的天线所触痛的神经,她想回到父亲生活之外,因为,父亲的生活让她感到困惑。
然而,除了张岚、母亲、欧丽丽、杜小娟之外,还有一个叫殷秀花的女人,她们中谁是“嫌疑人”?她们都触及到了父亲私人生活中的碎片,她们都有可能威胁到父亲的生命,那么,谁是真正的“嫌疑人”呢?她尽可能地搜寻着,仿佛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搜寻着父亲的踪影,因为在她们与父亲的纠缠中失去了父亲的踪影,意味着她们在父亲的生活中严重缺席:因为缺席同时意味着她们失去了纯粹的位置,无论是舞台的位置也好,还是床榻的位置也好,对她们来说都是一种从外套渗透到内衣之中的颜色。
范晓琼突然感觉到无法摆脱的忧伤,因为父亲的死亡之迹越来越黑暗。她自己的肢体仿佛染了色,一种涂鸦似的颜色;这是一种犹如一只飞舞的蝴蝶把自己突然变成标本似的颜色。
她终于累了,决定回屋去休息,她将随同火车的轰鸣、嘶叫声入睡。因为她要蓄积力量,她还要到那些纷繁复杂的世界的出入之地寻找她的嫌疑人,她回到了车厢,母亲就在对面,母亲似乎睡得很沉,于是,她也躺下了。这一睡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当她睁开双眼,她正在寻